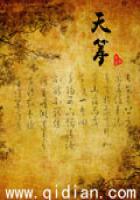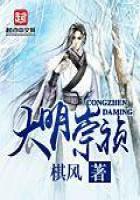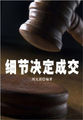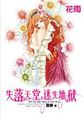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也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也愿意早日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坚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那就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愿望。”“引起战争,对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就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这么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张副司令前途,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最后,周恩来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张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23)但周恩来的这番话并没有说服东北军少壮派。苗剑秋不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大哭大闹起来,边哭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出“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那咱们就先破裂”这样的重话。孙铭久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来跪下,请求红军出兵。
周恩来只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送走少壮派天还没亮,南汉宸也赶到周恩来的住处。他向周报告了两则重大消息:一是孙铭久已经拟定了一个暗杀名单,内中不仅有主和派,还有共产党人。二是杨虎城态度有变。
原来,这天凌晨3点,杨虎城即把南汉宸从床上叫醒,对南说:“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这种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纯朋友关系,一是政治关系。在政治关系方面,我是对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你们要暴动,蒋介石派韩振声来要我逮捕你,我不肯,宁愿抛开部队去日本,不愿同你们决裂。1930年入潼关后,我用你当秘书长。1932年冬,黄杰兵压潼关,拿着蒋介石的命令要逮捕你,我不惜冒战争的危险放你走。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你这次来西安,我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现在回来的希望不大,他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24)显然,杨虎城的这番话,不仅是说给南汉宸本人的,也是说给中共代表团听的。否则,他不会深更半夜把南汉宸叫起来。同时,杨虎城此番话的背后,也还隐藏着更深的不便明说的意思:中共应当更多地帮助杨虎城摆脱困境,如果中共对杨帮助得不够,或者杨感到自己的安危没有保证的话,他将不再选择和平,而是可能会附和东北军少壮派的主张。
周恩来充分感受到杨虎城此番话的严重性,他吩咐南汉宸:你马上转告杨先生,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接着,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一起迅速赶到三原红军前敌司令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左权等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当前事态和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与会者认为,东北军和17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17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与他们协同打一仗。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否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打有两个前途: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我们应力争第一前途的实现。
会后,周恩来和博古、彭德怀、张闻天等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征求意见,并于当天收到毛泽东表示同意的回电。
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红军的决定告诉了杨虎城和少壮派。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你们。”
在中共这次紧急会议的前一天,东北军在少壮派的提议下,在渭南召开了由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由于王以哲因病未能出席,会议由“总部”中将参谋长董英斌代为主持。何柱国首先发言,认为“中央军”实力强大,假如打起来,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的前途也危险了。他主张接受甲案,和平解决善后。
何发言后,应德田起来发表了坚决反对和平解决的讲话,应认为:蒋介石是在虚张声势,真正打起来他就不敢了。我们愈软,他就愈硬,我们一硬,他就会软下来。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可能回来。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并且说:“现在杨主任和17路军都主张副司令不回来,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中共代表团也表示支持我们的主张,必要时红军也可以帮助我们打仗,难道我们反而胆小怕死吗?”与会人员在应德田发言的鼓动下,群情激愤,一致赞成应德田的主张。会议决定: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之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切,决一死战!40多名与会军官都在这个决议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不能执行渭南决议。但是,渭南决议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谁也没有理由擅自推翻这个决议。于是,他们想到了于学忠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的最高负责人,就商议请于学忠回来,由于做出最后决定。
1月31日,于学忠被接回西安。
当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等5人,分别代表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召开最高级会议。应德田等少壮派在室外旁听。杨虎城作为西安方面的最高首长主持了会议。
首先发言的是于学忠,他表示:我的意见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打对我们是不利的。
为什么不能打呢?于学忠分析说:我们只顾对付东线的“中央军”,西线还没有怎么布置,而胡宗南的军队已经进至宝鸡,再加上我们内部檀自新、沈克两个师有不稳的消息,我们在军事上处于内外夹击、腹背受敌之势,因此,打仗不仅不应该,而且不能打。何况,主战的理由主要是副司令没回来,打仗就能够把张副司令打回来吗?我看不但不能把张副司令打回来,恐怕还害了他。
于学忠的和平姿态,与王以哲、何柱国的意见不谋而合。王、何随即表示赞同,并提出:先撤兵,服从中央的命令。
东北军3位大将意见一致的和平态度对杨虎城产生了影响,本来此前的几天里杨是一度转向主战的,这时也表示了接受和平解决的主张,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
周恩来是最后的发言者。会议出现的如此结果他当然是高兴的,他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又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曾决定只要你们双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和平解决的主张,全力支持你们打一仗。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但是,会场外面“战”与“和”两派争执激烈,在会场之内却如此平静地通过了“一边倒”的主和的决议,这使周恩来感到十分不安。他严肃地提醒与会者:“请你们要注意内部团结和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在周恩来发言后会议作出决议:宜和不宜打,坚决促成和谈成功。这个决定,与两天前的渭南会议决议完全相反,这是一般人所没有料想到的,也使主战派大失所望。
遗憾的是,周的告诫并没有引起东北军将领的重视。2月1日上午,于学忠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开会,传达王宅会议精神。于宣布“按潼关谈判的协议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后,会场里鸦雀无声,于又说:“我受张氏父子两世之恩,打吧,怕打不回副司令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放声大哭,许多人也跟着痛哭流涕。
于学忠的解释未能使少壮派信服,他的哭诉也不能感动少壮派。这时,少壮派中情绪已经难以控制,特别是应德田、孙铭久等人,认定推翻渭南会议决定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是王、何在三方最高军事会议上没有反映主战派的要求的结果。他们在官兵中宣传:“先撤兵是投降蒋介石的另一种形式”,并决定:铲除王、何,保留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总负责于学忠,执行渭南会议的决定。
2月1日晚,少壮派在西安街头贴出了“除奸”的标语,并开始制作“反对和平”的袖章。
主和派及杨虎城均未深刻洞察严峻的形势,也未对少壮派采取防范措施,照常派李志刚前往潼关,准备与顾祝同签署协议,这等于火上加油,加速了少壮派走向极端的进程。
在得知李志刚即将前往潼关时,少壮派迅速调动部队一方面包围了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另一方面准备武装截留西安方面派往潼关的谈判代表,同时部署暗杀王、何的行动。
2日上午,应德田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处的名义发出《告东北军将士书》,表示:张副司令能回来,一切都可以谈,张副司令不回来只有拼命,用武力叫汉奸胆寒,迫使他们把张副司令送回来。
之后,应德田、孙铭久指挥总部卫队二营连长于文俊带一排人突然包围了王以哲家,于文俊手持驳壳枪,闯进王的卧室,对王以哲说:“军长,对不起你了。”随即连发几枪,将王以哲枪杀。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总部参谋长徐方等也同时遇害。
卫队二营副营长商亚东带领的枪杀何柱国的人马也赶到了何的家中,因何事先已闻躲进杨虎城的官邸,而死里逃生。
这时,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同样地闯进了几名东北军的少壮派青年军人。他们直奔周恩来的办公室,见来者怒气冲冲的样子,周很快明白他们的来意,非常气愤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周恩来义正词严的话,使这几名青年军官气焰顿敛,稍后他们一个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孙铭久赶到后,也跪地请罪。
但这已经晚了,王以哲被害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无法挽回的。它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导致了“三位一体”的解体。
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了,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信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线,驻渭南的部队当即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要为王以哲报仇。由于东北军过早地放弃了对“中央军”的牵制和阻挡,致使“中央军”长驱直入,乘虚开进渭南,继而向西安进逼。
孙铭久等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当杨虎城派人问他们如何自处时,他们都傻了眼。这时有许多人要杀他们的头,挖他们的心,来祭奠王以哲将军。2月3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3人经过彻夜商量,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3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
为了避免扩大事态,尽可能减少损失,周恩来当机立断,不避嫌疑,立即派刘鼎将孙铭久等几个为首者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同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杨虎城用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撤离西安。2月4日,在护送孙、应、苗离开西安后,杨虎城、于学忠敷衍故事,签发了通缉应德田等3人的通缉令。这样,就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从而也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周恩来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杀害了王以哲,但动机还是想救张学良,所以不能随便地牺牲他们。周冒着风险救了这3人,但这3人却没有以自己抗日立功的行动回报周恩来。孙、应、苗在云阳红军前敌司令部待了一个月光景,就离开了陕北,后来都走上了投日歧途。
就在少壮派3名首领离开西安的前一天,刘多荃擅自将渭南前线部队北移高陵,与缪激流部靠拢,让开了陇海线正面阵地,并派副师长高云鹏电话通知潼关的“中央军”樊崧甫,要他们提前进军。
接着,刘多荃派人捕杀了于文俊血祭王以哲;又令105师1旅3团团长葛晏春诱杀了该旅旅长高福源。高福源是张学良与红军沟通的第一个使者,于1936年被提升为少将旅长,并未参与“二二”暗杀王以哲事件。刘多荃和缪澂流还逮捕了所属团长万毅、康鸿泰和在东北军中工作的中共特派员邹鲁风,逼走了团长陈大章和营长王甲昌、商同昌等人。
在此前后,东北军骑10师檀自新部于2月2日在蒲城叛变,投靠南京方面,并扣留了陕西警备3旅旅长孙友仁、蒲城民团司令韩世本,缴了民团的械。2月6日,东北军106师沈克又叛离东北军,扣留了陕西警备1旅旅长王俊,将该部缴械。2月8日,陕西警备2旅沈玺亭、唐德盈两团投向刘峙,将部队拖向河南。
这些变化说明,“三位一体”已呈裂解之势。
2月5日,东北军将领撇开17路军和红军,由于学忠、何柱国、缪潋流、刘多荃等4名军长参加,在高陵召开会议,决定不再走与红军、17路军联合的道路,放弃甲案,而决定接受乙案。确定乙案的同时,对保留东北军总部也表现了不感兴趣,这意味着东北军将彻底分裂了。
尽管这一决定在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中仍有不同意见,后来张学良也仍然坚持应接受甲案,以保持“三位一体”的团结,但这位少帅已经无力左右他的部下了。因为在此前一天,即1937年2月4日,杨虎城、于学忠领衔7将领已经发表和平通电,宣布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并宣布了经与顾祝同谈判达成的四点协议:
1.在三中全会前,由委员长呈请国府,恢复张副司令公权,并发表职务,俾得自效:
2.陕甘军队部署原案,酌为变更,容纳此间切合实际之意见:
3.军队移防,除一部略变现实位置外,均俟张副司令返陕训话后,再行开始:
4.陕甘民众爱国团体,均仍旧维持,并对流亡人员,尽力妥为安置,以定人心,以备国用。(25)张学良只好让何柱国转告各部属:
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26)他还对王卓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