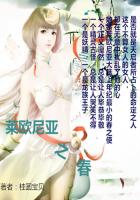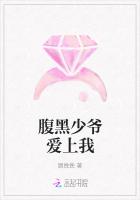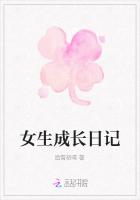保养精神,蓄积力量
水往低处流,当你的实力微弱、处境困难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受到打击和欺侮最多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采取忍耐的策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善于保存自己,作为忍的动力和理由。处于劣势的自己,要懂得保存自己的实力,寻找机会壮大自己。如果平时蓄积力量,在关键时刻自然就可以蓄势而发。
明朝的朱棣就非常善于忍耐和等待时机。明太祖朱元璋开创大明基业之后,为加强宗族势力,除了徐达等几个异姓人物外,把自己的14个儿子全部加封为王。明太祖驾崩后,因皇太子朱标早死,就由长孙允坟继位,即建文帝。建文帝一登基,即感到了10多位皇叔的威胁,于是他开始了大规模的“削藩运动”,把各位皇叔一个个剪除羽翼,有的流放,有的借机杀掉。最后只剩下燕王和宁王两个,因其环境特殊,又一时尚未找到借口,便暂时存留下来。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四子,他骁勇善战,也颇感自危,决意伺机行动,只是力量不足,只好暂时忍耐。建文帝也顾虑朱棣拥兵在外,又勇悍多谋,也不敢轻易下手。
不久,建文帝以高官厚禄收买了燕王的亲信葛诚,令他随时密报燕王的举止。葛诚就怂恿朱棣入宫见帝,以释嫌疑。这无疑是驱羊入虎口,朱棣的军师道衍力主不去,但朱棣却说:“此时我能兴兵,便当兴兵,若不能,不如暂往一行。”因此毅然进京。建文帝本想找个把柄乘机杀掉他,但燕王到京后处处谨言慎行,又显得十分驯顺,他反而无从下手。一个月后,他只好放燕王返回燕京。
京城一月,燕王察言观色,益感危机重重。回到燕京后,他立刻诈病,并传言病重。建文帝终不放心,又寻机把燕王所属劲旅调离燕京,并杀了他的几个得力部将。朱棣为使皇帝不疑他有变,便诈癫扮傻,甚而溜出王府,在街市上奔走呼号,抢夺酒食,说话颠三倒四,有时竟仰卧街头,整日不醒。建文帝派遣谢贵前击探病,当时,正逢盛夏天气,只见朱棣穿起皮袄,围炉而坐,还直喊天气太冷。但葛诚却密报朝廷,说燕王实是诈病,切勿被他瞒过。于是建文帝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密令燕京守城副将张信下手捉拿朱棣。
张信一直是燕王的亲信,接到密令后十分为难。他的母亲知道底细后,则劝他不可忘恩负义。张信就去见朱棣,朱棣仍在装疯。张信说:“殿下快不要这样。有什么,便对老臣直说无妨。”朱棣说:“我已经病得不行了。”张信便把建文帝的手谕拿出,以实相告。
于是,燕王急招军师道衍入室,共商救急之计。当晚设宴,预作埋伏,将谢贵及葛诚一并擒住。燕王朱棣愤愤地说:
“如夸在籍的普通百姓,尚且知道兄弟、宗族互相体恤;我身为皇叔,性命却朝不保夕。朝官如此待我,遍天下还有何事干不出来?”他扔掉手中拐杖,长叹一口气说:“我哪里有病,都是你们这帮奸臣逼出来的!”于是令人把谢贵等人斩首。朱棣随即起兵,直向南京讨伐建文帝。经过四年征战,终于获胜,登上皇位,定都北平。这就是历史上的明成祖。
评点
《周易?系辞下》中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在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要懂得隐藏自己的才华和真正的目的,等待不是一种退缩,不是一种服输,不是一种消极,不是一种被动,而是有心机之人的一种隐忍之道,是为了养精蓄锐,是为了伺机而起,是为了更有力地进取。
忍而不发,静候佳机
隐忍不发,等待时机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在敌对双方交战的过程中,双方的实力有时相差很大,处于弱势的一方,应该能忍,静下心来,等待时机。不要逞一时之气,贸然出击的结果,只会加快自己灭亡的步伐。等待,是一种意志上的磨炼。学会等待,就等于找到了通往成功的敲门砖。学会等待,才能在等待中走向成熟,在等待中找到机会,抓住机会走向成功。
公元221年,已经成为蜀主的刘备不顾将军赵云等人的强烈反对,出兵攻打东吴,以夺回被东吴袭夺的战略要地荆州(今湖北江陵),并为被东吴杀的关羽报仇。东吴孙权派人求和,遭到了刘备的严词拒绝。于是,孙权任命年仅38岁的陆逊为大都督,率领5万兵马迎击刘备的大军。
到了第二年初的时候,刘备的军队水陆并进,直抵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在长江南岸六七百里的山地上,设置了几十处兵营,声势十分浩大。陆逊见蜀军士气高涨,又占据有利地形,便坚守阵地,不与刘备交锋。当时,东吴的一支军队在夷道(今湖北宜昌西北)被蜀军包围,要求陆逊增援。陆逊却仍然坚持不肯出兵,并对众将说,夷道城池很坚固,粮草又充足,等我的计谋实现之后,那里自然就会解围,现在不必去救。
然而,陆逊手下的将领有意见了,他们见主将既不攻击蜀军,又不援救夷道,以为陆逊是个胆小怕战之人,都很气愤。众将领中有的是老将,有的是孙权的亲戚,他们不愿听从陆逊的指挥。于是陆逊召集众将议事,手按宝剑说:“刘备天下知名,连曹操都畏惧他。现在他带兵来攻,是我们的劲敌。希望诸位将军以大局为重,同心协力,共同消灭来犯敌人,上报国恩。我虽然是个书生,但主上拜我为大都督,统率军队,我自然应当恪尽职守。国家所以委屈诸位听从我的调遣,就是因为我还有可取之处,能够忍受委屈,负担重任的缘故。军令如山,违者要按军法从事,大家切勿违犯!”陆逊的这一席掷地有声的话,把众将领都镇住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不听从他的命令了。
陆逊打定主意坚守不战,时间长达七八个月。直到蜀军疲惫不堪,他利用顺风放火,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刘备大败,逃归白帝城,不久之后就病死了。
在忍耐中等待时机,陆逊取得了胜利。很多时候,忍耐不是畏缩,而是一种智慧。
郑庄公的母亲姜氏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就是庄公,老二叫共叔段。姜氏对共叔段特别偏爱,几次请求郑武公立共叔段为世子,武公都没有同意。
武公死后,长子霜生继位,是为郑庄公。姜氏见扶植共叔段的计划失败,便替共叔段请求庄公将京邑封给共叔段。庄公不好再推辞,只好答应了。
郑大夫知道后,立即面见庄公说:“分封的都城,它的周围超过300丈的,就对国家有害。按照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现在封共叔在京邑,不合法度。这样下去恐怕您将控制不住他。”
庄公答道:“母亲喜欢这样,我怎么能让她不高兴呢?”
大夫又说:“姜氏哪里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些想办法处置,不要使她滋长蔓延,蔓延了就很难解决,就像蔓草不能除得干净一样。”
庄公沉吟了一会儿,说:“多行不义者,必自毙。你姑且等待着吧!”
实际上,郑庄公的心里早已有了对付共叔段的方略。他知道自己现在力量还不强大,共叔段又有母后的支持,要除掉共叔段还比较困难,不如先让他尽力表演,等到其罪恶昭著后,再进行讨伐,一举除之。
共叔段到了京邑后,将城进一步扩大,还逐渐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据为己有。
公子吕见此情形十分着急,对庄公说:“国家不能使人民有两君的情况,您要怎么办?请早下决心。要把国家传给共叔,那么就让我奉事他为君,如果不传给他,就请除掉他。不要使人民产生二心。”
庄公回答说:“你不用担心,也不用除他,他自己将要遭祸的。”
此后,共叔段又将他的地盘向东北扩展到与卫国接壤。此时,子封又来见庄公,说:“应该除掉共叔段了,让他再扩大土地,就要得到民心了。”
庄公都说:“他多行不义,人民不会拥护他。土地虽然扩大了,但一定会崩溃的。”
共叔段见庄公屡屡退让,以为庄公怕他,便更加有恃无恐。他集合民众,修缮城郭,收集粮草,修整装备武器,编组战车,并与母姜氏约定日期作为内应,企图偷袭郑国,篡国夺权。
庄公对其叔段的一举一动早已看在眼里,并有防备。当他得知共叔段与姜氏约定的行动日期后,就命大将子封率领二百乘兵车提前进攻京邑,历数共叔段叛君罪行,京邑的人民也起来响应,反攻共叔段,叔段先是弃城而逃,后畏罪自系。他们的母亲姜氏也因无颜见庄公而离开宫廷。
评点
陆逊率领的吴军开始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他能够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忍耐的办法,在等待中寻找消灭对手的机会,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郑庄公和陆逊相反,他是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急于消灭对手,而是运用了“将欲擒之,先予纵之”的谋略,轻松地除掉了自己的对手。
等待机会,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的一种勇气,也是睿智的人的一种战略和策略。无论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要来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忍耐和等待是迈向成功之路的好办法。
天下之事,制之在始
古人常说要“慎始”,事情的开始对它以后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引导作用。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就制订了好的计划,考虑周全,那么,事情办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做事情一定要谨慎,对于那些不好的事情,一旦做过了第一次,就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那么后果就难以预料了。因此,我们必须要“慎始”,杜绝坏事的发生。
明代的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张瀚初任御史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参见都台长官王廷相,王廷相就给张瀚讲了一个乘轿见闻。说他某一天乘轿进城办事时,不巧遇上了雨。而其中有一个轿夫刚好穿了双新鞋,他开始时小心翼翼地循着干净的路面走,后来轿夫一不小心,踩进泥水坑里,此后他就再也不顾惜自己的鞋了。王廷相最后总结说:“处身立世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只要你一不小心,犯了错误,那么以后你就再也不会有所顾忌了。”张瀚听了这些话,十分佩服王廷相的高论,终身不敢忘记。
这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人一旦“踩进泥水坑”,心里往往就放松了戒备。反正“鞋已经脏了”,一次是脏,两次也是脏,于是便有了惯性,从此便“不复顾惜”了。有些人,起先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偶然一不小心踩进“泥坑”,经不住酒绿灯红的诱惑,便从此放弃了自己的操守。这和俗语“破罐子破摔”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不慎而始,而祸其终,这道理谁都明白,但要做到“慎始”似乎也很难。一些人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会设置种种陷阱,包括利用“糖衣炮弹”来百般诱惑,让你“湿鞋”。在莫泊桑的小说《小酒桶》中就有这样的事例。女主人公马格格瓦,将其田庄以每月250金法郎至她寿终的价格卖给一个叫汲可的老板。汲可为了让她早死,想出一条诡计:办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拿出“十足的陈酒”白兰地,请马格格瓦做客。原本滴酒不沾的马格格瓦,在汲可连劝带哄下终于连饮三杯。此后,汲可又常给她送酒,使她染上了酒瘾,终于在一天晚上醉到雪地冻死了。
这不仅是小说中的故事,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人。有的人以“就干这一次”为托词原谅自己。还有一些人,开始时并不认为事情程严重,觉得占点小便宜,捞点小外快,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殊不知,如此慢慢地放松了警惕,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旦醒悟,却已不能自拔。
评点
欲善终,当慎始。无数的教训告诉人们,把好第一关,守住第一道防线,是十分重要的。苏洵《上文丞相书》中说:“君子慎始而无后忧。”
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开个好头,需要很多因素。因此,任何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就要认真地去对待,做好计划,从一开始就要全身心的投入,为自己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无论是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各种强大的对手,这就难免产生激烈的竞争。要想脱颖而出,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讲究一些方式方法。其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是最有利的武器之一。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各自为政,给朝廷造成很大的困扰。而在各个藩镇中,淮西又是最顽固的一个割据势力。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去,他的儿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认为有机可乘,遂发兵征讨淮西。但是他派去的统帅,不是腐朽,就是自己另有企图。结果,花了整整三年工夫,费了大量财力,还是没有征服淮西。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大臣都认为不能再打下去,否则只会劳民伤财。唯有大臣裴度却认为淮西好比身上长的毒疮,不可不除。于是,唐宪宗拜裴度做宰相,决心继续征讨淮西。
公元817年,裴度向唐宪宗推荐了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李愬。唐宪宗十分高兴,便派李愬担任唐州(今河南唐河)等三州节度使,要他进剿吴元济的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此时,唐州的将士已经打了几年仗了,都不愿再打,听到李愬一来,有点担心。不料,李愬刚到唐州,就当众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派我来,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打吴元济,不干我的事。”
消息很快传到吴元济那里,吴元济打了几次胜仗,本来就有点骄傲,听到李愬不懂得打仗,更不把防备放在心上了。此后,李愬一点不提打淮西的事,仿佛完全忘记了自己肩负的任务。唐州城里有许多生病和受伤的兵士,李愬就一家家上门慰问,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将士们都很感激他。
有一次,李愬的兵士在边界巡逻,碰到一小股淮西兵士,双方打了一阵,唐军把淮西兵士打跑了,还活捉了淮西军的一个小军官丁士良。丁士良是吴元济手下的一名勇将,经常带人侵犯唐州一带,唐军中很多人都吃过他的亏,非常恨他。这一回活捉了他,大伙都请求李愬把他杀了,给死亡的唐军兵士报仇。
但李愬却只是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当将士们把丁士良押到李愬跟前时,李愬却吩咐兵士松了他的绑,好言好语问他为什么要跟吴元济闹叛乱。丁士良本来不是淮西兵士,是被吴元济俘虏过去的,见李愬这样宽待他,不由得十分感动,很快就投降了。
不久,李愬靠丁士良的帮助,打下了淮西的据点——文城栅和兴桥栅,先后收服了两个降将,一个叫李祐,一个叫李忠义。李愬知道这两人都是有勇有谋的人,就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跟两人秘密讨论攻蔡州的计划,有时讨论到深更半夜。李愬手下的将领都很不高兴,军营里更是传得沸沸扬扬,都说李祐是敌人派来做内应的。有的还有凭有据地说,捉到的敌人探子,也供认李祐是间谍。
李愬虽然信任李祐,但他怕这些闲话传到朝廷,一旦唐宪宗信以为真,自己要保他也保不住了。李愬反复考虑了一番,就向大家宣布说:“既然大家认为李祐不可靠,我就把他送到长安去,请皇上去发落吧。”
于是,他传下军令,把李祐套上镣铐,押送到长安。与此同时,他又秘密派人送了一道奏章给朝廷,说他已经跟李祐一起定好攻取蔡州的计划,如果杀了李祐,攻蔡州的计划也就吹了。唐宪宗得到李愬的密奏,就下令释放李祐,并且叫他仍旧回到唐州协助李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