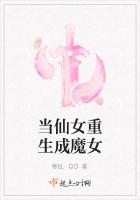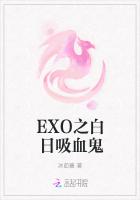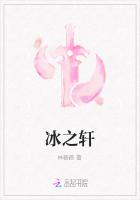曲折攀登道路岐,步履荆棘迎朝曦。柔姿不限盆花艳,风邪未肯把头低。他的心里有了这种意境,笔下也自有了一种前人未有过的神韵,从花的自然性属中,挖掘与自己的心境相通的哲理性内容。齐白石也画过牵牛花,他是用一种圆型结构来处理花瓣的,他觉得这种画法也许是反映了白石老人当时的心境。他觉得这种画法,抒发不出自己内心感情,就用浓浓的五笔把花形勾出,再用浓墨画上攀援的枝叶,于是他笔下的牵牛花独具一格,出现了一种自然质朴之美。有一首五言律诗体现他画牵牛花时怡然自得的心境:自无一寸地,种籽瓦盆达。朝夕勤浇灌,无须雨露沾。插竹为梁架,引蔓南窗前。看花且画花,心诚天地宽。从此画牵牛花成了他的一手绝活,海内外知名。一次在香港展览时,观者争购。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也得到一幅他画的牵牛花,看了画和画上的题诗,立刻联想到自己不平坦的仕途,还和夫人齐心说:“这张画画得妙极了,真正道出了我自己的心情,方便时请画家到家来,我请他吃顿饭!”
有一次他和花鸟画大师朱屺瞻相遇,朱老的一番话让他永记不忘:“我画画从不赶浪头,你喜欢,我这样画,不喜欢我也这样画,你展览我这样画,不展览我也这样画,永远追求自己的风格”。严格地说,王天一专攻花鸟画是从牵牛花开始的。方向确定后,他就广泛向卓有成就的老画家们请教各种花卉、鸟禽的意境和技法,在这方面他受到了何海霞、许麟庐、李苦禅、关山月、黄胄等大师的悉心指教,他领悟到一幅好的花鸟画,不仅在技巧上是高超的,而且作为形象的再创作也是美的。画一幅好的花鸟画,需要对花和鸟,不但在形象结构上熟悉它,而且要对花和鸟经过观察有所感受,寄画家之感情,表达人的理想和愿望。如画松意在高洁不屈,画梅花之冰肌玉骨香艳寒冬,画菊则呕歌其傲霜精神,画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画牵牛花的朝气蓬勃。所以画花鸟画都是以美的理想去表现和歌颂人们的精神面貌的,即所谓画花鸟画也是画人。
为了画好牵牛花,他在外出采风时,总是细心观察各地的牵牛花,比方有些地方把牵牛花叫做勤娘子,意在它能鸡鸣即起,催促人早早开始一天的劳动;有的地方又叫喇叭花,也有花催人勤奋劳作之意。牵牛花虽没有牡丹那样富丽,也没有菊花那样高雅,更没有兰花那样芳香,但它那种顽强向上,努力攀登的精神,令他十分神往。牵牛花能自荣自枯,不择环境而生存,不怕荆棘,越开越高,到了深秋枝蔓已枯萎,但仍在顶部开花,不被西风吹落。这种习性恰恰印证了他的强烈人生。
唐诗中有:“寻芳独立小篱边,翠蕊盈盈抱露鲜,最爱山村秋晓后,花光遥映蔚蓝天。”诗中描写蓝色的牵牛花辉映着农村秋天早晨晴朗的天空。
恽寿平也有词曰:“颜如龙胆,花号牛郎,抽毫借织女的机丝,炼药乞神农的灵草”。把牵牛花和神话里勤劳勇敢的牛郎星联系在一起。牵牛花不仅有红色的、蓝色的,还有紫色的、粉色的、白色和黄色的、红花白边的。在美国和日本另有一种矮牵牛花,花形与中国北方相同,不抽蔓,可以栽培在花盆里,且花整天不衰。在广东一带有一种叫五爪金龙的牵牛花,非常茂盛,它能攀援高大的树木直达顶尖,有时把树枝都能压弯。经过这样的观察,他对多种牵牛花的习性和特点,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牵牛花产生了深刻的感受,他的笔墨和敷彩技巧,渐渐达到得心应手的境地。
王天一的牵牛花曾多次参加国内各地的画展,引起许多观者的兴趣,有的重金选购,有的向他索取,有一位远在海南岛的不留名的朋友写来一封言词恳切的信,求他画一张“蓝色牵牛花”,他要挂在床头,永远砥砺自己。王天一深知这位朋友的心情,就连夜画了一张四尺对开的蓝牵牛花寄给了他。20年前,我们在藻鉴堂相遇时,恰逢《人民中国》日文版的好友准备赴日访问,他也作了几张牵牛花作为礼物,送给日本朋友。牵牛花在日本叫作“朝颜”,也是一种日本人喜爱的花,日本朋友得到此画后皆交口称赞爱不释手,东京的中国画研究中心的负责人藤山纯一先生是个“中国画通”,他拿到后远看近看赞曰:“这是中国新一代花鸟画家的画作,将来一定要邀请王先生到东京来办展览”。当然画牵牛花只是他花鸟画的一个突破口。
马兰慈
80年代初,王天一分得一小间陋室,他打算略加改造后变成一间画室,并给它起个名字,想了好久,也没想出一个中意的。一天,画友兼恩师许麟庐来访,他陪同去敦煌参观,回来的路上许麟庐见他煞费苦心的样子,就问他:“天一啊!有什么心事?”王天一告知原由,许老听了哈哈大笑,指着路边草丛中钻出的一簇簇马兰花说:“这种花的生命力极强,不怕寒风吹,不怕雨雪打,与你的经历很相似,何不以它命名?”王天一听了心里一亮,高兴地说:“好,只是叫马兰什么呢?”许老听了说:“叫斋啊、轩的都不好,你如今只是工人宿舍中的一间陋室,比茅草屋强点,莫如叫‘篯吧,镓是竹屋的意思,你目前的境遇,叫个‘马兰镓就挺好!”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许大师的一席话,就把画室的名字定下来了。
此前,王天一可以说是居无定所,长期在无尽的折磨中飘泊、动荡,现有的房子还是靠老伴张帆的努力,在她工作的工尸的工人宿舍中争来的。家里有七口人,一个老岳母,妻子和三个孩子,小舅子,挤得满满当当,根本没有作画的地方,如今有了一间画室,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回家以后,他立刻操起画笔画了一幅马兰花附诗一首,诗曰:
马兰生路旁,自枯亦自芳。春风花影动,疑是蝶寻香。画后他使用新名字马兰篯主。
小小的“马兰籙”不但成就了一代花鸟画大师,而且使王天一一家都成了画坛的后起之秀。
王天一的大儿子王大平自小是一个残疾人。生下来的时候不聋不哑,后来因王天一夫妇都参了军,随军南下时把他托付给老家的农民家,不久,就接到家乡的信,说孩子病了,高烧不退。王天一急忙请假回乡,把孩子抱了回来,到医院一查,说是得了脑膜炎,以后就成了不会说话的聋哑人。这孩子随他父亲又倔又犟,小时候有人欺负他,就跟人打架,在父亲遭殃的年代里,母亲无可奈何,就想了个狠主意,上班时就把孩子反锁在家里,孩子闷在屋里,母亲给他纸、笔让他画画,大概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到了上聋哑学校的时候,居然画得似模似样,上学以后仍然热衷于作画,王天一起初自顾活命并不赞成儿子再走这条路,妻子张帆说:“大平是聋哑人,难得有些爱好,总比上街惹祸好!”孩子虽然又聋又哑,却天资聪明,学得也很专心。以后当了工人还给厂里搞宣传,不久赶上文革运动,他也参加了革命造反,有一次对立面造反派说,王天一是反革命,你也反对毛主席,他一气之下,把毛主席的像章别在胸前的肉上,以表示他如何忠于毛主席。聋哑儿子文革后在省残疾人联合会当美术编辑,俨然成了一个画家,画的画居然能拿到市场上卖了。他曾是全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主席团委员、甘肃省聋人协会的副主席,成了兰州市里小有名望的人物。
老二叫王亚民,也是自小跟美术有不解之缘。中学毕业后,曾插队劳动,后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考入了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后不满足,又考入四川美院油画系进修,现在是上海一所学校的副教授、上海美协会员,作品参加了上海市油画作品展览。爱人郭光,同济大学毕业,建筑师,也在上海工作,爱好绘画。
最小的老三王少平也曾插队劳动,他也爱画,回城后在工厂里搞宣传,他作画虽不成功,但他却从王天一那里学会了另一种本事,美术设计,广告、展览都搞过,工厂不景气,听从父亲的主意,在兰州开一个小画廊,卖父亲和其他知名画家的画,除此,他还对青铜器、彩陶、字画的鉴定有所研究,看些美术书籍,也算是沾了美术的边。
他们的孙女也是在“马兰篯”降生的。大儿子生有一女一男,女儿是奶奶抚养大的。孙女自小聪明好学,受祖父母的影响,也酷爱画画,现在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她的画也参加过省上的展览。她找了个伴侣,是兰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美术设计。孙子王廓,老二的儿子,上中学,美术作品参加了天津主办的全国青少年美术作品大奖赛,还得了第一名。
现在“马兰篯”的主人王天一可以说是美术世家。“马兰篯”的女主人张帆,早年因为热爱美术才跟王天一结的婚,但老伴的命运却使她大半生处于苦涩的生活之中,尝尽人间的艰辛,等把儿子和孙女都拉扯大了,她的青春年华巳过,但她没有灰心,退休以后,才拿起了梦寐以求的画笔,多年在王天一的熏陶下,她对绘画并不陌生,虽是“马兰录”最后一个拿起画笔的人,却进步神速,画起来竟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画得入迷,忘了吃饭。王天一只好自己下厨把饭菜做好,冲屋里大喊:“老太太,快来吃饭!”吃着饭,还打趣地跟老伴说:“怎么样,咱俩换换班吧?”张帆画画追求的是另一种风格,王天一问:“你为啥不画牵牛花?”张帆把嘴一撇说:“我不跟在你的后边学步呢,免得人说‘马兰镓的女主人是王天一手把手教出来的,人家不相信画是我画的。”退休十多年的工夫,喜欢画鱼和猫,画得很扎实,如今张帆的画已经达到了展览的水平。
“马兰篯”还帮助培养了不少美术新秀。帮助过不少的年轻人,不过也是良莠不齐,最让王天一伤心的他有一个来自农村的徒弟,自己找上门来,当时他是农村户口,一家人吃饭还得给生产队补交120元钱,王天一当时生活也很困难,硬是给他凑足了钱交到队上。渐渐入门以后,一家工厂把他招工到厂里当了美术工,后来又调到兰州某个单位,得到老师不少帮助。他小有成就以后,就自吹自擂起来,到处打着王天一旗号招摇撞骗,说什么:“我是王天一的亲授弟子,我的牵牛花比老师的还棒,我画的驴胜过黄胄!”还说他是“中国第二黄胄,中国第一驼”。整天自封画家在市面上混。前几年过春节,他到“马兰镓”给老师拜年,师母见了批评一顿赶出了家门。还有个别学生追求荣誉地位,断了奶头忘了娘,在背地不认老师。王天一说:学生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他以为人品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帮助过的学生多数人品都很好。
艺术馆
王天一夫妇都眷恋自己的故乡,地处嘉陵江上游的成县,是个民间工艺之乡,曾有过民间泥人作坊。他们曾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家乡办个泥娃娃工厂培养人才,使乡人走致富之路。两人在兰州和其他地方收集了半箩筐泥人造型,分两次运回故乡,终因资金和人才无着,泥娃娃躺在文化馆的库房里成了废品。后来王天一跑到省里跟省委书记提出在陇南成县利用自然资源办个工艺美术中专以培养人才,这个主意省里同意了,采用土法上马的办法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办成。他热爱他的家乡,总想给家乡办点实事,他想给自己的故乡留下更多的东西,办一座“天一艺术馆”,给乡里添一道有文化品味的风景,但这又谈何容易,建一个艺术馆需要一大笔资金,国家出是不可能的,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办成这件事。说起来王天一这些年除了绘画,已经帮别人建了好几个艺术馆,他帮助了中国画研究院建院工作,又帮助黄胄操持过“炎黄艺术馆”,在甘肃还筹建了甘肃画院。就连成县的同谷书画院也是经他策划的。当然这些都是国家出钱,他只能出智慧帮助作策划,不管怎么说,跑前跑后,他是为美术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的广东旅游局听到西部有个画家王天一有很高的画艺,请他们夫妇俩到广州、深圳、香港去搞展览,卖出所得共二十七万元,有了这笔钱后,他的心动了,不过,这时他和老伴的想法有点不一样,按老伴的想法是:一辈子在坎坷中作画不易,兰州的住处也不理想,也没有解决,再说她看到这里斗过他的人心里总觉得害怕,莫如在自己的故乡,建个四合院,两个人以后可以回到家乡颐养天年,死后,儿孙们也有个去处。孩子们也都赞成母亲的主意。王天一的想法却是,用这笔钱修一座艺术馆好,他完全没有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意思,想到的是,一是可以把自己毕生的画作留给故乡;二是希望这个艺术馆能成为成县的一个小小的文化中心,能为繁荣本土文化和艺术创作,促成一个学习和交流的空间;三是他希望这里能使更多的有志于绘画的青年,在这里受到美的熏陶,得到美的情操的启发,使家乡真正成为一个绘画之乡!他的这些理由终于说服了家人,跟县里一说,县里自然是双手赞成说:“你这是为成县干好事,地皮没问题”。不想工程上马后,土地并不是无偿的,材料也要花钱,卖画的二十七万全搭进去刚够搭个主体框架,这就使王天一背着画具到处去化缘,以画换钱。期间也得到县上、地区和有关同志的支援,又凑得了二十万总算把主体工程建完了。接着又建了小花园和长廊、花亭,总共用了六十多万终于把艺术馆建成了。现在集展览、收藏、交流为一体,已免费参观开放三年了。
艺术馆建在成县的南门外,占地二亩,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二园联成一片,开幕剪彩那天,省里、县里来了许多贵客,王天一在会上吟诗一首:
七十年岁不稀奇,风雨行舟一瞬息。一生光阴真无悔,半世折磨实可悲。而今庆幸开庆典,高朋亲人笑满席。再盼春秋二十载,发奋丹青不服低。大家听了都唏嘘感慨不已。小孙子望着爷爷两鬓的白发说:“爷爷建这座艺术馆把头发都建白了!”老伴说:“这是王天一一辈子的心愿,我们死了也带不走,儿孙们将来也不一定回来住,只求它成为成县的永久纪念物,也算是成县没白养育了她的一双儿女!”
王天一现在全部帽子都已经摘掉,恢复了真党员的面貌,原来的政协委员和省画院副院长头衔都已经退掉,成了真正的“自由身”,不过他的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美术家协会会员、甘肃文史研究馆馆员都一直保留着。他说:“我先天不足,后天亏损,肯定不会成为大画家的,不过我还不会放下画笔,只要一息尚存,我还要画下去!”
他常到天一艺术馆走走,画画吟诗,怡然自得,这次来京时跟中国美术馆馆长杨力舟互相约定,“80岁时将在中国美术馆开一次大师级的画展!”
2000年冬日完稿于北京
【注】鲍文清《中国建设》高级记者、着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