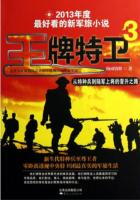他布置完后盘腿坐在草地上,望着一片“哞哞”叫的牛群、咩咩叫的羊群,得意地嘿嘿笑出声来。这是他得到战利品最多的一次。他发现,到草原上,掠取财物,很容易得手,而且是大批大批的。看那杨团长,在牧区几年,富得流油,调防他还不愿意回去,原来这里面有名堂。把这些牛羊献给马主席可以邀功请赏。他又把双手枕在脑后欣赏着自己的战利品。几天来,绷紧的神经一下放松了,这个刽子手,像死尸一样,平展地躺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直到勤务兵把他扶进了扎好的帐篷,端上了刚出锅的鲜嫩羊肉,递上烧酒,这刽子手才恢复神智,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和部下们淫荡地品论着抢来的女人……
囚禁妇女的帐篷一隅,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呼唤,“久美……久美”。马海龙怀里的小男孩带着哭腔挣脱他,朝叫声跑去。马海龙紧随其后,知道这里有小男孩的亲人,或是亲戚、熟人,同时,马海龙知道了这小男孩的名字叫久美,让卫兵把久美放进去了。
酒足饭饱后,当然就是思淫欲,他们肆意蹂躏妇女,大发兽性。女人们的哭喊惊叫响彻夜空。
马海龙从这群强势野兽和弱势羔羊的撕扯中,抱着久美离开了暴行之地。
深夜,匪兵们都昏昏睡去,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反而让人觉得安静,哨兵们已习惯从狗断断续续的叫声中,判断是否有危险。有时嫌它们叫的无聊,放松了警惕性。
其实,尕尕的人马已经赶来了。离得不远时,他让队员们下马,马蹄上包上毛毡,牵着马悄悄靠近,然后突然袭击。起初狗是听到了动静吠叫,随着越来越近的人马靠近,狗已经嗅到了主人的气味,断断续续地叫着,在召唤主人。是啊,哪有不认主人的藏獒,藏獒的品质就是对主人的绝对忠诚。所以哨兵被狗的忠实品德迷惑了。他们认为最安全的时候危险已降临了。
可见危险和安全是相对的,危险和安全总是相辅相成。这不是吗?平安中潜伏着危险,危险又存在于平安中。同切部落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变成了危险的绝境,而匪兵们又想从狗叫声里判断出来平安,偏偏是危险降临的预兆。
离目标只有50米时。尕尕一声令下:
“上马冲杀进去!”
营地被这突如其来的人马杀得乱了方寸,晕头转向,一时难以招架。尕尕的人马趁机赶上牛羊,抢回妇女快速撤出。
狗叫得更凶猛,仿佛是在为主人助阵。尕尕命令手下的一人:“快去!把拴狗的绳子都给我砍断。”
匪兵们在夜里辨不清方向,不敢轻举妄动。等到天亮,马师长清点人数,发现死伤三十多人,所有的战利品顷刻间失去了,就连那几条藏獒也随主人跑了。马师长垂头丧气。直叫喊:
“这些番子,简直是反了,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天亮后,马师长才组织人马去追击。
尕尕重新调整部署了计划。他召集部落的人开了最后一次会宣布了决定:
“整个部落一起撤离,行动缓慢,匪兵们很快会追上来的,为了给部落撤离创造更多的时间,我们组织人马,在匪兵追来的路途中,安置人员,一路进行阻击,占据险要的位置,边打边撤,依次转移到下一山头。妇女小孩赶上牛羊,径直撤离。”
他们与马师长追来的人马,打了两天两夜的阻击战。大家估计部落撤离走远了,准备撤出。可打红了眼的尕尕,想诱敌深入,过把瘾,痛快地打最后一仗,多杀几个匪兵,以报血海深仇。队员们也情绪亢奋,赞同尕尕的决定。
再勇敢的人,战术思想落后,就注定是失败者,尕尕是很勇猛,可这不能抵挡凶狠的对手。
他们把匪兵诱进了一个大山谷。这个山谷两面山势高峻险要,乱石穿空。尕尕选好地势,让人埋伏在两山的半腰。等到马师长的人走进沟里,他们开始从山上滚石头来阻止前进。等到马匪们爬上山坡,靠近些时,他们瞄准射击,展开了激烈的交战,双方伤亡过半。
太阳落山时,马师长命令他的人马撤出山谷。他像一头咆哮的熊,让传令兵把巴吾找来。巴吾战战兢兢地挪来了:“马大人,什么事?”
“你想想看,除这条沟,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追上部落。”
马师长最怕的结果就是部落出走。
马师长边说边把手里的马鞭甩在石头上。巴吾一看这情形,抖抖颤颤地走向前,小声地说:
“马大人,恐怕部落已经追不上了。”
“那你想想看,有什么办法,把尕尕收拾掉,我看他已经弹尽粮绝了,又没有后援,活捉这家伙有可能吗?”
马师长说完瞪着他那双鼓出来的金鱼眼,急切地等巴吾说出计谋。
巴吾看看四周,又献计说:
“马大人,我带一部分人绕个大圈,从东面翻过山,再到南面,把他们的后路断了,天亮后你们往前赶,我从后面包抄上去。看他们往哪里跑。”
马师长点头说:
“好,就这么办。”
叫过来一个下属交代说:
“尕祁连长(尕,青海方言,小的意思),带上你的人马,跟这番子去。”
巴吾惘然地看着马师长的嘴,他听不懂马师长说什么,他猜想马师长对他不信任,才让祁连长跟着。他心里不是个滋味,认为自己就是人们常说的夹在两块石头中间的手——左右为难,两边都不讨好。
尕尕这边,也看到了形势的危机,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他让伤员和一部分人撤离,去追赶部落,并作了交代:
“如果我冲杀不出来,部落继续向西藏方向撤,西藏那边日子不好过,就回来投奔其他部落里,但我们同切部落的人绝对不要去郭麻部落,饿死也不要投在他的部落里。我有言在先,也算是遗言吧,谁去投奔就杀谁,你们代表我执行。”
离去的人们把自己的食物袋子留了下来,趁夜色下山向南追赶部落去了。
拂晓,有人惊呼,向尕尕报告说:
“头人,你看,我们的退路没有了,这些魔鬼从山后包抄上来了。”
尕尕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退路会被截断。
尕尕跑到山头一边,只见后山坡上,敌兵像散落的牛粪缀满山坡,已经爬到了半山腰。他一看此情形,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对身边的人说:
“我没有像活佛那样的先知,没有像狼那样灵敏的嗅觉,才走到了今天的绝境,没想到对手会来这么一招。”
“没有退路只有用命拼死。”这在在场的人们的回答。尕尕巡视了一遍在场所有人的面孔,低沉地说:
“与虎狼厮杀吧,胜输听天由命,生死由神来定夺,大家投入战斗,像个男子汉,膝盖不能软。”
有一个小伙举着右手喊:
“头人,放心吧!我们的牛羊肉不是白吃的,我们从小穿梭在大山峡谷的胆量不是白练的。”
“好!来世我们还是做头人和属民。”
这是尕尕说的最后一句话。
尕尕说完,直接走到山头的制高点,搬动身边的石头,堆起来,作为武器。人们散开了,各自找到位置,在做准备。
又一场激战拉开了,子弹打尽了,就地取材以石头做武器。
这石头是最具杀伤力的冷兵器。滚下的石头,弹起来飞得很高,又落到坡面,碰撞飞溅起火花,冒着青烟,伴着轰鸣声,飞奔而下。下面爬上来的人躲避不及,伤腿伤胳臂,甚至有脑袋开花的,死伤几十个。可他们手里的武器比石头利索。子弹不长眼睛,可它要你的命,你看不到它,它喜欢往你身子里钻。
山上的人一个一个倒下了。
山下的人疯狂地扑上来了,尕尕的人挥刀冲出掩体,与追兵们展开了肉搏战。
尕尕的人马受到两面夹击,巴吾带领的人已经从山背后爬了上来,截断了退路。
尕尕是在上山无道、下山无路的情况下,被巴吾和上来的人死死围住生擒了。
巴吾上到山头,看见尕尕喊:
“流浪人,你无路可逃,投降吧!”
“我是没有退路的狗,到最后也要龇牙咧嘴对待你们。
尕尕边说边直径冲向巴吾,满脸的凶狠吼道:
“老狗。来吧!”
尕尕与巴吾都手持长刀搏斗,跟上来的匪兵,围上来七八个,有的抓住尕尕的胳膊,有的抱住尕尕的腿,撕扯一番后,尕尕被抓住了。他身上却吊着二群累赘。
尕尕对得意的巴吾说:
“你这条老狗,里外不分,朋友和敌人认不出,远近不会丈量,善恶浊清不会分辨,你枉做了佛的信徒,你的双手已经沾满了血,我想,你的下半辈子不会好过。”
巴吾走上前揪住尕尕的头发说:
“流浪人,你想做头人,做不成了吧?百户是你当的吗?屁股还没坐热吧!就要没命了。”
巴吾的这些话,刺激了尕尕的神经,刺痛了他的心,是的,尕尕的目标刚实现,身份刚被认可,地位和权力刚抓在手里,却遭此一劫。
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怒火攻心,挣脱那七八个人的束缚,一拳砸在了巴吾的嘴上。巴吾的两颗门牙飞得不见踪迹了,他忙捂着血乎乎的嘴含含糊糊地喊:
“把这个流浪人捆起来。”
祁连长拔枪对准尕尕。
尕尕轻蔑地看了一眼对准的枪口,继续训斥巴吾:
“我不是输给了这些人,而是输给了你这样袖筒里的虱子,我的心就如冰块一样凉。谚语说得好,蚂蚁走多了会粘死在树脂上,青蛙蹦高了容易受伤,我是走多了路的蚂蚁、蹦高了的青蛙,命该如此。可是,你怎么与魔鬼打起交道来,杀起无辜的人来心狠手辣,葫芦宝地的惨案一半的罪过由你背负吧,你的良心被天狗吃了,他们是刽子手,你就是攥在他们手里的杀人刀,你的罪过还小吗?即使堕入十八层地狱也便宜你了。”
听到这些话,巴吾嚣张的气焰没有了,也没有还口,喘息的粗气也慢慢地平复了下来,眼睛不敢正视尕尕,只是一只手捂着脸,一只手垂着,吐着满口的血水。
被俘的同切部落的人有二十多个,他们拒绝投降,被枪杀了。
马师长在五花大绑的尕尕身边背着手转来转去,拖着大马靴,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脚步声由重变轻,由轻变重。可见,尕尕着实让他感到恼火。
不是吗?部落跑了,他在马主席面前难推其责。人马损失不少,这与他原来预想的结果相差甚远。尽管他是活捉了头人,可他心里很清楚,他没有赢,真正的赢家是尕尕。
尕尕让部落成功出逃了,这是他最大的失败和最大的失误。让他感到沮丧恼怒的原因还有,到手的财物失去了,再也捞不着,煮熟的鸭子飞了。他那张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像充了气的皮囊膨胀着。
尕尕率领部落顽强抵抗的方式,在草原上会成为仿效的样板,部落出走,头人举旗对抗,对马步芳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马师长瞪着尕尕,对通司说:
“告诉他,叫他投降,把出逃的部落叫回来,向郭麻头人学习,郭麻头人是与政府合作的榜样,好好给马主席进贡、纳税。想同我们对抗,打得过么?不就是今天这个下场。”
通司逐字逐句翻译给了尕尕。
尕尕说:
“要砍要杀随你们的便,投降,在我的人生信条里还没有,你们就别费心思了。离弦的箭能回头吗?冲出牢笼的鸟能飞回来吗?向东流去的水头能逆流吗?逃离虎口的人能再入虎穴吗?你们白日做梦吧!”
说完这话以后,尕尕从此变成了哑巴、聋子。他自己不说话,也不听别人说话。
马师长怎么劝降他都不应声,软的硬的手段都使尽了,气得马师长围着尕尕转来转去。最后,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
“你的狠劲哪去了,这会儿装聋卖傻,我要把你的铁嘴钢牙撬开,等着瞧。”
尽管马师长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可他心里很憋气,这个蛮横的强盗有极强的报复心理。他要的是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战果,要的是顺从恭敬的藏民,而不是牙齿碰牙齿的结果,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这种不屈服的反抗使他受到羞辱,更激起了他的凶残报复欲望。部下的话激起了他的报复灵感。
“师长,这次我们损失太大,什么也没捞着,就这么空手回去吗?”
马师长想了一想,同切部落的属地上就只剩两座寺庙了。他对祁连长说:“尕祁,跑的跑了,杀的杀了,你说还有什么?”祁连长诡秘地说:“师长,不是还有两座寺庙吗?你又不是不知道,藏族的寺院是个聚宝盆,我们捞一把去,还有一座尼姑寺院。”
他往下不说了,众人都会意地相互看看,脸上挂着淫荡的笑容,凝固了几秒的空气,一下被哄笑撕裂了。空气里又飘荡起血腥味,风里暗含着杀气。
寺庙的和尚早就听说这些人的凶残和野蛮,他们做了积极的备战工作,寺院墙上挖了枪眼,加固了大门,准备好了几天的粮食,背好了能喝几天的水,拿起武器,严阵以待。
巴吾一看马师长的人马要去洗劫寺庙,想劝,又没有胆量劝阻,不满还不敢表现出来,但惊扰佛门的事,他绝对不参与,怕惹上坏名声或遭到佛的惩罚,他找借口说身体不舒服,胆囊炎发作,回去找活佛看病。
马师长心里也清楚。这些藏族人对寺院从心里到骨子里充满了虔诚和敬畏之心,带上反而碍手碍脚是个包袱。况且在找葫芦宝地和捉尕尕两件事上,他立了首功,就同意了巴吾先和民团带上伤员再派了他手下的一些人,还有带着娃娃的马海龙也跟巴吾一块押着尕尕先回去了。
马师长望着离去的巴吾一队人马,对祁连长说:
“马主席以番制番的手段就是高明,不是这个番子,我们跑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是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睛,能办成啥事。”
匪兵们闯到寺院,停在山脚下向寺院喊话:
“让你们的寺主下山来见马师长,我们师长有话要对他说。”
他们本想把寺主诓骗下来,挟持寺主以令和尚们不要反抗,束手就擒,想在不受到任何反抗的情况下,顺手牵羊,轻易地掠取寺院的财物。
全寺和尚知道,活佛去了凶多吉少,老管家再三阻拦活佛别出寺门。
“活佛,您千万别去,这些畜生不讲信用,凶性残暴,杀人如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您千万别出去,难道我们被杀的人还少吗?您要出去,就是白白送死。”
众和尚跪下也再三哀求:
“您千万别出去!”
寺主说:
“如果我出去,杀我一个人,能免去寺院的血光之灾,也算我为寺院修得圆满功德,万一我遭到不测,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报仇,这是他们的圈套,他们到寺院的目的,就是冲着这些法器和文物来的,大家关好门就待在里头。”
说完活佛整了整袈裟,把多余过长的袈裟摆甩在肩头上,从容地出门向山下走去。
马师长对通司叫喊:
“告诉他,让和尚们打开寺庙迎接我们进去,向我们投降。”
活佛说:
“佛门是净地,怎么容得你们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踏进禁地,玷污了圣地,我拒绝你们进入寺庙。”
马师长骑在马上,瞪着他那布满血丝的金鱼眼睛说:
“尕祁连长,给这个佛爷喂给一颗子弹,送他上西天。”
祁连长顺手举枪对准活佛的心脏扣动了扳机,活佛饮弹倒地。
马师长从马上下来,绕着活佛的尸体高声喊:
“佛爷不是神吗,刀枪不入,怎么只吃了一颗子弹,就爬不起来了。起来呀!起来呀!”
匪兵们围着活佛的遗体发出阵阵的哄笑。寺庙的和尚从了望孔里看到了这一切,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寺主,他们强压胸中的怒火,化悲痛为力量,在老管家的带领下,和尚们忙把寺庙里的主要佛像、法器埋起来。他可是在葫芦宝地亲眼目睹过这些恶魔对待财物的贪婪,掠去财物采用的手段之残忍。他催促和尚们抓紧时间埋财物。
在老管家的指挥带领下,众和尚有条不紊,分工明确,紧张有序地挖坑、搬运、埋藏,看着走近寺院的匪兵,他们分秒必争地埋藏、转移财物。
而寺院外的匪兵也没有闲着,他们开始从山下冲上来,包围、围攻寺庙了。砸门、叫喊、鸣枪,寺院的部分和尚进行了还击,部分和尚抓紧时间继续抢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