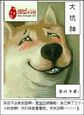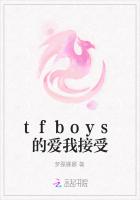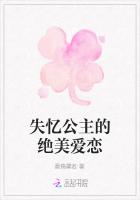春暖花开,面朝大海。赶海的人早早地来到海边,他们要赶在涨潮之前把网兜和鱼篓装得满满的呢。海娃直起腰,向港子那边望望,对老海夫海伢说了声“我到港东去,那儿文蛤大些”,就趟着浅水过去了。
海滩上,人声鼎沸,熙熙攘攘,一片祥和;太阳像一张老人的脸,红彤彤的,笑兮兮的,慈祥地照看着海滩上密密麻麻的人群。莫非大难临头总是这样?莫非老天爷总是以乐极生悲的现实来启迪人们的智慧?突然,人们惊呼起来,潮水像脱缰的野马奔涌而来,转眼间港子里水涨漫起来。不对呀,离涨潮的时刻还有一个时辰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怪潮,海伢并不恐惧,因为对于经常出海的海夫来讲,这是司空见惯的家常饭,至于在平缓的海滩上遇到潮水上涨,有海谚曰“担着海鲜往岸跑,潮头紧随脚跟咬”,但今天就不同,他一同出海多年的伙伴却在港子那边,凭多年的经验,海娃过不了港子了。
听老人说过,大海每天给人们一条金牛,但要一条人命的代价,莫非今天轮到海娃了。海伢从腰间解下还没有来得及喝的装满烧酒的军壶扔给港子对面的海娃,“兄弟,少喝点海水吧”!又解开担绳抛过去,“扎得牢一些,省得我回头来找不着你这‘宝贝’”!然后,挥泪自兹去,哗哗潮水啸啊。
“海娃呀海娃,谁叫你贪婪,活该……哈哈哈哈”这是迎接死神的狂笑,这声音三分像笑七分是泪呀。总不能就这样坐而待毙啊,他把挑海鲜的扁担插入沙泥,又用满满两网兜文蛤挤压住竖直的扁担,心想“这两兜文蛤可不能丢了,办丧事时,够炒二十盘子哪”,接着用海伢留的担绳一头结在扁担上,一头绑在手腕上,“绑牢一点,否则亲人到哪里去找我呀……绑长一点,万一潮水高了,过早地被淹死,划不来”,“该喝酒了,伙计说得对,少喝点海水吧”,“空军壶也扣在绳子上,万一鲨鱼把我吃了,亲人们还能找到水壶和文蛤”,“好啦好啦,你小子就来吧……”
潮水好似万马奔腾,铁蹄过处黄浑一片汪洋,海鸥惊飞,啧啧而噪,太阳尴尬地藏到水雾中去了……
退潮了,人们又奔向沙滩,仍然是来拾海鲜的,知情的人是来寻“宝贝”的。海伢冲在最前面,后面的人俨然是他的大部队。人们呼喊着“海娃”的名字,哭里呼啦地奔跑着。
看见了,直竖的扁担像一根旗杆,那面“旗帜”呢?看哪,“太阳”下面、“大海”沙滩的烂泥上,隐约躺着一个“大”字,准确地说是个“太”字……
走近了,走近了,人们发现,我们的海娃没死,他生命的发动机还在“呼——哧——,呼——哧——”地运转哪,周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酒气。
(《东方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