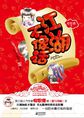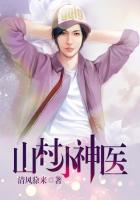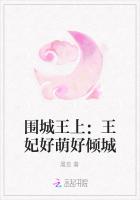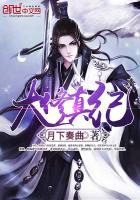我这人生活随便,从不喜欢受束缚,特别是在家中。
在家中,我可以随便上床睡觉,甚至不脱鞋,把脚搁在床框上;我可以乱扔瓜皮和果壳,弄得床头、案头、地面和电脑的键盘上满是;我可以随时打开VCD高歌一曲,虽然声音有点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但自娱自乐很开心;我还很放肆用力地,让我身体的不雅部位,发出那种号角声或唢呐音,有时还有调子,很夸张。出门办事,我可以将门虚掩着,甚至索性不关,有时是忘了关,但绝对不担心失窃。我的“家”,像是没扣上的锁,是开放的。
我不是神仙,所以我“结庐在人境”,在城里买了房;我是普通人,因而我入乡随俗,由妻子做主,住房也装潢了。别的不说,单那地板就花了三万,会客室木地板,卧室羊绒地毯,厨房大理石。这一切弄完以后,室内是一尘不染。但是,我感到很不自由,进房先得换鞋,衣服不能随意丢,吃饭不可以随便吐渣,烟灰要归缸,不漱洗妻子不准上床;既不能大声唱歌,更不能跳踢踏舞。时常有人叫门,“我们是水电公司的……”,“我们是家政的……”,“我们是推销产品的……”,“我们是来陪你唠嗑的……”,“我们是……的”,门铃“丁冬、丁冬”地响个不停,我总是警惕朝门后的铁棒看看,再提心吊胆的去窥猫眼,最后把门打开一条缝,生怕门外是一个手持匕首的歹人。那天,来了一个乡下朋友,我掬了一捧葵花籽出来消闲,果壳全撒在地板上,妻子面露难看色,弄得人家很尴尬,我也难为情。我现在的“家”,是上扣了的“锁”,且为“双保险”。
原以为,建新家,弄装潢,家会变得更舒适,谁知现在的家,却像一把架在脖子上的枷锁!这种感觉,一是来自装潢后带来的诸多不便,二是来自妻子的过多的管束。装潢使家居美丽了,极大地满足了视觉和触觉的享受,带来了不少精神上的愉悦。如果让它脏乱差,装潢还有什么意义?为此,妻子和我耗掉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怨气由此而生。我虽然知道,妻子对自己的指责是对家的爱护,也就是对我爱恋,不过,谁又能消受得了这苦口的良药?
我想离家出走,去单位住单身宿舍,但又怕耐不住单身的寂寞;我想到远方去打工,却又怕旅途无聊和浓重的乡愁,还有挤“民工潮”的狼狈。从这种意义上说,蜗牛多好,把“家”背着走,只容自己住,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尽管负担重了点。
怎样的“家”,才是理想的?“家”字的底是个“豕”字,即家里可以养猪,说明“家”是很随便的;如果把那“豕”字换成“女”字,又表明家里有女人,生活才安定;流行歌曲唱,“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让我懂得,家不在乎面积大小;黄梅戏这样唱,“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使我明白,家要和睦温馨,不强调装潢;巴金的《家》告诉人们,封建、落后和太多的“规矩”会使它破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由家庭构成的,小家还需要“大家”的呵护,社会的祥和与国家的富强都是家的坚强后盾。
这细胞,随意一点、活跃一点好啊!
(《盐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