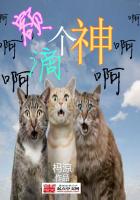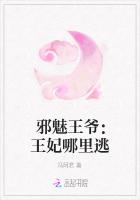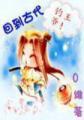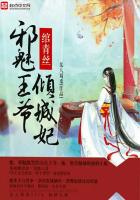先后五只猫,都没能寿终正寝,我要向猫忏悔。
从小我就喜欢猫,视之为宠物。外婆还为我编了一首谜语:“生来爱吃鱼,模样像老虎。白天睡大觉,夜晚抓老鼠。”那只花猫也是她为我逮的。花猫好可爱,肚皮连下巴,毛色雪白,像是披了块餐巾准备用餐似的,脸秀气得活脱脱村姑模样。猫饿了,仰头,翘尾,跟你讨吃的;不给,准在你腿上蹭来蹭去;吃饱了,它就坐到一旁“洗脸、梳头”,蜷成一只“保暖鞋”,眯起眼睛,念起“经”来,外婆说猫原来是和尚投错胎变的。那只猫从不累人,大小便自屙自盖,挺讲卫生的。每每练习抓老鼠,以自己的小尾巴当敌人,拼命地转圈。我用草叶子、布条儿或毛线球逗它,它更是兴奋不已,一会儿跳到东,一会儿跳到西……那天,全家吃早饭的时候,不知它从哪里抓来一只拇指大小的老鼠,东衔西躲,“呜呜呜”地叫个不停,大概是向主人炫耀成绩。
那“村姑”越长越出溜,不到一年,已从一只小猫妹长成大猫嫂了。重身不久,有了一群孩子。我对它的感情也由喜欢变成尊敬和呵护,因为它做妈妈了。当时我家很穷,食物不足是经常的事。外婆对一窝猫说:“也要给你们来个节制生育。”说着拿来一只簸箕,垫上一块红布,把眼睛尚未睁开的一堆小猫崽捧进去,只留下一只个头大点的。外婆一手端簸箕,一手挽着我,走到小河边。只见外婆颤抖着手,嘴里念念有词:“小猫,小猫,下河洗澡;捉条大鱼,吃个饱饱。”说着外婆双手合十,把小猫撂向河心,小猫“殁呀,殁呀”,叫了三两声就沉默了。回来的路上,外婆一句话也没说。那天,老猫回窝,不见了心肝宝贝,急得四处找寻,还仰头向我叫“没有噢,没有噢”,我不敢回答。只见它疲惫无力地回到窝里,“孤囡儿,孤囡儿”地叫着,舔舐着剩下的独子。我端来鱼汤拌饭,它看也不看,一连几天都这样,眼见得一天天瘦下去,两个礼拜后,猫妈妈死了。
外婆后悔。我忍不住哭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善待它的后代。
不久,高速公路经过我的村庄,响应上级号召实行集体农庄,我们家第一次搬迁。但那只猫不愿走。新居落成,我把它抱到新宅,给整条鱼它吃也留不住。一撒手,它又溜回老墩子上去了。没法子,我只得天天送食去。有时没空,或是忘了,它就得挨饿。墩子和水塘夷为平地,当年初冬就变成一望无垠离离的麦子。老猫找不到栖身的地方,我们也找不着它。后来听农民说,老猫就死在公路旁边的麦田里。
农家老鼠多,养猫是必须的。我们家还是又逮养了一只雄性的黄猫。那家伙可凶呢!不让人摸,捉老鼠很厉害。它每天都有“荤鲜”,它吃的比我家当时的伙食好。谁知,那年夏天,我在纳凉,忽然听到撕心裂肺的猫叫声,它来到我的跟前,一向不让人碰,今天居然要我抱,当我把它抱到煤油灯前一看,啊!口吐白沫,眼睛布满血丝,不好!中毒了!我赶紧用肥皂水强行给它洗胃,它一点儿也不挣扎,没过多久,它却挣脱了我的手,绝望的悲叫了两声,一头栽倒在地。原来它吃了邻居药死的老鼠。
这位英雄,没有死于敌手,而葬送于友好的伙伴——人类。
我现在住在单位,孩子在省城读书,工作之余,不免寂寞,又想逮只猫养养。这不,第四只猫来到我家。这只猫为波斯猫和本地猫杂交的后裔,好吃懒动,像个养尊处优的绅士,喜欢跟人撒娇,与人同食,睡沙发,还学会了在室内泥盆里拉屎,还会上抽水马桶撒尿;我怀疑它怕老鼠。有一次,它看到窗台落了一只麻雀,居然警觉地伏下身子瞄准、跳跃,可是没能跃上窗台,却重重地摔在地上。乐得麻雀于窗台上唧唧直叫。
尽管他不能抓老鼠,但我蛮喜欢它的,他乖巧,从不偷吃,也不碰碎花瓶。那天星期六早晨,我起身去菜市场买鱼,给它吃。回到家,哎,猫不见了。我四处打听,一个收破烂的告诉我:猫被捕了。这些捕猫人,在猫经常出没的地方,放一只夹子,夹子上缚一只活麻雀,当猫去捕麻雀,并被夹住了。据说,这些猫运到广东,每只买五十元;把猫肉和蛇肉一起烹调,叫龙虎宴。第四只猫就是这样没了的。一群可恶的人!
第五只,四只脚毛色全白的公猫,是新年前不久从学校食堂领养的,准确的说是失踪了。今年春节,我全家旅游“新马泰”。可初六回到家一看,猫不见了。临行前,我曾拜托邻居照看,可人家说,那猫啊,就是不肯去他家,总是守在家门口“没有窝,没有窝”地叫,过了几天就不见了。算了,后悔自责无济于事。邻居也说那只猫不怠懈——“四脚白,家家熟。养不家的!”我知道,那是劝我。哪知,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在路上,碰见了那只猫。不过唤也不理睬,它已不认识我了。我心里顿生一种负疚和失落感——没死就好,只要它过得好。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它的踪影。
每当有人问我还逮不逮猫时,我的心就会颤抖。
唉!人们的“宠”爱,有时也是一种伤害。
(《中国教师报》《北海晚报》《江苏农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