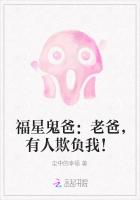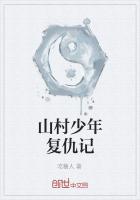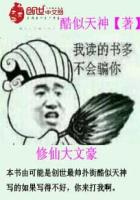文蛤的俗名
这次去西安参加笔会,老朋友神秘的对我说“今天请您品尝一味佳肴,是我特地央人从上海捎来的”,一拍手,小姐微笑着走T台似的端上一碟加盖的菜肴,我下意识地咽了两下消化液,理了理餐巾。当小姐掀开盖子时,我俩不约而同地叫起来:文蛤!不过我声音平淡,表情也不稀奇,老朋友一眼就看出来了,闪电般思索后道,噢!你是东台人,文蛤的故乡。“来来来,今天啊,这文蛤别有风味,家乡海鲜西安做。”接着我们边吃边聊起了有关文蛤的话题。
“这杲昃(东西),在我们东台叫轴碗儿,轴碗儿这名字还是你们中原人起的呢!”“噢?是吗?”
我们东台的部分人就是你们中原人的后裔呢。大约有了范公堤的时候中原人就去东台筚路蓝缕了,去的时候还把当时的战车带上了,可到了那儿发现不适用,后来就把它改造成牛车,整个车身还是木制的,只是四匹马换成四头牛,车座变成平顶方盘,车轮子由两个改成四个,且加宽了。战车只能在平原或戈壁上走,而牛车还能在水上行呢。哎,车上有一个部件始终保留着,那就是轴碗儿(也有人叫它车碗儿),位置在轮轴顶头,形状像文蛤,又像仰着的D字(牛车每行一段路就要往轴碗里加一次油润滑,否则,车子失油支溜支溜不润滑)。你们中原人一到海边,见到这么多文蛤,不知道叫什么,就称它为轴碗儿。如今的人啊,忘了轴碗儿的来历,产生这样那样的猜测,是可以理解的。
“什么时候带我去你们家乡看看?可以亲手采拾到轴碗儿吗?”“春季。可以!”
菜花开,轴碗肥
菜花吐金的季节,我们渔村的小伙伴都下海扒轴碗儿。菜花开,轴碗儿肥嘛。那时,大人们出海,我们几个小伙伴,也背上网兜,唧唧喳喳地跟了去。
轴碗儿一般都藏在沙泥里,不过它埋着的泥面上都有一个通气的眼儿,形状像一个个钥匙洞。只要用两齿耙子(扒轴碗儿的专用工具)轻轻一翻,轴碗儿就被捉住了。
大人们扒轴碗儿一直扒到背不动,而我们,够吃就上堤。瞧,我们的小兜兜都装满了;不知谁先叫了一声:“走啊,去烧轴碗儿吃!”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朝海堤方向的高地跑去。
轴碗儿的吃法不一:有用刀子剖开两爿介壳,翻转着剐下肉子,洗净后吃(类似“牡蛎”的吃法);或用油炸熟了吃,这是最普通的吃法;若是把剐下来的肉子剁碎,用淀粉和猪肉泥搅拌后,放到油锅里煎成丸子吃,这吃法就讲究些;采拾多了,还可以将轴碗儿肉子煮熟晒干待平日慢慢做汤吃……轴碗儿的食谱可谓多矣!
可在这茫茫海滩上,我们海边的小孩子家吃轴碗儿就是别具一格了。
一到“营地”,大家放下“战利品”,立即分头行动。捡柴火的捡柴火,挖土洞的挖土洞。各人兜兜里的轴碗儿全倒在一块事先准备好的布片上,包好,再放到刚挖好的土洞里,接着又把洞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土,最后架起干柴烧。约摸十分钟光景,轴碗儿熟了,好香啊!这不,我们像一群小“馋猫”,聚在一起吃起来。有的被烫得甩手嗷嗷叫,有的舌头嗖嗖直打滚,逗得大伙儿笑不拢嘴……
老朋友这时就像当年的鲁迅听闰土讲海边的西瓜和猹,都入迷啦!
“等吧,等菜花都黄灿灿一片了,我来接你。”“好!一言为定。”“……不行,不行吆!”“咋的啦?”“那时禁捕。”
(《东台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