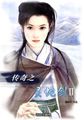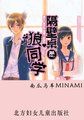郁达夫欲饱尝正宗的秋味从江南去了北平,我说,现在要体验正宗的隆冬也得上北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冬至一到,村边大河的冰足有一拉掌厚,可以溜冰,今天也是冬至,你去看看,波光粼粼,杨柳依依。这不得不让人思念纯正的冬天。
冬至是农历第二十二个节气,亦称“交九”或“数九”,即从冬至开始,九天一个“九”,总共九个“九”,数到八十一天时,在南方,便“九尽桃花开”了。
从气象的角度说,大致每九天一股寒潮,老百姓们称之“作九”,往往发生在前一个“九”的尾巴;从畏寒的心理方面谈,“九”与“久”谐音,言寒天漫长。古人每逢冬至,就逐日消寒,巴望春天早点降临。明代《帝京景物略》载:“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从防御严寒的层面看,“九”和“酒”又可以结拜,人们常以酒抗寒,“来来来,今儿个天太冷,弄两盅”,此言耳熟能详。
“头九冻河二九开,三九四九等春来”。“头九冻河”为事实,可“二九”的冰未必就化“开”,至于盎然的春意还远着呢,尽管“立春”的节刻恰是五六九间。民间把“三九至六九”叫做“九心”——“九的中心”是最寒冷的天气。“三九四九冰上走”,“三九四九冻破碓臼”,“三九至四九,匠工不出手”。别说“麦一种,手一拱”的野外作业的农民,就连室内制作的工匠也不能伸出手来干活。苏北地区的在黑龙江打工的木匠,元旦(或冬至)未到,就早早背了行囊和工具回故里,准备过年了——冻得吃不消呀。“寒露霜降,光鳏儿现象”,我不知这些光棍儿“九心”里怎么过。“春打五九尾”或“春立六九头”,大年就在“九心”里。生命垂危的人比比于这个时候赶往阎王那里安家落户,还记得祥林嫂吗,不就是在大年三十夜“祝福”时刻“老了”?此时强健的体质、“轻暖”的寒衣、营养的食品来得多么重要!“打了春,赤脚奔”。言下之意,到了“六九”,天气就暖和了,这不绝对。我国幅员辽阔,此时打赤脚,在南国可以,中国勉强,北国万万不可,非冻烂不行。在北国,春季特短暂,“吃了端午粽,方把寒衣送”呢。歌剧《刘胡兰》中唱道“数九寒天下大雪,天寒地冻心里热”,是革命的热情温暖了她的心窝。“九九艳阳天”,是“十八岁的哥哥”带来的。梁山伯的书童叫“四九”,“书童”者,陪读之年幼男仆也,身体瘦瘦的,衣服黑黑的,人家看了都觉得冷,旧时代仆人不可能丰腴,创作者拟角色名真高明。
“九是风冷,人是穷冷”。我们当地人把“九风”叫做罡暴。凛冽的风刀霜剑,刺骨的寒冷,人都能对付;唯心灵的冷漠,让人难以承受。“雪中送炭”,简直就是东方升起第二颗太阳,你想,“雪”是白的、冷的、自然的、给人痛苦,而“炭”呢,是黑的、热的、社会的、给人温情,对比强烈,反差悬殊,人们一定感激涕涟。“卖炭翁”是雪中送炭的人,可惜生不逢时,“一车炭千余斤”只换来“半匹红绡一丈绫”。当年孔繁森在西藏阿里工作时,接受过一回“年礼”,年脚下,老百姓扛了满满一袋子东西送给他过年,他好说歹说不肯收,但当老百姓解开袋子说是“干牛粪”时,他爽快地笑纳了——这是“雪中送粪”呀!“卖火柴的小女孩”可说是“雪中送火”,可是,她时空错位,命途多舛,换取了善良的中国人的多少眼泪呵!
如今,气候变暖,隆冬虽没有往年冷,但冰冻仍然是有的,温暖着的人们啊,你准备为那些寒冷的人做点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