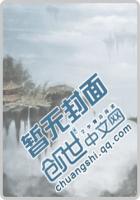正因为如此,陕北画像石中反映畜牧业题材的画面比较多。绥德、米脂县出土的几幅“放牧图”,有的是牧人扬鞭赶着一群牛,有的是牧人赶着一群马,有的是牧人赶着一群羊,还有的是马羊牛混群的。特别是绥德出土的一幅“放牧图”,画面中部有各种飞禽与驴杂嬉在一起,正中央刻两只长角牛在角逐;画面两端各刻一幅“驯马图”,牧人一手紧拉马缰,一手举鞭抽打,马被缰绳拉得弯颈扭头,前身跃起作挣扎状,似为牧人制服犟马的场面。还有一幅“牧场图”,画面中间是一阁楼,阁楼内牧主与人对话,左右各站一侍者,右边还有一人在跪拜。阁楼左侧是成群的牛、驴和野兽,右侧是成群的马和野兽。除此以外,还有几幅反映个体喂养的“饲养图”,一般是树下有一槽,一马吃草,一人饲养。绥德出土的饲养图”特别别致,在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下放一槽,左边马在吃草,右边饲养者张弓射树上栖落的小鸟,生活情趣非常浓。
这些画面说明陕北当时畜牧业相当发达,既有“马千只,牛倍之,羊万头”的大牧主,也有牲畜不多的个体牧民。
三、狩猎
狩猎原是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种主要手段。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自然条件的制约,狩猎在一些地方退居到次要地位甚至消失,但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有些少数民族活动的地方,狩猎仍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
陕北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有些时候还长期被少数民族占据和统治。东汉时期就有较长一段时间被匈奴占领。匈奴习俗是“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东汉时期陕北狩猎活动盛行,这与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
狩猎活动对汉民族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的作用上:一是进行作战训练或演习;二是进行娱乐;三是获取猎物。关于这三方面的情况,史书记载较多。《月令》曰:“天子乃历(敕)[饰],执弓挟矢以猎。”《月令章句》释:“亲执弓以射禽,所以教民(载)战事也。四时闲习,以救无辜,以伐有罪,所以强兵保民,安不忘危也。”《月令》又载:“孟冬天子讲武,习射御,角力”,“秋季天子乃教田猎,以习五戎。”《月令章句》释:“寄戎事之教于田猎。武事不可空设,必有以诫,故寄数于田猎,闲肄五兵。”《汉书地理志》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些记载说明,古代把作战训练或演习是与狩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常从上至长扬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弛逐埜兽。”《汉书·食货志》载:“元鼐中,天子行猎新秦中,以勒兵而归。”《汉书·杨雄传》又载:“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到汉中,张罗网置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猴、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扬射熊馆。”此记述的狩猎活动,目的是在于娱乐。至于获取猎味,那是狩猎中自然的事情了。皇帝如此重视和喜爱狩猎,郡县乃至乡里,狩猎活动也是非常盛行的。
陕北的每座画像石墓中几乎都刻有狩猎的场画。有的狩猎队伍扬幡骑马,有骑士前导,轺车紧跟。最生动的还是与野兽搏斗的场面。有的是一群猎手骑马张弓追逐一群鹿,猎犬、猎鹰随后紧跟;有的是猎手张弓射虎,虎跃起前爪进行捕抓;有的射熊,熊站立起来嘶叫;有的徒步执剑刺野猪,野猪张大长嘴扑咬;还有不少画面是猎手弯腰翻转射天上飞禽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牛君狩猎图”,画面上有十八个猎手骑马狩猎。有的张弓射鹿,有的伏身张弓追野猪,有的用长戟刺熊,熊站立起来咬住戟头不放,有的用网捉捕飞禽,还有的摇旗呐喊,呼狗助阵。这些画面活生生的表现出猎狩时一派紧张、喧闹的场面。
东汉时的世家地主、牧主,为了防卫和镇压农民起义,保卫自己的财产和安全,便把自己的“徒附”和“宾客”中青壮年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成为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些青壮年除了从事农牧业生产外,还担负着“葺治墙屋,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草窃之寇”的责任。到了秋谷入仓时,按照军事要求,“顺阳习射”,“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同时,地主、牧主家中还豢养一批“剑客”、“家兵”和“死士”,成为他们私人武装中的骨干。主人出门时,常数十人或近百人跟随;狩猎时则一马当先。画像石“狩猎图”中的猎手,很可能就是地主、牧主豢养的一批“剑客”、“家兵”和“死士”。
四、出行宴饮
东汉时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这些豪门贵族,出行时是“鲜车怒马”、“连车列骑”,仆从前导后拥;宴饮时“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享乐时,“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倡讴妓乐,列乎深堂”,玩耍时,“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踢鞠斗鸡。”每天享乐无度,过着荒淫奢侈生活。
陕北画像石中的“出行图”有多幅。有的是主人骑马,仆从徒步跟随;有的是主人坐车,前有“伍伯”辟路,后有驺从护卫,一派耀武扬威、盛气凌人的样子。米脂县出土的“出行图”是上下两行出行队伍,共八辆车,其中五辆轺车三辆辎车,骑吏十一人,其中有四骑吏扛戟,戟上挂幡。出行队前有三人迎客,一人跪拜,二人弯腰打辑。绥德出土的“出行图”,有轺车一辆,车前三骑吏导从,车后一骑吏背剑:后为辎车,最后是一骑吏驺从,出行队前站一人相迎,双手打揖,卑躬鞠敬。子洲出土的“出行图”则是轺车、辎车各一辆,前三骑吏导从,其中两骑吏执戟,迎面有二人,弯腰打揖相迎。
等级不同,出行时乘坐车的种类也不同。据《后汉书·舆服上》载:皇帝乘坐乘舆、金根、安车、立车,驾六马;太皇太后,皇太后乘坐金根或耕车,驾三马;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乘耕车,驾二马;皇太子、皇孙和公、列侯乘安车,驾二马;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官车有皂盖、朱两幡;千石、六百石的官朱左轓。景帝中元五年,始诏,中二千石以上右骈,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
上述的中二千石以上官吏乘坐有皂盖的车,应为轺车,有四维杠衣的车应为辅车。所谓轺车,即是一马驾驶的轻便车。《晋书·舆服志》:“轺车,古之时军车也。一马曰轺车,二马曰轺揖。汉代贵辎骈而贱轺车,魏晋重轺车而贱辎骈。”辎车,是有帷盖的车子,既可载物,又可坐卧。《释名·释车》:“辎车,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也。”陕北画像石“出行图”中的车辆,都为一马驾驶的轺车和辎车。
等级不同,出行时随从的人数和车数也不一样。《后汉书·舆服上》:“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琪弩车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又载:“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皆带剑,持棨戟为前列,捷弓九鞬。”从陕北画像石中的“出行图”看,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官秩是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的郡守、长史等高官,出行时属车有五吏、贼曹(掌捕盗贼)、督盗贼功曹(掌人事)、主簿(掌文书、行政事务)、主记(主记录)等车;又有环弩(连弩手)、伍伯(役卒)和骑吏等导从。此类有米脂县和绥德义和村出土的两幅“出行图”。
第二类:官秩在千石至六百石的官吏出行时,属车也有贼曹、功曹、主记、主簿等车和伍伯、璅弩、骑吏等,但人数较前者少。绥德四十里铺出土的“出行图”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官秩在三四百石的县长和郡的属官等,出行时属车有一至两辆,随从有伍伯、璅弩和骑吏少数几人。此类有绥德赵家铺子和子洲出土的两幅“出行图”。
第四类:官秩在二百石以下的小吏,出行时只有乘车一辆,无属车也无随车,或仅跟随一个随从。陕北画像中有多幅这类“出行图”。
陕北画像石中,墓门框上一般都刻有门卒执戟守卫和门吏打揖恭迎客人以及家役执长扫帚站立,表示庭院已打扫干净,请客人进入等图案,说明当时迎宾送客,朝夕宴饮的活动很盛行。绥德义和镇园子沟出土的“宴饮图”,左边是一车一骑,右边是二人一马,其中一人佩剑,中间是连栋阁楼,内坐四人,两两相对宴饮,阁楼上挂两只山鸡和一只兔子。王得元墓出土的“宴饮图”,中间阁楼内二人对饮,阁楼两边二十四人,舞者舒展长袖翩翩起舞,拊鼓协唱。这正是“庭室千品,旨酒万钟”,“多列女倡,歌舞于前”,“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情景的写照。
五、建筑
两汉时期,中国建筑体系基本形成。特别是东汉时期,成组的斗拱开始应用,木构楼阁逐步增多,砖石建筑发展起来,砖券结构开始应用。陕北画像中有“建筑图”数幅,使我们可以窥见东汉时建筑成就的一斑。
单阙图:“阙”是汉代一种独特建筑物。最初“阙”称“观”,是“于上观望”的意思。“观”又名“象魏”,是“其上县法象,其状巍巍然高大。”汉代的阙是宫门前的一种装饰建筑,“门必有阙”,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阙是门前的饰物,用以别尊卑,但在汉代一些祠庙、陵墓前和画像石中出现,则应是死者生前尊卑情况的反映。阙有“单阙”、“双阙”、和“子母阙”多种,从建筑材料看有砖质、石质等。陕北画像石中的阙是一“单阙”,阙上有楼观。
阁楼图:东汉时的木架构筑技术已娴熟,二、三层甚至更多层的木架楼已不少见。陕北画像石中的“阁楼图”有二层和三层的,有单体建筑也有连栋建筑。其形式和结构都表现得非常细腻,甚至建筑物上的瓦片和装饰物也都细致地表现出来,是研究古代建筑的好材料。
斗拱图:建筑上用斗拱,是中国建筑的独有特点,绥德出土的“斗拱图”,柱和斗拱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这种特写式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宝贵资料,柱础、圆柱、三层成组的斗拱都刻得非常细致,结构关系也表现得很清楚。
六、日常生活
东汉时期的庄园经济特点是自给自足经济,农业、牧业、手工业、副业和商业活动,都是由荫庇下的“徒附”来承担。陕北画像石中反映“徒附”从事农业、牧业和狩猎的内容前面已提及,但反映从事工业、副业和商业活动的内容却没有发现。这可能是东汉时期陕北这些活动不太盛行,也可能是这类画像石还没被发现。值得注意的是,画像石中却有不少反映当时日常生活的内容。在这些生活题材画面中的劳动者,一方面可能是庄园中的“徒附”,另方面也可能是个体农民。但是,这些日常生活题材不论反映的是庄园里的生活还是个体农民的生活,其共同点是具有浓郁的陕北地方特色。
宰羊图:把羊前后各一蹄捆绑在两根木柱上,将羊倒挂起来,羊头垂下,一人执刀准备宰杀。旁卧一狗,昂头注目,盼着主人能赏赐点碎肉。右边是一群鸡、鸭、羊。从古至今,陕北都是盛产羊的地方,羊肉是陕北人民喜欢的食品。画像石中出现宰羊题材,反映了陕北人民生活上这一普遍现象,也是画像石中表现的一个地方特色。
杀猪图:我国养猪,古今比较普遍,食肉也比较广泛。陕北画像石中的“杀猪图”是把猪捺倒在地,一人弯腰一手压住猪颈,一手提长尖刀猛刺。旁有一狗,可能是猪吼声太大,气氛紧张,它惊恐的狂叫着。
杀牛图:从陕北画像石内容看,当时这个地方牛很多,成群的牛都有表现,所以当时陕北人食牛肉也就是普遍的事了。画像石中的“杀牛图”。是把牛蹄捆绑放在地上,一人手提长刀准备割掉牛头。
烤羊肉串图:烤羊肉串是对羊肉的一种吃法,在新疆、青海、宁夏和陕西等地很普遍。今日这种吃法在西北一些地方还很多。画像石中的“烤羊肉串”图,是一人手拿一串穿好的羊肉在炭炉上正烤,其操作方法与今日烤羊肉串方法相同。这种题材在陕北画像石中出现,说明“烤羊肉串”历史悠久,也是陕北画像石的一个地方特色。
吊水图:这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陕北画像石中作为题材加以表现,说明艺术家们反映当时日常生活的广泛和真实。陕北画像石中的“吊水图”,是在一个筑砌有高沿的井口上,安装一个木架,架上装一滑轮,轮上系绳子,绳下端吊一桶。一人在井旁操纵吊水,从这一图上,使我们真切地看到当时人们的生活情景。
烧火做饭图:这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陕北画像石中的“烧火做饭图”中,左侧有一锅台,上放一大锅,右侧的火堂前,跽坐一人在烧火,后边的灶壁上,挂着一排灶具。
两鸡交配图:自古至今,我国农家都有圈养鸡、鸭、狗等家禽家畜的习惯。陕北画像石中的“双鸡交配图”图面上,有两只鸡、两只鸭和一条狗。狗在蹲着守护门户,鸭在自由的寻食,两只鸡一公一母正在交配。生活气息十分浓郁。
牛车图:东汉时富人出行是乘车或骑马,而贫苦的人出行或步行或牛车。陕北画像石中的“牛车图”,是一牛拉一车的单辕车,驭者坐在车辕上,身略前倾,牛为缓慢前行状。
七、舞乐百戏
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过程中,创造了舞蹈和音乐。这是劳动人民的艺术,反映他们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在原始社会时,人们就“击石拊石,百兽齐舞”,但到了阶级社会,这种艺术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并且据为己有。孔子在谈到舞乐用途时说:“安上治民,莫大于礼;移风易俗,莫大于乐。”《汉书·礼乐志》亦说是“通神明,主人伦,正情性,节万事”的东西。这说明统治阶级是把舞乐作为统治和治理人民的工具了。
陕北画像石中有许多舞乐百戏场面。坐而观赏的是地主或牧主,长袖曼舞,拊鼓跳丸的都是蓄养的男女优伶。这些舞伎和乐伎,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史记·货殖列传》说:“中山地薄人众……女子则鼓鸣瑟,跕利屣,游媚富贵,偏诸侯”,“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跳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贫富两个阶级,构成了这一幅幅舞乐百戏画面。
汉代的许多舞蹈是与唱歌相结合的,即是且歌且舞。舞蹈的名称往往是由歌词内容而定,因此,有些画像石的舞蹈也难给个确切名称。但根据文献记载和舞乐百戏画面,可分以下几种。
舞乐图:舞者为“长袖”、“持巾”,边舞边歌唱。绥德县王得元墓中出土的舞乐图,舞者和观者有二十四人。舞伎长袖翩跹,多姿多态;观者拱手停立,全神贯注。王得元墓中出土的另一舞乐图,有五人组成,其中三人翅袖折腰,姿态轻妙优美。另外还有多幅单人舞乐图,舞姿各式各样,刻在画像石的框格内。
鞬鼓舞:一个长形大鼓放置在高架上,鞬鼓伎一个或两个,站立或跪下,边击鼓边舞蹈。陕北画像石中的鞋鼓舞有多幅,有一人站立击鼓,有一人跪着击鼓;也有两人站立击鼓或跪着击鼓的,还有两人跪着击两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