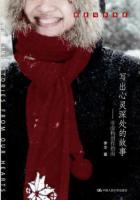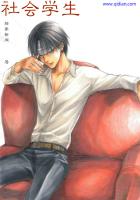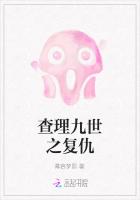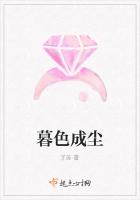孟东由北京回来后,仍旧办抗大展览,因这个展览是宣传毛主席、宣传延安精神的,是项政治任务,尽管造反派闹腾,但这个展览工作没人敢去冲击。孟东和宣传部的一位姓张的同志就住在展览的现场(位于新城广场东南的新城区文化馆),日夜就在那里。而文化局的局长们虽被揪了,但局里的广大干部却按兵没动,既没有造反,也没成立战斗队,更没有走向社会。但是,形势逼人,下属单位(尤其是文艺团体的造反派)又给局机关的干部贴大字报,说他们是“观潮派”、“保皇派”等等。革命风暴谁都害怕,所以局里的干部就商量成立一个群众组织——战斗队,他们不是为造反,而是弄一个挡箭牌,免得下属单位的群众组织来找麻烦,说白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糊弄别人,保护自己”。商量来商量去,就是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当头头,因为当时局里干部的状况是:不是家庭出身不好,就是个人历史有点问题,谁都不合适出来。推来找去,大家推出了家庭出身贫农、个人历史又清白的陈孟东和工人出身的李务成当头头。当时陈孟东还正在办展览,一直到1966年底才回机关。由于曾在北京街头看到的那些事情,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当局里造反派的头头。经过同志们的再三动员,说是为了保护大家不受冲击,成立战斗队是做样子给人看的,他也只得答应了。
那个时候,事情就那么怪,有人造反,不一定是战斗队的头头,有人没有造反,倒被推举为战斗队的头头,真的是历史给人开了一个大的玩笑。一般情况下,玩笑只是一笑了之,而历史给陈孟东开的这个玩笑,则影响了他几十年。若干年后,原文化局推举他的那些同志们很内疚地对孟东说:“孟东,是我们给你找的事,是我们害了你。”其实,陈孟东心里很清楚,他虽身为文化局群众组织的头头,既无领着大家去造反,也未干任何坏事情,以后有人之所以抓着他的小辫子不放,那是别有原由。
四
1967年初,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要求,已瘫痪的省文化局很快成立了生产领导班子,其成员有原副局长路鸿逵,原局办公室主任延文舟,局艺术处干部汪浔和社文处的陈孟东。生产班子按照解放军支左委员会的要求,开始抓全系统的业务工作,陕西省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前身)的“农民起义展览”就是从那时着手筹备的。
好景不长,生产班子的工作开展时间有半年多,社会上吹起了一股“经济主义”歪风,造反派们联合起来要求升工资,向上级机关要钱。文艺系统的陕西省歌舞剧院、省戏曲剧院、省戏校和西安市的狮吼剧团等单位的文革前不久新招收的所谓“学员”们,集结一起,常到文化局找生产班子的成员纠缠工资问题。此事关乎国家经济计划,文化局哪有权力给他们涨工资!所以折腾了很久,谁也不答应,谁也不签字。那些众多的学员们就使用了造反派惯用的一招——到文化局院子里静坐、绝食。开始,生产班子成员们与他们还相安无事,还能正常上班,几天后,那些造反派们饿极了,准备采取武的行动。他们扬言,要把生产领导班子的成员逮起来,用拳头逼他们签字。一天晚上,孟东回来很晚,他进门给我说:“今晚可能有人来闹事,你注意点。我去给王世昌说一声,让他也注意。”他在王世昌家尚未回来,就听到博物馆院子里铃声响了(在文革中博物馆人对保护文物很重视,门房值班人一旦发现大门口有成群的陌生人要求进门,就按铃向全馆人报警)。听到铃声,孟东和世昌自然知道是咋回事,他们趁着夜黑和地形熟悉,跳过博物馆后院的高墙从柏树林43号的家属院逃走了。等那帮人到了我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对我进行审问,我只回答:不知道去哪了,下班就没见人。他们虽没对我动手就撤走了,但这一晚,我一直没睡觉,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道孟东的下落。
从此后,局生产领导班子的成员东躲西藏,转入地下工作。他们曾在国棉五厂的广播室和省煤炭设计院的招待所待过,也一度转移到韩继宗同志西一路的家里。这期间孟东曾穿上别人的衣服,化装回来看过我和孩子一次。
1968年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混乱的局面好转了很多。孟东被调到省革委会文化组工作。文化组除几个解放军外,搞业务的就他一个。不久,省革委会之下成立了文化局,总后203部队的庾拮吉同志派来当局长,原文化局的副局长路鸿逵为副局长,陈孟东任社文组副组长。
那个时候文博系统的形势只能用“萧条”二字来形容,各博物馆关门,外县的不少文物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那真是百废待兴的年代。
孟东当时30岁出头,精力十分旺盛,一搞起文物工作这个本行,他像是服用了兴奋剂,每天从早到晚,东跑西奔,了解各地的文物现状,撰写保护文物的通告和各种文件及汇报材料。晚上叫开博物馆的大门回家是常有的事(当时我家在博物馆里)。
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了一大批唐代金银器,陈孟东就像是他家挖出了宝贝似的高兴至极,有好多天,他饭都顾不得回来吃,整天和文管会发掘的同志一起守在工地,生怕那些宝贝有点闪失。他把工地上出现的任何情况,随时向局领导汇报,及时处理。
业务工作要开展,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专业人员不足的问题。当时很多文博工作管理人员和考古研究人员都下放农村劳动锻炼,还有些大学生分的工作专业不对口。经过孟东的推荐,为文物系统调进了一批专业人员。如方鄂秦同志,由美院毕业分到玻璃厂工作,为提高半坡馆的陈列水平,把他调到那里当美工。还有一对年轻夫妻的事情,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孟东下班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你看,我今天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信,也不知道他们是咋认识我的,如果他们写的情况属实,那真是考古工作上很需要的人。”
写信的夫妻叫刘庆柱和李毓芳。信中说他们由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旬邑县山区的一个中学教书,因学校没有开历史课,改教了别的课。还谈到他们的处境、生活状况和心情,最后提出希望能归队从事考古工作,愿把一生贡献给祖国的考古事业。从孟东当时的表情和口气来看,他对这两个年轻人非常理解和同情,也为这两个人能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写信而感动。但是,同情归同情,他毕竟对这俩人的情况没有更多的了解。也不能单凭他们自己写的信就有所行动。有次他去北京办事,专门找到北大考古系的高明和俞伟超两位老师,从高、俞二位那里了解到刘和李是考古专业的高材生。他心里有底了,决定调他们到文物系统。
但是,那个年代,由外县往西安调,像登天一样难。西安调不进,先调到咸阳也行,于是孟东就和成阳地区文化局的张局长商量,先把他们调到咸阳的文物单位。结果,他们调到了咸阳地区文化局。二位如鱼得水,靠着考古工作上取得的成就,如今已是国内有名的考古学家,刘庆柱还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和学部委员。如今每每在电视上看到这位风度翩翩、学识渊博的学者在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就想起了30年前充满着无奈、期待和希望的那封看似平常而又不平常的信。
孟东很在乎才能,也很重视学历,但他又不是“唯文凭论”。他不从学历高低看人,而是看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他说,工作实践和大学学习一样,都可以培养出有知识的人。当时他常以省博物馆的情况为例,给年轻同志们说:“博物馆那么多讲解员也都没上过大学,他们肯钻研、好学习,跟着老同志学,都掌握了一门专长,不是什么工作都能担得起吗?”
70年代初,省考古所与省文管会合并,文管会与博物馆又是合署办公,实际上就是一个单位,我们都住在博物馆大院里。作为在上级机关工作的孟东,根本就没把博物馆和文管会的同志看作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当作朋友和兄弟。那时的发掘工地非常多,有咸阳的、凤翔的、临潼的以及陕北陕南的,野外调查的机会就更多。对于考古发掘工作,他不是看谁有文凭谁没文凭,而是看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考古所过来的杜葆仁同志没有大学文凭,但他工作十分踏实认真,每当老杜身穿蓝色劳动布工作服、脚穿翻毛高腰黄色皮鞋、背一个白色工具包由工地回来,从我家门口路过时,孟东总是投以敬重的目光和他打招呼。他常给我说:别看老杜不是大学生,搞起发掘一点不比别人差,他肯吃苦,有钻劲,别人不愿去的地方他去,别人不愿挖的工地他挖,我很欣赏这样的人。
文管会的很多同志,都是常年下工地,他们脸晒得油黑,每次回来都是风尘仆仆。在孟东心里,好像那些同志是为他家挖宝似的,他很过意不去。所以,每逢春节,趁他们在家休息,他让我备些小菜和白酒,轮流请同志们来家聚会,边喝边谝,谝笑话也讲工作上的事。文管会一位能说会道的同志对我家的下酒菜调侃说:“红萝卜丝,白萝卜丝,红白萝卜丝”,当时大家确实是都很清贫,那些萝卜丝还是凭“购物本”按人头定量供应的萝卜做的。生活虽清贫,但当时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相互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那真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年代。
五
1973年前后,局里又来了一位老干部任副局长。这位副局长和中央的康生熟悉。一次康生通过他索要一套西安碑林全部藏石的拓片。事情被当时作为文物处负责人的陈孟东和王世昌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给,并通知省博物馆的领导说不能给。因为文物政策有规定,碑林藏石的全套拓片不能掌握在私人手中,更不能赠送。送首长、送外宾只能是个别碑石的拓片。最后还是挑了一部分碑子的拓片送给了当时身为中央首长的康生。送拓片的事情大大惹怒了这位副局长,一则是使他在康生面前丢了面子不好交代,再则是文物处的小小负责人竟敢犯上!从此后他就与陈孟东、王世昌和省博革委会主任结下了怨恨。
1974年3月,陈孟东被派到杨梧干校劳动锻炼七个月,和他同去的有省文管会的陈全方同志。
就在这一年的6月份,省文化局在西大街局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大会,参加会的人是局系统各单位的领导(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内容不记得是学习和贯彻中央文革的哪个文件,也不知道是为哪个问题需要几位局领导表态,几个局长的表态大家都没意见,唯独那一位副局长的表态大家不满意。因为与会的革委会副主任和委员们都是原来群众组织的头头,说起话来火药味很浓,大家七嘴八舌和这位副局长进行了辩论,气得这位副局长几乎晕过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到此,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从1977年开始,全国上下各系统,各单位开始彻底清查“四人帮”的罪行,并联系各单位的实际。清查造反派们干的坏事。文化系统查来查去,把1974年6月的会上造反派“围攻”副局长(革命干部),作为重大事件——“七四·六事件”。
1977年的全年,陈孟东又被派到户县水堡村蹲点,所以清查工作他没参加。当年他既没有参加“七四·六”会议,如今为“七四·六”定性他也不在局里,因此,他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七四·六事件”。
几年以后,文化局领导班子调整,拟从局里提拔一个副局长,上级来进行考察和民意测验,测验的办法是无记名投票。测验结果,孟东的票是绝对多数。事后局里的一位同志来我家给我说:“老陈在局里威信很高,这次投票,大家都投的他,老陈几乎是全票。”
这时,“七四·六”会议上被围攻的那位领导已调离文化局,又恰巧是调在了文化局的上级机关,当孟东的材料报上去后,这位当年的副局长非常生气,说陈孟东是原文化局群众组织的头头,在“七四·六”会议上还参与闹事,带头围攻他,这样的人绝不能重用等等。从此,陈孟东就戴上了一顶无形的黑帽子。直到去世,他就是在这顶帽子的重压下工作的。
知道内情的人很清楚,“七四·六”会议期间,孟东正在杨梧干校头顶烈日“龙口夺食”搞夏收呢!他不仅没有迫害老干部,在干校反而和原陕西省省长赵守一处得很好,要不然,他以后怎么会与赵守一的长子赵联成为好朋友呢?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往往上边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下边人的命运,很多人都知道孟东冤枉,可是,这种事情,说了就说了,过去就过去了,不可能有谁站出来给平反,他自己也不能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说吧!只能是一个字——忍。
后来,局里又来了一位新副局长。孟东原和他不认识,更无冤无仇,不知为什么,他上任后就对在他手下工作的陈孟东有看法。有次,孟东和文物处的刘合心去陕南旬阳县出差,工作办完后,他们又去旬阳与湖北交界处的大山里,调查被传为楚长城的遗迹。他回来后一边给我看照片,一边向我讲述他们此次调查的经历,去时口袋里装着冷馍作干粮,他们走的山路人迹罕至,不仅布满荆棘,而且常有野猪和熊出没,每人手里都拿一个长棍,又当拐棍又作护身武器。从他的照片看,一手提个破革包,一手拄着个棍子,活活像个讨饭的。虽然很苦,但他和合心同志都很高兴,终于看清楚了那段所谓“楚长城”的真面目,他们认为那是楚国的边城而不叫长城。
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出差和有意义的业务调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的陕南之行被这位副局长猜疑为是一次阴谋活动,惑疑他们去串联,准备颠覆领导。于是,这位副局长,不惜浪费人力和财力,紧接着又派一个搞行政的干部再去旬阳,调查他俩的“活动”,结果什么把柄也没抓到,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孟东仍是坚持一个“忍”字,他的逆来顺受精神简直比《水浒》中的林冲还林冲。
孟东之所以奉行着勤、默、忍的三字格言,我知道,在他内心深处死死地抱定一个想法,他常给我说:“我干工作不是给他哪个人干的,我是干的陕西的文物工作,我不能因为某个人给我过不去,我就放松自己的工作,反而还要多干、干得更好。”他是越压、越打干劲越足,在这一点上他又像阿Q。
六
有人说,陈孟东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点不假,他和任何人任何事一样,不可能是众口一词。正如当年省文管会一位不是哲人而像哲人的人说过的话:“有的人,在民间很臭而在官方很香;有的人,在官方很臭而在民间很香。”这点,不仅从孟东去世后追悼会的场面和情景可以证明,而且从他生前的一些事也可证明。
说也奇怪,陈孟东这个小人物的事情引起了全国不少省的文物界同志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