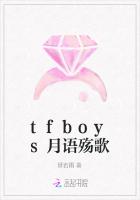第二天早上,他一见到过去的工作伙伴就说:“我说,乔,第二十街有个法国人。他挣够了钱,要回法国去。留下个挺不错的小规模蒸汽洗衣房。你要是想安顿下来,就在那儿开个头吧。拿这笔钱去买身衣服,十点钟到这个人的办公室去。他替我找到了这个洗衣房,他会带你去那里看看。要是你喜欢,并且觉得一万二的价钱合适,就告诉我,它就归你了。现在走吧,我忙着呢。待会儿再见。”
“听我说,蒙汤,”乔压住心里的怒火缓慢地说。“我今儿早上到这里来是想跟你聊聊。懂吗?我可不是来要什么洗衣房的。我看在老伙计的份上,想跟你叙谈叙谈,可你却把个洗衣房塞给我。让我告诉你该怎么办。你带着你那个洗衣房见鬼去吧!”
他想冲出房间去,可马丁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扭回来。
“听我说,乔,”他说,“你要是这么来,我就打烂你的脑瓜。就因为你是我的老伙计,我要使劲揍你。听懂啦?你听我的,好吗?”
乔一把揪住他,想把他摔倒在地,可他拼命挣脱出来。他们俩紧紧扭打在一起,在房间里兜来兜去,最后两人重重摔在一把椅子上,把它压了个粉碎。乔的两条胳膊被抓住,胸脯被马丁的膝盖顶住压在底下。等马丁把他放开后,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现在我们可以谈上两句啦,”马丁说。“你打不赢我。我要你先解决那个洗衣房的事。完事后回到我这儿来,我们看在老伙计的份上聊聊。我告诉过你,我现在忙着呢。你瞧。”
这时,一个仆人送来早班邮件,是一大堆信和杂志。
“我怎么能一边看这么一堆东西,一边跟你聊呢?你去把洗衣房的事定下来,然后我们再见面。”
“好吧,”乔勉强同意了。“我以为你要赶我走呢,可我猜,我错了。可我告诉你,蒙汤,要是正式交起手来,你休想打败我。我的拳头可比你的打得远。”
“我们改日较量,等着瞧。”马丁微笑着说。
“好极了,等洗衣房一开张就打,”乔伸出胳膊。“你看见这长度了吗?把你的胳膊都比没了。”
这个洗衣工走出去把门关上后,马丁舒心地呼了口气。他越来越讨厌交际了。他每天都觉得跟人们应酬是一种极大的负担。跟人们在一起让他不安,搜索枯肠没话找话让他恼火。人们把他弄得烦躁不堪,他一跟人接触,就马上考虑找什么借口把他们打发走。
他并没有开始看信,懒洋洋地坐在椅子里,一连半个钟头,什么也不干,他的意识中只有些模糊而不完整的念头,确切些说,他时有时无的意识中只剩下每隔上好久才出现一回的这种念头了。
他打起精神开始浏览那些信件。他一望而知,其中十几封是要求他签名留念的;有向他请求捐助的;有怪人写来的信,有的声称自己造出了永动机的样机,有的能证明地球表面其实是个空心球体的内壁,有的要求资助,以便购买加利福尼亚半岛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有的女人写来信要求跟他结识,其中有一封让他觉得好笑,因为信中附上了她付给教堂座位费的收据,以此证明她是个有信仰有责任心的女子。
每天的一大堆信中都有编辑和出版商的大量来信,编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他的稿件,出版商真诚地要他的书稿,他们要的都是原来他那些受到藐视的可怜稿件,当时,为了买邮票把它们寄出去,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进了当铺。还有些意外的支票,有的是英国杂志购买连载权的稿酬,有的是译本的预付稿酬。他的英国代理人通知他说,他有三本书的德译本版权已经卖出去了,另外,瑞典出了他的瑞典文译本,然而是因为瑞典不是伯尔尼协约的缔约国,所以他从这些译本中得不到一分钱。俄国写来一信,诚恳地请求允许他们出版俄文本,可这完全是空有其名,因为那个国家也不是伯尔尼协约的缔约国。
他接着看那包文摘剪辑,发现自己的作品已成为当今的时髦,他已经成了个轰动一时的人物。他创作出的所有东西,统统被送到读者面前。这看来就是他走红的原故。他的作品风糜了读者大众,就像吉卜林那样,当时,他已经奄奄待毙,读者在大众心理的刺激下,一窝蜂都读起他的作品来。马丁记起,全世界的这帮读者,当时读了吉卜林的作品,虽然根本看不懂其中内容,却拼命为他喝彩,但是没过几个月,又忽然向他扑将过去,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马丁想到这里,不由咧开嘴笑了。他自己难道过几个月就不会受到类似的对待?等着瞧吧,他要捉弄他们,远走高飞,去南海建起他的茅草屋,做起珍珠和椰子干生意,乘坐装有舷外浮材的单薄小艇在珊瑚礁上飞越,捕捉鲨鱼和鲣鱼,到泰奥海伊山谷的峭壁之间去打野山羊。
他这么一想,才突然明白了自己的绝望处境。他清楚地看出,自己正在死荫幽谷中等死。他的生命力正在逐渐消失、衰弱,他在一步步走向死亡。他意识到现在每天要睡多长时间,而且还渴望睡眠。过去,他痛恨睡眠,因为睡眠夺走了他生命中的宝贵时光。二十四小时中仅仅睡上四个小时,他还觉得这四小时的生命被剥夺了呢。他以前多么舍不得睡觉啊!可现在,他却舍不得生活了。生活并不美好;他尝到的生活滋味不是甜的,而是苦的。他的危险就在于此。不渴望生活的生物只能走向死亡。某种隐隐约约的求生本能在他身体中躁动着,他明白,必须离开了。他朝屋子里扫视了一圈,一想到要收拾东西,他就觉得是个负担。也许留到最后时刻再收拾更好些。他现在可以去买上一套行装。
他戴上帽子出门,走进一家枪店,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挑选自动步枪、弹药和渔具。做生意的方式有所改变,他得知,要订货就要等到了塔希提以后。反正可以从澳大利亚订。这个方式让他觉得高兴。他避免了某种麻烦,这时做任何事都让他觉得不舒服。他高高兴兴回到饭店,想到那张莫里斯安乐椅,他就觉得心满意足。可是,一走进房间就发现乔坐在他的安乐椅中,心里不由难受得哼了一声。
乔对那家洗衣房十分满意。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明天他就要去接管。马丁闭住眼睛躺在床上,听他说个不停。马丁的思想已经飞向远方了,远得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是在思考。他偶然回答上一两句也得花费一番力气。可这还是跟他从来就喜欢的乔谈话呢。但是乔却对生活充满热情。乔生活中的喧闹冲击着马丁疲惫不堪的心灵,让他觉得难受。好像他是一根探针,刺得他疲惫的感官疼痛不已。乔提起他们得打上一架时,他几乎尖声叫嚷起来。
“记住,乔,你得按以前在雪莱温泉旅馆时你立下的规矩去经营这家洗衣房,”他说。“不许加班干活。不许连夜苦干。不许雇童工操纵碾压机。哪儿也不能用童工。工钱要合理。”
乔点了点头,掏出个笔记本来。
“瞧,我今天上午已经定下些规矩。你觉得怎么样?”
他念了一遍,马丁一边表示赞成,一边在犯愁,不知道乔什么时候才离开。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黄昏时分了。他渐渐想起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他朝屋子周围望望。显然,乔见他打起盹来,就悄悄溜掉了。他心想,乔倒还挺懂得体贴人。接着,他闭上眼睛再次沉沉入睡。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乔为了控制、组织洗衣房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没怎么来打扰他;直到开船的前一天,报纸上才刊出了他在玛丽波萨号上订了票的消息。出于求生的冲动,他去找过一个大夫,作了全身检查。他浑身上下什么毛病都没有。大夫说,他的心肺功能极为强壮。就大夫所知,他的每个器官都十分正常,而且工作得也十分正常。
“你什么毛病也没有,伊德先生,”他说,“确实一点毛病也没有。你的身体健康极了。说实话,我真羡慕你的身体。棒极了。瞧你的胸膛!你这杰出的体格,秘密就在你结实的胸膛和健壮的胃口里。你这样的体格一千个人中只有一个,不,一万人里只有一个。如果不出意外,你应该能活到一百岁。”
马丁明白,里奇的诊断是对的。他的身体没问题。毛病出在他的“思考机器”中,这种毛病除了到南海去之外,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可现在的问题是,他在就要出发的当儿又不想走了。南海就像资产阶级的文明一样,对他失去了吸引力。想到要走,他的热情全都消失了,至于动身的种种准备,他觉得那简直是肉体上的折磨。假如他已经上了船,倒会觉得舒服些。
最后一天真是场痛苦的煎熬。帕勒坦·西杰勃特蒙和戈苔洛忒一家在晨报上看到他要出发的消息,赶来为他送行,哈尔莫·冯·施米特和曼琳艾也来跟他道别。此外,还有些事务要处理,有些账要结清,他还得忍受川流不息的记者们。他在夜校门口跟里奇·康诺利匆匆说了声再见,就赶忙离开了。回到饭店房间,他发现乔来了,因为整天都忙于洗衣房的事直到这时才有空来看他。最后这起访客让马丁再也忍受不了啦,他两手紧紧抓住椅子扶手,边讲边听,足足忍耐了半个钟头。
“你知道,乔,”他说,“谁也没把你拴在那个洗衣房里。那儿没有绳子拴你。你随时都可以把它卖掉,随便把钱花个痛快。你要是觉得烦了,随时可以卖掉它,再去流浪。你觉得怎么痛快就怎么干吧。”
乔摇了摇头。
“我再也不去流浪了,谢谢你的好意。流浪倒是挺有意思,只是有一点不好:没个姑娘陪伴。我这个人没个女人不成,可当了流浪汉就找不成女人。有好几回,我从一些房子前面经过,听见里面在开舞会,有女人的咯咯笑声,从窗户里望去,还能看见女人们穿着白裙子,脸上带着笑容。唉,跟你说吧,那种时候真叫人活受罪。我实在喜欢跳舞、野餐、月下漫步之类。我喜欢搞好这个洗衣房,既排场,又能在裤兜里装上叮当作响的一大把美元。我已经看上个姑娘啦,是昨天的事,可你知道吗,我已经想好要跟他尽快结婚啦。我一想到这事就乐得打口哨。她是个美人儿,眼神儿和蔼,声音说不出的温柔。我要跟她结婚,等着瞧吧。我说,你有这么多花不完的钱,干吗不结婚呢?你准能找到个天底下最好的姑娘。”
马丁微笑着摇了摇头,可心里想不通,男人干吗都想结婚?这简直是个最让他惊讶,最让人费解的事。
开船之前,马丁站在玛丽波萨号的甲板上望去,见里奇·康诺利躲在码头上一大群人的外围。“带她走,”他忽然这么想道。“要做点好事多容易啊。她会感到无比幸福的。”一时间,他仿佛觉得无法抵御这种诱惑,然而片刻之后,又被这个念头吓坏了。这想法让他恐惧。他那疲惫的灵魂仿佛喊着提出了抗议。他哼了一声离开船栏杆,喃喃地说:“伙计,你病得不轻啊,你病得不轻!”
他躲进自己的豪华客舱,直到船离开码头才走出来。吃午饭时,他走进餐厅,发现自己的座位是船长右侧的贵宾席;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发现,自己成了船上的名人。但是所有乘过船的名人中,没有哪个比他更觉得不舒服了。整个下午,他躺在甲板上的一张椅子里,闭上眼睛断断续续地打着盹,晚上早早就上了床。
第二天一过,所有晕船的乘客都复元了,全体乘客都出现在甲板上,但是他见的乘客越多就越讨厌他们。他明知道自己对待他们的作法并不公正。他逼着自己承认,他们是些善良、和气的人。但是他一这么承认,马上就对这种说法加以限定:善良、和气得跟所有资产阶级分子一个样,也具有资产阶级的偏狭心理,而且同样无知。他们的谈话让他厌烦,他们渺小、浅薄的头脑里空空如也;而年轻人兴高采烈的精神和过度旺盛的精力又让他惊讶不已。他们从来无法安静下来,片刻不停地在甲板上掷绳圈,抛铁环,来回溜达,要不就大声嚷着俯身在栏杆上观望跃出水面的海豚和第一批出现的飞鱼。
他总是睡个没完。早饭后他就倒在帆布躺椅上,手里拿着本杂志,可又看不进去。一页页的文字让他厌烦。他弄不懂人们干吗有那么多东西要写,想着想着,就打起盹来。午饭锣声响起后,他为自己不得不醒来感到恼火。醒着让他不快。
一次,他试图打起精神,摆脱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就走进前面的水手舱去。可是,好像现在的水手也换成完全不同的一路人,跟他以前在水手舱那时根本不是一回事了。他从这帮面孔呆板、脑瓜愚鲁的畜牲中找不出与自己的共同之处。他极为失望。在上层社会中,谁也不欢迎马丁·伊德本人,可他又回不到自己的阶级中去了,他们过去的确欢迎他的。他可不喜欢他们。他看不惯他们,就像他也无法忍受那帮一等舱里的乘客和喧闹的年轻人一样。
在他看来,生活就像一道强烈的白光,刺得一个病人睁不开疲倦的双眼。在他醒着的每一时刻里,生活的光芒火辣辣地照射在他周围、照耀在他身上。他感到浑身疼痛。疼得难以忍受。这是马丁平生第一次乘坐头等舱。他过去乘船航海不是待在水手舱里,就是在统舱,或者在黑乎乎的煤舱里铲煤。那时,他顺着铁梯从热得让人窒息的底舱爬上甲板,常看到帆布遮阳篷下身穿凉爽白色衣服的乘客,他们逍遥自在、无所事事,船上的服务员能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和愿望,当时他觉得他们生活的圈子和他们的活动简直就是在天堂上。啊,他现在也在这里,而且是船上的名人,吸引着全船的注意,坐在船长的右边,却偏要回到水手舱和锅炉舱去寻找失去的乐园。他既没有找到新的乐土,连原来那片领地也找不到了。
他竭力想活动一下身体,找点乐趣。他走进船员餐厅,结果却为离开那里而感到高兴。他跟一位不当班的舵手聊了一会儿,那人是个挺聪明的人,马上就对他宣传起社会主义,还往他手里塞了一叠传单和小册子。他听着那人满口的奴隶道德观念,懒洋洋地想起了他那尼采哲学。可这些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他记得尼采说过一句疯话,说他怀疑真理的存在。可谁又能说得准尼采就一定不对呢?也许任何地方都没有真理,就连真理中也没有真理,根本就没有真理这么一种东西。可他的脑子很快就疲惫不堪了,坐回椅子中打瞌睡让他感到惬意。
他在这条轮船上已经很悲惨了,然而一桩新的苦恼又袭上他的心头。轮船抵达塔希提后怎么办?他就得上岸。他要先去订货,然后登上条大帆船去马克萨斯群岛,去干那千百件想起来都叫人害怕的事情。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逼着自己认真考虑,总会发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千真万确,他正是在死荫幽谷中徘徊,他的危险在于并没有真正感到害怕。假如他感到了害怕,他就会向生的方向努力。由于他并不害怕,所以他才越来越向幽谷深处沉沦下去。他从过去熟悉的生活中没有找到欢乐。玛丽波萨号这时进入了东北贸易风区,但是,这股醇酒般的劲风却让他觉得恼火。他把椅子挪开,逃避这个过去与他日夜相伴的老伙计,躲开它热烈的拥抱。
玛丽波萨号开进赤道无风带那天,马丁感到比以前更加悲惨。他想睡都睡不着了。他睡得太充足,这时只得醒着忍受白得刺眼的光芒。他心烦意乱,到处走动。空气又湿又粘,阵雨过后他也不感到精神爽快。生命让他感到痛苦。他像头困兽一样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直到走累了才坐进椅子里,坐乏了就站起来再走。他耐着性子看完了那本杂志,又从船上的图书室挑了几本诗集。可是这些书也引不起他的兴趣,后来,他只得不停地溜达。
晚饭后,他要在甲饭上逗留到很晚,可这也对他毫无帮助,因为他走下自己的客舱后,还是睡不着。他连这种暂时逃避生活的事情也做不成了。这可太过分啦。他打开电灯,想看看书。有一本是斯威潘的诗集。他躺在床上翻看了几页,突然发生了兴趣。他读完一节,打算继续看下去,却不由自主地回到原来那一节。他把书扣在自己胸脯上,陷入了沉思。的确如此,就是这么回事!奇怪,以前他居然没想到!一切的意义不过如此;他这么久以来一直漂荡着,如今,斯威潘才向他揭示了幸福的出路。他需要安息,而安息正在这里等待着他。他朝圆形舷窗瞟了一眼。好,够大的了。几星期来,他第一次感到快乐。他终于找到治疗他这疾病的良方。他把书举起来,缓缓朗读那一节:
告别热恋的生命,
摆脱希望与恐惧,
面对冥界的众神,
献上简短的谢忱;
生命从来有尽期,
长眠一去不复归,
江河逶迤长烦恼,
大海深处得安息。
他又朝敞开的舷窗望了一眼。斯威潘向他提供了答案。生命是邪恶的,或者说,它变得越来越邪恶,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了。“长眠一去不复归!”这行诗让他深为感激。这简直是宇宙的恩泽。当生活变得让人痛苦让人厌倦时,死亡就会用长眠给人安慰。他还等待什么?该走啦。
他站起身,把头探出舷窗外,望着船体划开的乳白色浪花。玛丽波萨号吃水很深,要是他双手攀住窗口,脚准能够到水面。他可以悄然滑入水中。谁也不会听见。一阵浪雾打湿了他的面孔。他的舌头尝到一股咸味,味道不赖。他不知道是不是该写上一首绝唱,可是又一笑置之。没时间啦,他急于成行。
他关掉客舱里的灯,以免泄漏自己的秘密,然后把双脚先伸出舷窗。他的肩膀给卡住了,他用力缩回身子,把一条胳膊贴在身子一侧先挤出去。轮船这时正好摆动了一下,帮了他的忙,他钻了出去,双手吊在舷窗上。他的双脚一碰到水面,他就撒开手,身体掉进乳白色的浪花里。玛丽波萨号的船舷从他身旁飞驶而过,像一道黑黢黢的墙,上面时而有几个亮着灯的舷窗。它的确开得很快。他还没来得及细想,已经被甩在船后面,在浪花和泡沫劈啪作响的海面上缓缓游着。
一条鲣鱼在他白色的身体上咬了一口,他放声大笑。鱼撕下他的一块肉,疼痛让他想起了跳海的目的。刚才忙于活动,竟然忘记了原来的目的。玛丽波萨号上的灯光在远方越来越模糊了,可他却在这里满怀信心地游着,好像他的目的是要游到一千英里外最近的陆地上去似的。
这是求生的本能。他停止游泳,然而,他一感到水漫到嘴边,立即拼命划动双手,浮出水面来。他想,这是求生的意志,于是发出一声冷笑。啊,原来他还有意志,这意志还挺坚强的,但是最后再使把劲,这意志就不复存在啦。
他换了个垂直的姿势,朝天空静谧的星星望了一眼,同时把肺里的空气全都呼出去。他手足并用,猛地一划,肩膀和半个胸脯露出了水面。这是为了得到下沉的冲力。紧接着,他一动不动,听任身体往下沉,像一尊白色的石像,沉了下去。他故意把水深深吸进肺里,就像有人吸食麻醉品一样。他感到窒息后,胳膊和腿不由自主地拼命挣扎起来,又把他推到水面上,暴露在清澈的星空下。
他轻蔑地想道,这是求生的意志。他竭力不把空气吸进快要憋炸的肺里,但是办不到。好吧,他要换一个方式。他把肺里吸足了空气。这回足够沉到很深的地方啦。他翻转身体,使出浑身的力气,调动全部意志,头朝下游去。他越游越深,睁开眼睛望着幽暗中鲣鱼冲来撞去的磷磷闪光,希望它们别在他游的时候来咬他,因为被咬疼后,他紧张的意志说不定会垮下来。但是它们并没有咬。他不禁感激生命给予他的最后恩惠。
他不停地向深处游啊游啊,直到胳膊和腿都累得再也划不动为止。他知道已经游得很深了。他的耳鼓开始疼痛,脑袋里也开始感到嗡嗡的响声。他的忍耐力眼看就要垮了,可他仍然逼着胳膊和腿把他的身体向更深处推进,最后他的意志崩溃了,肺里的空气猛地冲了出来,变作一个个汽球般的水泡,擦着他的脸颊和眼睛直往上冒。接着到来的是一阵剧烈的疼痛和窒息。他还没有死,这个念头在他晕眩的意识中回荡着,死亡是不痛苦的。他还活着,还能感觉到活着的剧烈痛苦。可这是生命给他的最后打击了。
固执的手脚开始痉挛般地拍打、搅动,力量很虚弱。他到底战胜了自己的手脚,也战胜了求生的意志,让他的手脚乱动个不停的正是那种意志。他沉得太深了,他的手脚再拼命挣扎也浮不上水面去。他好像觉得懒洋洋地漂浮在一片梦幻的大海上,沐浴在五彩缤纷的光辉之中。那是什么?好像是座灯塔。可它在他的脑子里,它发出明亮而闪烁的白光。它闪烁的越来越快。他听到一阵长时间的轰隆声,似乎他正顺着一段深不见底的楼梯摔了下去。落到楼梯底下时,他陷入黑暗之中。这便是他最后的意识。他掉进了黑暗。接着,他便失去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