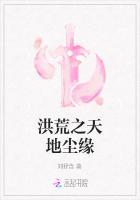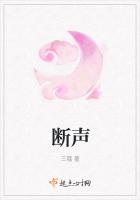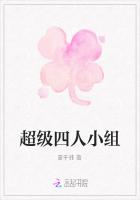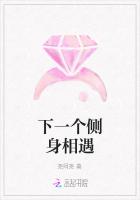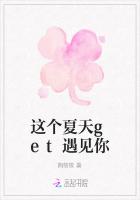散文是能者最多的一种写作体裁。可以说,谁都会写散文;又可以说,能写好散文的人不多。我自认为就是“谁”与“不多”之间的那个人。我不敢说是“那种人”,因为我就是我,我不能代表别人。实际上,散文之惑,常存一心,谁又能没有“独此一家”的体会呢?
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散文是会生长的,像人一样。如果作个比喻,本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一片叶子—当然有好看的也有不好看的,或不那么好看的—那么,目录页上从前往后的时间之干自然就是散文生长的记录了。我是这么想的,这本书也是这么编的。这是不能不首先有所告白的。
的确如此,散文是会生长的。在“青记录”中,青涩之痕虽无形却显见,但它不仅是我用“文笔”观察世界特别是大自然之始,更是一个中学生在“文革”中审美取向的“另类”记录,因此,我并不“为少作悔”或愧。至于“热回首”,自然重在一个“热”字了。那是一个热血青年离开《西双版纳,我的乳娘》之后,在北京,用一篇又一篇更成型也更刻意的散文向那片遥远的热土致敬。至于是热土孕育热血,抑或是热血孕育热土,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青春无敌,谁能没有一个“热”字可资纪念?“采缤纷”中,不仅有种种京都情缘,更有些闲情偶遇或偶寄,当然,也开始有了些民事或文事思缕,因为我毕竟已经受邀为《中国新闻出版报》专门写一篇《我记忆中的记者节》了。至此,散文这棵大树在我心中更加开疆拓土,原来世上散文不仅有作家一脉,还有记者一脉。实际上,世上三百六十行,人人可以写散文。什么叫散文?最宽泛说,凡不受格律拘束之文,即是散文。具体说,现代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对某些片段的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篇幅一般不长,形式自由,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语言不受韵律的拘束;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甚或三者兼有。散文本身按其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杂文、小品、随笔、回忆录等。
至此,散文是会生长的,其“学”也“无涯”自是“学无涯”的题中之义了。既曰“学”,则不仅有“说”之心得,亦有“读”之叹赏;至若“无涯”,则不仅有关于少年鲁迅的“演讲”,而且有《〈九三年〉绝对是雨果写的》恁般武断—若谓不信,可以“探幽烛微”那其中的艺术语言是否能有第二位任何人可为?
“走四方”算是心门大开又机缘巧合的近年旅痕。真像韩磊所唱的那样:“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只不过这里的“一村又一庄”似可改为“一篇又一章”;“迷迷茫茫”倒是真的,因为我写的每一篇散文发表后,几乎总是有一种遗珠之“茫”挥之不去。这也许就是“谁”与“不多”之间的那个人的一种毛病吧。
但愿在“散文是会生长”中,我这个毛病和其他一些毛病都能够日渐消弭。为此,我曾《带女儿去“寻根”》,那是对蓬勃之青春的“爱无休”;我也曾到《诗开始的地方》去“浪淘沙”,那是对少年之“母校”的返璞归真。我相信,散文是会生长的,就像人总是在成长一样。我还相信,散文不仅会生长于未来,也会像人一样成长于过去—只要我们善于从过去的“毛病”中吸取教训—不是“我们”,而是我:期待着您的指教。谢谢您阅读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