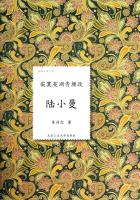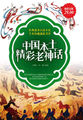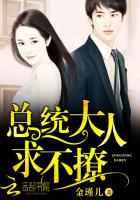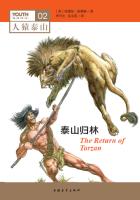岁月悠悠,居也悠悠。在岁月之居里,我曾作东道主飨客,吃的是华屋之梦;我也曾大梦初觉,身处京都而欣然;但更多的时候,我却是静卧己榻,一任那遥远遥远的草房情倏然而至,渐热渐暖地弥漫我的身心……
呵,一个小小的湖,像一只深藏在崇山峻岭中的眸子温柔地向我们飘来。而湖边,就是我们的新居了。茅草顶,泥巴墙,一走进屋内,到处都湿漉漉的,新篾笆床底下还长着青青的小草呢。把我们从北京接到这祖国南疆来的领导怕我们印象不佳,连连解释道:“这房子是为你们的到来刚盖好的,住一阵就不会这么湿了。以后咱们还要盖瓦房哩!”大家对他的解释都没在意,因为我们长这么大,还都没有住过这样的草房子哩。
住这样的房子真是生平一大乐事。看书倦了,翻身而起,往床底一瞧,绿色盈眼,不亦乐乎?一钻被窝,宛如钻进潮湿的雾中,脑子格外清醒,不亦乐乎?正“清醒”时,房顶的茅草中“嘎吱”掉土了,这没什么;忽然,房顶上又发出了“丝丝”的声音—哎呀,不好,有蛇!大家纷起,电光四射—不是蛇,是一只老鼠!它真狂,竟敢在光电的夹击下,就在我们的头顶明目张胆地乱窜。最后,也许是它向我们“示威”够了,一下子窜向了别的屋,翻起的声音立刻又在别的屋子响起—
不亦乐乎?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就在那“不亦乐乎”的茅草屋外面,就在那夜色温柔的一水湖畔,我们曾举行过一个又一个的即兴晚会。记得其中一个是“木瓜晚会”。事前毫无准备,也没有哪一个可以算作导演,但每人一句脱口而出,一首“木瓜诗”便永载我们的青春史册了:
架起一堆篝火,高高地烧起
我们活捉到的毒蛇。
再把摘来的生香蕉全扔到里面,
朋友们:
让我们高唱一曲《国际歌》!
这里还有一个木瓜,
快把屋里的人们全叫到月光下,
让我们共同面向北京城—
请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来尝尝吧!
这首诗现在看来当然是比较幼稚的,但记忆中那种充满了动感的热烈场面至今还令我感到热血沸腾。记得那一晚我们兴奋过度,晚会散时已是次日凌晨了。天上繁星历历,这预示着一个十分罕见的晴天。大家正为此而高兴时,又见月亮渐渐迷蒙了,头上的天空渐渐弥漫了茫茫的大雾,两米以外就看不见人了。大家一边用手电筒乱射迷雾,一边纷纷嚷道:“大自然,魔术师!大自然,魔术师!……”
的确,身居那临时性的居所茅草房中,我们常有被大自然这个魔术师捉弄的痛感。且不说当地半年湿半年干的气候,雨季时的潮湿难耐,就是旱季到来时,偏处西双版纳一隅的那里也并非总是晴空丽日,而是经常热风肆虐,红尘漫天。每逢此时,我们四处漏风的茅草房便成了难以设防的红尘之舟了。于是,“不亦乐乎”遁去,“徒呼奈何”激励我们自力更生盖瓦房。
我们在北京时都曾居住瓦房或预制件楼房,但真要自己动手去盖栋瓦房,却对谁来说,都是生平第一遭。好在我们都是“知识青年”而并非无知识青年,我们不会就学,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于是,一栋新瓦房很快就盖起来了。
然而,我最难忘的,还是在盖新瓦房过程中,在“最后的茅草房”中所度过的每一个白天,每一个夜晚。有诗为证:
草房里的火光,
闪烁在祖国的最西南边疆。
冬天的夜晚冷吗?
不,我们的心里暖洋洋。
暖洋洋,草房里的火光。
一天的疲劳被你驱走;
你跳动着,
多么像我们即将完工的新瓦房……
下石脚的时候,
暖洋洋的火光:
我们这些人里哪个干过呀?
第二层面石愈打愈把汗水淌。
砌出线砖,
真是愈砌愈“出线”。
但是,暖洋洋的火光,
这又怎么能够把我们阻挡?
砌砖柱,还不是一样!
告诉你,暖洋洋的火光:
有的人返工了七八次,
却始终也没有气馁、“缴枪”!
如今,已经开始砌土基墙。
但是,暖洋洋的火光:
滚一身泥巴的日子短,
滚一生泥巴的道路长……
我们还要上屋架、钉椽子、
安玻璃、粉墙;
我们还要更炽热地燃烧自己,
像你一样把天下的草房照亮。
这首《草房里的火光》,就抒写在我曾居住过的那栋遥远茅草房的最后时刻。认真回想起来,我当时在那潮湿而又温暖的茅草房中所写的“诗”还真不少,记得还有一首:
方志敏同志的赤贫,
总在我的脑海里闪光。
踏着革命先烈们的脚印,
我怎能不把这低矮的茅屋歌唱?
早晨,突破乌云,
茅屋里最先射进阳光,
我总感到青春的热情
如澎湃的海洋。
夜晚,寒风阵阵,
茅屋里潮湿阴凉,
我却感到浑身的血管
充满了力量。
茅屋啊,茅屋,
哪里有你天地宽广?
四野的鲜花怒放,
我要日夜把你歌唱。
先烈们的热血不会白流。
新一代的战士正在成长。
茅屋里艰苦奋斗,
革命的理想才能张开翅膀……
这首《茅屋之歌》,像上述《草房里的火光》和《木瓜诗》一样,都是我人生宝库里永不褪色的宝贵珍藏。岁月悠悠,居也悠悠。“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时候逆向思维也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