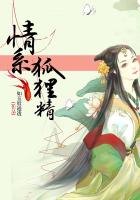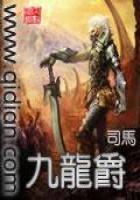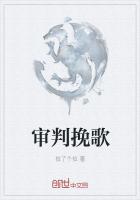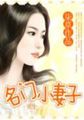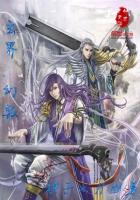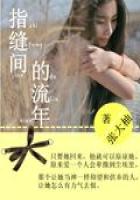四面环山的一爿小店,像镶嵌在赭红色土地上的一颗珍珠,至今还在我绵延不断的情思之中熠熠闪光……
山重水又复,我的遥远遥远的米干店哟,如今你一定旧貌换新颜了。
然而我还是喜爱你那低矮的茅屋,喜爱你那小小茅屋里永远热气腾腾的氛围。就在那米干犹香的氛围之中,我又看到了茅屋一角那油乎乎、湿漉漉的土基灶台。“啊,两口大锅的水都烧开了,老板娘,你上哪儿去了!”
“我么,你看,没人来帮我劈柴,我都得自己干。”老板娘抱着一捆刚劈好的松木柴正走进来,我听出她的话外之音是在责怪我几天没来光顾米干店了。
是呵,老板娘的那爿米干店真难划得清和每一位顾客的关系。就拿我们几个北京伙伴来说,许新源是开拖拉机的,于是就顺道给老板娘捎点柴禾;徐叶明是司务长,每次到县上买菜,都要问问老板娘带什么佐料;而马玉良是个木工,米干店的桌椅板凳一活动了就找他。岂止这几个,当时身处彼地的北京知识青年,哪个不以老板娘的米干店为自己的第二食堂!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部的伙食真是一言难尽,只有记忆中的米干店,进去就香!看,老板娘开始用小石磨磨滇米了,我不由得又上去帮她转起来。磨盘悠悠情悠悠。老板娘在磨眼儿里倒水了,只见乳汁一样的米浆潺潺而下。我急忙又帮着澄滤,老板娘则腾出手来,又把浆舀上一个又一个的大铝盘。上锅一蒸,片刻之后,铝盘上呈现溢满周圆而又平展展的米粉了。其色白而透明;要吃呢,还得掀开,一刀一刀切成面条状,分盛到一个个小碗里,再放上甜酱油、醋、蒜泥、韭菜以及辣椒油、芝麻油等调料——当然不一定什么都放,实际上是老板娘有什么就放什么。但不管放什么都好吃:酸辣适口,爽滑至极。不光我们爱吃,大凡到县上赶街时路过该地的尼人,没有一个不驻足品尝的。
呵,情悠悠,梦未休。远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小小米干店呀,虽然马玉良当时真想为你制作一些桌椅板凳,但可惜的是,米干店太窄小,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过这样也好,和老尼们挤在一起吃米干的滋味儿,更有一番情趣在心头!首先是筷子乐!
尼人多有用手抓吃的习惯,用起筷子来,不是拿反,就是夹不上来,每逢有此难者,我们便放碗相教。好在吃饭小技,并不难学。聪明的尼人一教就会,我们则教会之后再吃自己的米干,更觉温热适口。其次是买东西方便。
尼人多居山上,常猎野味,爱种芭蕉,我们则坐吃米干店中,二者可以兼得。野味种种,无论是珍奇的旱獭皮,还是可口的麂子肉,或者是仅有一尺长的小棕熊,我们常常可以“不猎而获”;至于那熟透了的、鲜黄鲜黄的大芭蕉,尼人常常不要钱地任我们吃,他们笑称这是学“用筷子”的“学费”。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老板娘也是个尼族人。那是有一天我在米干店对面她家里看到一张照片才发现的。那是一张已经被岁月漂得有些发黄的旧照片,照片上的少女头戴一裹小帽,有成串的银饰下垂;双耳挂着两个大银环,面色温顺而略带喜色;垂辫于肩,胸配银饰,裙子系得很高,紧接上衣;脚上穿着一双绣花尖头鞋。“啊,老板娘年轻时好漂亮!”我不禁脱口而出。“旁边那个,就是我爱人。”她故意把“爱人”说得具有“北京味儿”,我这才注意到,原来照片上的尼少女身边,还有一位戎装的解放军!呵,怪不得老板娘汉化得如此彻底,原来……“刚结婚不久,他就打土匪牺牲了。”还没等我发尽感慨,她就径直说道,眼神中略带几分哀伤。我正要安慰她几句,但很快地,她又一下子恢复了常态,非拉我回米干店“再吃一碗米干去”。
呵,米干再好吃,也是人做的;米干店再小,也永远在我的记忆中闪闪发亮—那是老板娘的亲情之光,那是尼人的友爱之光,那是镶嵌在遥远土地上的一颗夜明珠啊!
我为此常作赭红色的梦,常常又置身在四面环山的一爿小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