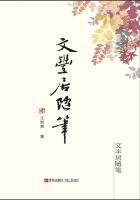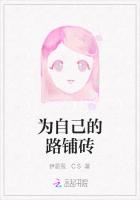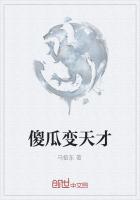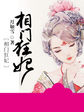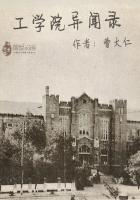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汪老曾祺素以小说和散文名重于文坛,我却看到过、听到过、受赠过他的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汪老写诗确实不多,在其自选集的序言中他曾告白于世:“我年轻时写过诗,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写。”汪老年轻时自然是我年幼时。记得我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曾很偶然地在一本杂志中看到过一组题为《早春》的小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令我眼界大开:“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什么叫形象思维?当时我的年纪自然不会想到这么高深的文学意念问题,只是于混沌中有所顿悟,但后来的悠悠岁月中,只要我一想到或讲到形象思维这个问题,就一定会想到或讲到汪曾祺这两句小诗。我认为“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就是形象思维的最佳启蒙语。
一晃过去了几十年。去年春天,我曾有幸和汪老及其他一些作家同赴云南去参加“红塔山笔会”。记得是在瑞丽的一次烟界人士座谈会上,汪老这个“超级烟民”侃侃而谈时,竟然朗朗上口一首五言诗:“玉溪好风日,兹土偏宜烟。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这是我第一次听汪老当众诵念自己的诗,当时禁不住想起了自己上小学时第一次看到汪曾祺那两句小诗时的情景,心中甚感欣然。当缘分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女郎又一次切近你的身边时,谁又能不如此呢?只是这一次的珍闻之缘,已经由“形象思维”的顿悟,升华至对“汪老风格”的一种独特品味了。再请听汪老自诵诗后的当时告白:“诗是打油诗,话却是真话,在家人也不打诳语。”
一次红塔山笔会,71岁的汪老与同行的冯牧、李瑛等前辈作家和大家相处得极为和谐。这里的大家,不仅指参加笔会的其他作家,也包括红塔山下的玉溪卷烟厂全体职工。去年10月,我又一次赴滇采访时,玉溪卷烟厂一位普通的打字员小张告诉我,自那次笔会之后,汪老竟与之通信不辍,甚至还给她寄去了自己的两幅画,上面还有专为她写的诗。汪老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的稀有继承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自然很想一睹小张手里的真迹,然而行履匆匆,终未如愿。好在可以无憾的是,我归京后未久,就收到了汪老寄赠我的一幅墨宝,上面是一首非常漂亮的“调林栋”:“踏破崎岖似坦途,论交结客满江湖。唇如少女眼儿媚,固是昂藏一丈夫。”这首诗如今就挂在我家的墙上,谁看了谁笑。我自然将笑一生耳。
缘分,这就是缘分。汪老在我心中,永远地首先是一位诗人,一位可爱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