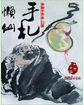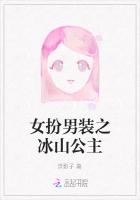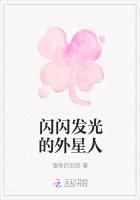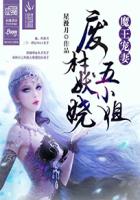广播仿佛离我越来越远了。在最近很全面地写的一篇文章中,历数《唯有传媒笑傲江湖》,其中却没有提到广播!
发现这一点,是在收到刊有这篇文章的《传媒》杂志的第三天,我去参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成立暨中文系47周年系庆校友会”,在会后的饭局中,我昔日的一位大学同窗竟然递过来一张“北京经济广播电台”的名片—哦,原来现在的中国,还有着广播这一行当!
这样说太不恭了,上述文章中的百密一疏也实在是罪不容诛。但广播离我的现在实在是越来越远了,也是我不能不承认并且相信不少人也都有同感的一个“传媒”现实。
其实,广播曾经像电视一样,主宰过我们亿万国人的注意力,但那确乎已经是非常遥远的事了。要不是大学同窗那张名片猛地撞击,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忆起早在上中学时,作为学生会的宣传委员,我曾经是北京二十五中“集体荣誉之声广播电台”的主要操持人,不但撰稿,还播音。
回忆总是美好的。在祖国最遥远的西南边疆“上山下乡”时,我也曾经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一个静谧的夜晚,一个人驻足街头的那个小小三角花园,静静地聆听罗天婵那曲美妙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当然,我们当时每日必听的,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因为那雄壮的乐曲声骤一响起,我们还没有歇过乏来的身子就必须起床了……
那时候,不知有多少个那时候,广播如影随形,是我们生命中的“另一个”。但个体生命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在今天,“古老”的广播或许还是很多生命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起码,我也并不是对花园里晨练老人挂在树上的那个小收音机或打的师傅扭开的那个“交通路况信息”熟视无睹或充耳不闻。但广播于我,真个是自从强势媒体电视取而代之以后,特别是新兴媒体因特网悄然袭来至今,确乎然已经有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
士别经年,当我又见到我那位同窗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说起来我的这位大学好友也是我的中学同窗,他竟然还记得我弄“集体荣誉之声”时曾经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当一个中央级的播音员。啊,他这“如隔三秋”的第二次撞击竟又撞出了我心深处的一种广播未了情。是的,那是一个梦,只不过这个梦早就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我的嗓音具有一种磁性的魅力。这不是我自己的溢美之词,而是在一次学习会上,当我说话以后,在座的一位年轻女同事竟情不自禁地说她刚才入神了,好像听到了某个电影的悦耳配音。还有一次在大街上,偶遇一位半生不熟的中央台女记者,还没说几句话,她就由衷地说:“你说话这么磁,真应该来我们台播音。”像这样的经历还有若干,特别是在更多遭遇的唱卡拉OK时,我的声音从来是有磁性的。这是众人所公认而我也日渐自信的一种“上帝的恩赐”。
但我实在对慷慨的上帝有所辜负。逝水悠悠,生命有所不逮尚不足憾;早知“新桃”可以“换旧符”却未在“旧符”已旧之时有所舞蹈,而仅仅满足于在“新桃”面前有所思,这实在是深有憾意的一种人生未了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