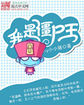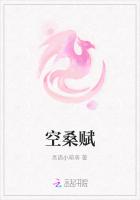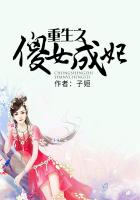说剪报,首先要说:当今时代,尽管电子媒体及媒介的受众日益扩大,但纸媒如报纸的读者亦未见明显的、大面积萎缩。这其间,有相当部分的重叠,亦有不小部分的固守。此或可一喻为当今的中美关系,宽阔的太平洋,当可容二者共存共荣。
既然如此,关于读好报纸、用好报纸的种种方法或注意事项,我们今天仍然有话要说、有话可说。即使是老生常谈,亦可能是常谈常新。
比如剪报。中国的剪报史,当可从有报纸出现那一天就开始了。谁在看报时,遇到有用的资讯或不忍释手的文章,而不顺手一剪,以备再用或再看呢?当然,“顺手一剪”也必须手侧备有剪刀。这也就是说,所谓剪报,必须是有备的行为,而不可能是心血来潮或什么“下意识”。这一点认识很重要,它告诉我们,有“剪报”的意识,就是对读好报纸、用好报纸“有备”。相较于那些有眼无心、只是对每天的报纸“随便翻翻”的人,这些“有备”的读者显然更成熟、更理智,他们对报纸的态度也显然更尊重、更珍爱。
这种对报纸的尊重与真爱,是我们“说剪报”首先要提倡的,它是我们读好报纸、用好报纸的必要前提,非如此不能进入每日报纸的丰富之门。
当然,我们读好报纸的唯一目的还是要用好报纸。但考究中国剪报史,所谓读以致用,其实也还是有客观需要与主观需要两种情况。前者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勃兴,甚至催生了一种“剪报产业”—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资料中心,陆续印制出版了很多种剪报刊物,公开发行,十分畅销。当时还真有很多读其剪报、用其剪报而发家致富或企业大发展的例子不断见诸报端。后者如国内外的很多著名学者、作家等,他们或因有主观意念而开始不断地搜集相关资料,或因只是对某些资料感兴趣而逐渐清晰了某方面的写作计划,而剪报,就是这两种资料收集的必经之一途。比如李敖,他不仅剪报,还剪书!他能写出那么多类别迥异、知识新颖的书来,跟他有过人的资料收集功夫十分有关。在他异乎寻常的家里,到处都是井然有序的书报刊等各种资料。那就是他的独家之秘、写作宝贝。这其中,除了书籍以外,不断收集来的剪报(及剪刊剪书等),当占相当一部分。
但是,天下能有几个李敖?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我们注重于做好剪报,用好剪报,倒不一定非要著书立说,只要能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加强我们的文化素养即可。
准此,我们或可在“当代剪报人群像”中各择一位,只要能入列其中即可。
其一为“权宜”之剪者。诸事缠身,时间有限,真是不能静下心看刚来的报纸,可又不愿一时错过有趣或有用的资讯或文章,亦不愿一大摞报纸总在眼前压着或压至明天变得更多,那就抓紧时间“扫”吧!而在“扫”的过程中,只能把那些“打眼”的标题或具“朦胧美”的文章剪下来,留待有暇或静心时再看—当然还是要抓紧时间,只不过可抓紧另外的时间了。这就是“权宜之剪”—你能对号入座吗?
其二为“只为下一次相逢”而剪者。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看报时遇到某些文章或因其内容或因其文采或因其他如标题、某句话等等,虽不属一见钟情,却也不舍弃之如路人,怎么办?那就剪下来吧—即使只是为了下一次相逢。相逢因为曾相识,相弃因为曾相知。热衷于做剪报的朋友,你能于此“对号入座”吗?
其三为因其“有用”而剪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纸就是我们每一位读者的学校,而且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学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资讯,如政府的政令法规、市场的消费信息,以及看病就医、文艺演出等等,都可以在每日的报纸上看到。而有时候,你不剪报则必有错失。此类“剪报”是很多人都做的,你肯定也能“对号入座”吧?
其四为“欲荐别人看”而做剪报者。谁没有亲朋好友?谁不愿热心助人?有时候,你在报上看到大有益于某熟人的文章或资讯,情不自禁地就要操弄剪刀留存下来,以便推荐或提供给某熟人看。这是常有的事,甚至有的剪报朋友还乐此不疲—你能“对号入座”吗?
其五为做剪报如“收藏奇珍异宝”者。这种人做剪报特别认真,特别细致,大多专备一册,凡入册者皆视为终身伴侣,百般恩爱。当然,这些“奇珍异宝”亦自属货真价实;收藏这些“奇珍异宝”者亦自属剪报佳人。亲爱的朋友,真希望你能对此号,入此座!
剪报世界,气象万千。上述种种,只不过是初始一列。但与此相悖者,亦不乏见,例如“剪而不读”者,或束之高阁,或藏之名山,又管什么用呢?更有“不注意更新”者,连“蒸汽机时代”的种种剪报还珍藏着呢—这似乎也没什么必要。更可怕亦更令人扼腕的是:不断地剪,却从来也不看,到最后剪报成灾,只好卖废品了事—岂不可悲也夫!
既然报纸的事业还在一如既往地发展,我们广大读者的剪报习惯就应该继续保持与坚守,就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因为这不仅是报纸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必要理由,更是我们每一个人获取优等知识,提高生存质量,以自身的不断进步来推动我们“文化立国”的一个必须。我们每一位读者,都应该为创造一个“文化中国”而更高地举起“剪报”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