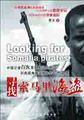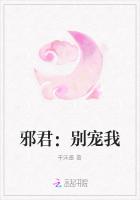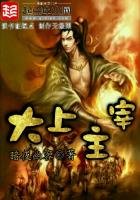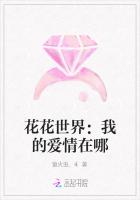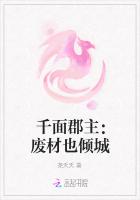在学习领域,值得深说的内容其实比很多人意识到的都要多,例如日记,例如日记之空白。
坚持写日记是尽人皆知的一个好习惯。但既乎尽人皆知,如果你在“百度”上进行“日记”搜索,据说那“答案”有“无数条”之多。这就确乎有一个问题:相关日记之“尽人皆知”,是耶?否耶?
以“日记之空白”为例,难道不应该“深说”一下吗?
一般人的理解,“日记之空白”即是那时疏懒,不过是“人性”之一种,何必深究?更有此众的年轻人十分推崇孙燕姿的那曲《相信》:今天日记空白没有关系,不必每件事情都在意。
此种于“日记之空白”一事上的“不在意派”,不能说有错。他们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权利。他们知道弦绷得太紧也许会断。他们中知识细胞更丰富的一些人甚至知道,生命就应该“留白”,否则还有什么艺术趣味!
但是,像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于“日记之空白”一事上有“不在意派”,就一定会有其“在意”一派。而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零和游戏,实为对立统一。这就像人性中既有疏懒之时,也一定会有奋进时刻一样。无论疏懒还是奋进,都是我们每一生命个体在日记这个特殊载体上最自然而然的真实呈现。
且看在《鲁迅日记》中,他是怎样处理1932年1月31日以后之“空白”的:“二月一日失记。二日失记。三日失记。四日失记。五日失记。”一直到“六日旧历元旦。昙。下午全寓中……”这“失记”是什么?是记还是没记?是空白还是不空白?
这说明,“日记之空白”与“不空白”实具不可区隔的有机联系,这就像“在意”与“不在意”实属对立统一一样。或可曰,世界上只存在写日记派和不写日记派这两种,不在意“日记之空白”者,其实只是“写日记派”之疏懒一小支。
但千里大堤,有时候也会溃于蚁穴。疏懒固不可耻,但也仅止于可解可谅而已。相较而言,作为“写日记派”的可靠质素,还是以提倡一丝不苟为要。
这当然很难,但人生的至高追求不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吗?一丝不苟地坚持写日记,其实也是一种“只要肯登攀”的青春意趣。人生之趣,莫过于“当我们年轻时”,或指点江山,或潜龙在胸—
而这“潜龙在胸”,不坚持写日记,又怎么能做得到?又怎能够知己知彼,将来百战百胜?
这“将来”,并不仅指于可能的战事一端,更指我们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千难万险。
的确,若论人生,一个人的成长宛若在一条必由之路上艰苦跋涉,深一脚,浅一脚,泥一脚,水一脚,痛一脚,痒一脚,等等,若不坚持每天写日记或经常地写一些日记,又怎能“甘苦寸心知”?又怎能“吃一堑长一智”?又怎能变“事后诸葛亮”为“事前诸葛亮”?又怎能……可以说,坚持写日记,就是坚持在自我创造的一所秘密学校里,坚持自我批判,坚持自我升华,坚持自我完美。想一想,人生苦险又苦短,这一“自我坚持”的求索精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必要又必须啊。
以笔者而言,一直很佩服那些终生写日记者。而年近8旬的一位前贤即是这样一位可敬可佩之人。这从他以前和近日赠我的多种著作中即可得到明证。那些白纸黑字的著作中,不仅有显而易见的“日记”,还有他事无巨细全保有的“书信集”,还有他纯纪实其一生的“长篇小说”,以及他毕生“写真”的作品集,等等。我粗浅计算了一下,这些“作品”总共约有2000多万字。而其中有少许文字,竟与我曾经历过的一段文学活动有所重叠,因而我能感受并判断,他所记叙的那些人和事都是真实无误的。这种感同身受的复合印象,使我对这位前贤“终生写日记”的判断与敬佩,既确凿无疑,又无以复加。
在中国历史上,对“终生写日记”情有独钟者,实不乏其人。经学家俞樾认为日记起源于东汉,如刘向《新序·杂事一》中有记:“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又如司笃伯《封禅仪记》即已逐日记叙登泰山之事。及至两宋,中国之日记进入繁盛期,陆游和范成大等,均是影响深远的日记名家。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三尚有记载:“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缀书。”清代李慈铭日记逾百万字,薛福成有《出使四国日记》,梁启超亦有《新大陆游记》,更有《曾文正公日记》,等等,均是影响至今的名人日记。民国时期的名家日记,更是灿若群星,辉耀当代。
于此确凿无疑。我们又怎能对“日记之空白”“不必……都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