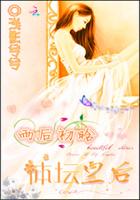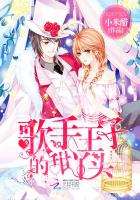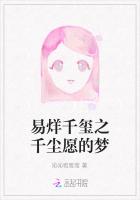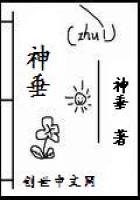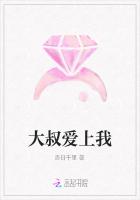在我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目前的专业布局中,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一向隔膜。我有时纳闷,为什么非要把研究中国语言的人和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放在同一个学术单位呢,既然他们这样老死不相往来?
治文学的人偶尔也会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做一点文体学或风格学研究,但面对专门的语言学研究仍然感到头痛,视为畏途。治语言学的人,虽然知道很勤奋地到文学作品中寻找“语料”,偶尔也会像文学研究者那样谈谈某位作家的文字风格,但若要他将这种研究落实到文学史的系统考察,他多半会以专业分工为由,敬谢不敏。
但大家都知道,在文学和语言之间存在着可以亦亟待开垦的一个开阔的中间地带,任其抛荒,双方都有莫大的损失。可见文学与语言学的隔膜并非研究者心甘情愿,实有某种不得已的苦衷。
这里恐怕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
首先,迄今为止,在我国学术界还没有建立一种大家共同认可的将语言和文学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适当的方法论。文体学与风格学固然是经常运用的方法,不过须知,文体学和风格学乃是学科边缘相当不清楚的传统的美学范畴和相应的文学批评模式,很难适应现代学科日益细化的知识谱系。语言和文学研究者同时倚重文体学与风格学,恰恰说明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匮乏。
其次,现代学科的细分,往往诱导人们将某些明显的退化误认为进步。比如中国古代以文字训诂为主的“小学”不仅作为全部人文研究的基础,也几乎包揽了全部人文研究的领域。而在现代,“小学”日益收缩,最后退回到传统的文字训诂(相当于目前汉语言专业古文字方向),这固然是学术进步,但语言文字研究对人文学科的根本意义和普遍的指导价值也渐渐隐没,以至于不仅文学研究,甚至某些摩登的语言学研究,都公然把语言文字知识的缺乏不当回事。一大批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历史和现状缺乏起码知识和感受力的学者混迹于甚至把持着人文研究的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滑稽的学术悲剧。这种情况,就好像一大帮外乡的陌生人闯进某个家庭而以主人自居,俨然谈论着家庭的各项事务。
“次殖民地”·“语言游戏国”小批判集其实在中国现代,语言文字学仍然充当着人文学科的基础。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许多治社会史、考古、文学、哲学和艺术史的学者本身就是优秀的语言文字学家。古事弗道,即以中国新文学而论,其开端就是一场特殊的“语言学转向”。略具常识的人都知道,“五四”前后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是一场语言革新运动。不仅中国新文学随着中国的新语言文字一道成熟,对新文学的反省也始终围绕着语言文字问题展开。“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胡适)无论对新文学还是对新的汉语言文字之学都是有效的价值公设。在现代中国,谈文学而不涉及汉语言文字,谈汉语言文字而不涉及文学,都是不可思议的偏枯。在现代语言学界之外,语言之谈论,也蔚然成风。从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刘大白这些“五四”元老到郭沫若、陈望道、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郭绍虞、冯至、朱光潜、巴金、陈梦家、钱锺书、胡愈之、李长之、胡风、聂绀弩、周扬、胡乔木这些继起者,无不终生究心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新生与新文学发展的血肉相连。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有专文和专著讨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和语言。
在新文学界内部,有关语言的思考也绝非像通行的“现代文学史”叙述的那样到胡适为止。实际上,胡适仅仅发动了第一轮进攻,在他之后,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反思和深化才是一个更加精彩的持续的思想运动,并且形成了值得后人认真对待的学术传统。
当代学术界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现代学术传统的意义并自觉地加以继承呢?这只要想一想80年代中后期,以西方哲学研究界为首的人文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所谓“语言学转向”大表惊诧,兴奋莫名,奔走相告,就略知一二了。
我岂敢嘲笑西方哲学研究界(简称“西哲”)及其跟风者少见多怪,又岂敢指责他们数典忘宗,只是想强调一点:紧紧抓住语言文字问题,紧紧抓住近代以来备受震荡和迫压之苦并在震荡迫压中走出无路之路的汉语言文字,以此为元问题辐射开去,致思现代文化乃至现代社会诸问题,本来就是“吾家常事”,就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界无须烦琐论证的共识。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给了我们不少启发,但这种启发对我们自身的现代性问题的揭示,恐怕远远赶不上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界上述共识所蕴含的思想遗产——如果今天这份遗产果真被发现并加以妥当利用的话。这是我们省思自身问题时所积累的学术话语,所探索的方法论。它不是悬空、外加的用过就丢的工具,它本身就启示着一种道路,是从我们生命内部发出的呼喊。这样的道路与这样的呼喊一旦被指明,一旦用通行的话语翻译出来,后来者应当更容易心领神会。
80年代中期至今,国中陆续有人赓续“五四”话题,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举其大者,有作家汪曾祺访问美国时大声疾呼汉字对汉文学的决定性作用;有“九叶诗人”郑敏在20年代末期《学衡》杂志即予介绍的欧内斯特·范罗诺萨启示下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正面反思;有申小龙对现代学术史上围绕《马氏文通》一段公案的重新检讨,以及后来备受争议的“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相继提出;有作家李陀对毛语的灵感来袭的研究;有刘禾对“国民性话语”的重述与“跨语际书写”的视野拓宽;有王一川基于自己对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理解而执著探索“现代汉语的形象”;有汪晖对“民族形式讨论”中地方土语的再讨论;有老学者任洪渊先生对现代汉语诗歌问题独到而才气焕发的阐发;有高玉对现代文学发展中语言问题的系统整理。近代汉语研究界,意大利青年汉学家马西尼对现代国语成立与外来词的研究,周振鹤、游汝杰对近代中国“语言接触”(特别是传教士汉语学习与《圣经》汉译)的研究,也使人大开眼界。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有关汉语问题的争论就更加丰富了,许多批评家对于林斤澜、汪曾祺、王蒙、莫言、韩少功、李锐、孙甘露等独特的语言形式的研究,越来越显示出与现代文学和现代学术界的语言问题的有机关联。
所有这些研究,应该都是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逐渐复活的我国现代文化界上述遗产交相为用的结果。这类研究超越了孤立无援的美学的文体学或风格学,真正进入历史研究的领域。其中现代汉语和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无疑是全部问题的最突出的焦点,而这正是“五四”元勋们主要思考的问题。历史转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开端。
文贵良博士的新著《话语与生存——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应该放在此一学术史序列中,才可以让读者更好地来“解读”。我觉得这部书最大的特点也可以说最大的成功之处,首先还不是著者喜欢戛戛独造因而往往奇崛生硬的术语,而是他给自己的研究预先设立了一系列限制。
海德格尔说过,“谈论语言有时比谈论沉默还要危险”。这是真的。语言无所不在又四通八达,盘根错节,你以为找到了某个蛮不错的角度,兴奋无比,跃跃欲试,可进去之后,走不多远,就会歧路亡羊,莫辨南北。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不举也罢。我本人尽管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意识”一直感兴趣,但至今仍然停留在感兴趣的水平,不敢造次,生怕应了那句学者们最讨厌也最害怕的老生常谈:“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更糊涂了”。这种痛苦我想贵良也没少尝,但他没有畏惧,持之以恒,并多少找到了克服困难的办法:限制语言研究的角度,以确保自己不至于迷失在语言问题的歧路上。
首先,他把研究范围严格限制在1937—1948战争年代的中国文学。这一时间段的截取,吸收了陈思和先生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战争文化心理”的论述,以及钱理群先生后来对“天地玄黄”的1948年文学论争的分析。事实证明,这一限制非常必要。尽管他在讨论战争年代中国文学及其特殊“话语”时也频频涉及战前与战后,但这一切莫不围绕战争时期特殊的语境展开,他的全部论述因此有了一个坚定的核心。
其次,他明确指出自己所从事的是“话语”研究而非一般的“语言”研究。在开始研究之前——确切地说是在研究的全过程直至完成研究之后——他认真梳理了“话语研究”的学术谱系,宣告他的“话语研究”方法论,不是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分离,和他主要依仗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理论也不尽相同,因为他还吸取了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思想,在“话语研究”中突出话语(言谈)主体的存在状态。他把这种合并福柯与海德格尔的研究思路称为“话语生存论”,书名也叫《话语与生存》,其方法论的自觉,可见一斑。
最后,在“战争”和“话语”两层限制的基础上,他又顺理成章地提出第三层限制,或者说第三次聚焦。他的全部阐述,始终以战争年代中国文学话语的三位标志性人物——作为政治话语主体的毛泽东、作为虚悬的大众话语主体的赵树理、作为知识者话语主体的胡风——为中心,依次分析这三个话语主体的生成历史、话语特点和“存在之状”,并进一步探索三种话语如何从战前的并置关系合乎逻辑地发展到战争期间和战后不可避免的互相渗透、彼此冲突、残酷绞杀直至强制同化的关系。
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和精彩之处,就在这里。
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在阅读过程中经常觉得,他对战争年代文学的分析,虽然归结为“话语与生存”,但许多内容又不能完全局限于“话语与生存”。如果用其他的方法(包括文学史研究的通常方法),好像也可以达到相似的结论。比如,关于毛泽东作为政治话语主体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宣告确立的过程,在高华、黄昌勇、朱鸿召、袁盛勇等学者对“延安整风”与“延安文学”的研究中已基本成型;至于赵树理的在民间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虚悬主体,在众多的赵树理研究特别是陈思和有关民间/庙堂二元结构的论述中,也颇为清晰。既然如此,“话语生存论”的特殊贡献如何能够崭然显露?
我想这不能怪贵良的“话语生存论”在方法论上不够完善,主要还是中国学界在横移福柯、海德格尔等西方学者创生于西方学术文化特殊语境的理论模式时,急于为我所用因而难免削足适履的风气有以致之。
我由此想到,在中国现代,“话语”生产还有另一种或许没有被贵良充分意识到的看上去并不严肃也并不正经的方式。事情也确实不一定像贵良设想的那么严肃正经。大多数情况下,话语的移植并不等于思想的共鸣,倒会带来思想的混乱。话语的繁殖也决不等于思想的增长,倒容易产生思想的混乱。
这是文化史、文学史和学术史经常出现的情形,现代中国这种情形或许更加明显,因为现代中国,按照胡适之的说法,是一个尚未脱离“名教”的国家;按照周作人的说法,是一个带有萨满教的相信语言的力量的半野蛮国;按照冯友兰的说法,是一个特别能够生产文字概念的国家;按照鲁迅的说话,不仅是“文字过剩国”,更是“文字游戏国”;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是一个在语言文字上特别不自信的“次殖民地”;按照胡风的说法,是一个喜欢“坐着概念的飞机去抢夺思想竞赛的锦标”的典型的东方后进国。在这样的国度,思想的英雄也是文字的巨人,思想的侏儒也是文字的矮子。所谓思想,诚如闻一多在研究《庄子》所指出的,并不在文字之外,就在文字之中。没有离开思想的文字,也没有离开文字的思想。文字是思想乃至情感、幻想、憧憬和狂热的现象学在场的图景。因此,那种试图由表及里发现文字游戏背后的思想、权力、政治的过于严肃的话语分析,反而容易被无处不在的文字游戏所欺骗。勇敢而智慧的话语分析或许毋须深求,反而恰恰要戳破文字/思想或思想/文字并无深度可言的公然的游戏本质,不可堕入游戏之中,去追求文字游戏背后并不存在的深度所指。
举一个例子,当大家都被各种进入中国的其势汹汹的“主义”闹得头晕目眩时,鲁迅却认为这些“主义”并没有“来了”,“来了”的只是“来了”,只是被这些“主义”、“旗号”所激起的一阵又一阵无谓的思想波动而已,甚至只是关于什么什么“来了”的传闻、谣言、恐吓、欣喜或一般的消息报道罢了。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鲁迅才很少正面对待进入中国的各种主张,而习惯于分析和解剖在中国推销各种主张的人士所怀抱的目的、所采取的方式对于现代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这种很不正经的“话语分析”,不是也能从一个角度打中要害吗?
因此我觉得,对毛、赵、胡三位的“话语”,贵良的分析还过于注重语言背后权力、政治、体制、组织、生存处境和思想、意志以及个性这些其实并不难看清或者应该交给其他历史学科来处理的因素,而对语言本身的移植、繁殖、灌输、生造、大规模游戏的实情,倒有些轻忽了。
贵良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一开始,他就强调话语分析不能离开语言层面的考察。事实上,无论对毛的政治话语还是对赵的大众话语,他都力所能及地考察了他们“向外”的用语方式。至于对“言用者胡风”特殊的“置身”性的语言风格和具体用语习惯乃至他的“语言创伤”的考察,更是本书闪光耀眼之处。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不够充分。至少按照贵良的知识积累来说,还可以做得更好。我记得贵良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讨论李佩甫《羊的门》和韩少功《马桥词典》的“话语”,非常精彩。他在分析当代文学的“话语”时,是否比分析现代文学的“话语”时,有更多的自由度呢?抑或他所服膺的福柯、海德格尔的话语理论与基础存在论过于繁杂的概念范畴本来就容易束缚中国学者的手脚?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话语分析”,固然可以借鉴福柯或海德格尔的方式,但是像奥维尔那样在小说或随笔中自由地描绘“新说法”(New Speech),或者分析“政治学与英国英语”,也同样值得借鉴吧?我觉得,相对于福柯和海德格尔,奥维尔的方式对于分析中国话语的中国学者来说,运用起来或许更加得心应手——而且恐怕更适合我们这些从文学专业贸然跨进语言学领地的不安分者。
这也许是吹毛求疵,也许完全出于我对贵良的学术追求的无知。果如此,那就要请贵良原谅,并有以教我了。
这本独特的著作的更多内容,著者文字俱在,不劳我来笨拙地转述。书稿放在我这里将近两月,如果从接触原稿(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算起,则差不多三四年过去了,但有些章节我至今仍然不能完全懂得。现在就把这些不能完全懂得的地方提出来,相信贵良是不会以为太过悖谬的吧。
2007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