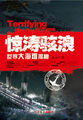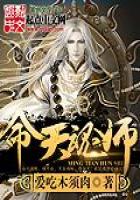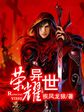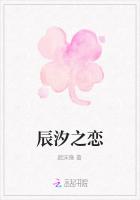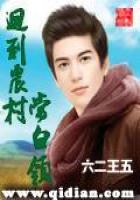第一期《艺术旬刊》(以下简称《艺术》)诞生于1932年9月1日。朴素的本色封面上,在刊名“艺术旬刊”四字下方,选配了一幅野兽派风味浓郁的人体素描。底下注明了: 每月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月三期;编辑兼发行者: 摩社编辑部。一册只有薄薄的二十页,包含了五篇主要论文: 《中国艺术界的清算》(李宝泉)、《梵高的热情》(刘海粟)、《现代法兰西的美术工艺》(陈之佛)和《现代绘画的精神论》(倪贻德);一篇画家随笔: 《薰琹随笔》(庞薰琹);一篇解释“Muse”词源词义的《摩社考》(张若谷);以及一篇以画家个展为对象的艺术批评《刘狮个展概评》(倪特)。刊中含四页插画,选登了六幅画作,分别是: 梵高的《风景》和《林》、马蒂斯的《人物》、克斯令的《肖像》、夏葛尔的《诞生》和佛拉芒克的《街道》,虽然只是黑白印制,但采用铜版纸精印,纸张和印刷质量都相当细腻雅致。此外,还有几处展览预告、征稿规约之类的补白及最后的“编辑者言”。通篇看来,此刊篇幅虽小,五脏俱全,且编排紧凑,图文并茂,品位不俗。浏览之余,好奇的读者最关心的可能是诞生它的“母体”: 何谓“摩社”?
创刊号中虽有《摩社考》一文,但作者张若谷只交代“摩社”乃“Muse”一词的法文译音,具体解释了古希腊神话中九尊“摩社”(文艺女神,今通译缪斯)的不同形象和含义,指出:“中文的解释,便是‘观摩’的意思,摩社的宗旨是发扬固有文化,表现时代精神。”可是,作为刊物编辑兼发行者的“摩社编辑部”,又是什么来历和构成呢?
针对这个疑问,编者倪贻德(尼特、倪特)在旬刊第2期“编辑后记”中做了补充性的说明:“摩社,是最近成立的艺术团体,也就是产生本刊的母体。”并详细报告了摩社组织的经过和概况:去年冬季,我从武汉回沪,会见海粟先生。我们谈起国内艺术界的消沉的情形,以及企图发展的计划。他说:
“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志,有一个华胥社的组织,曾经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个华胥社文艺丛刊。现在我们不妨将他扩大组织,出版定期刊物。这是在中国现艺坛很需要的事情。”
我说:“编辑艺术刊物,我也早有这意思。中国艺术界现在真很需要这样的刊物。我们的学识虽然尚属有限,但我们不来干,更有谁来干呢?”他们原计划于次年(即1932年)春创刊,但受“一·二八”沪变影响而搁置。直到“7月中旬的某晚,集合同志十数人,在辣斐德路496号海庐的大门前,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对于社的命名及宗旨,讨论很久,结果推举刘海粟、王济远、傅雷、庞薰琹、张弦和我六人为社章起草委员,再定期举行成立大会”。“8月1日,假中华学艺社举行成立大会,通过社章,定名为摩社。”摩社成员,除了上述六名社章起草委员外,还有关良、王远勃、吴茀之、张辰伯、周多、段平右、张若谷、潘玉良、周瘦鹃等。
从摩社的发起来看,它主要“是因了编辑刊物的动机而组织的”,是刘海粟1929—1931年间第一次赴欧游学考察时组织的华胥社的“扩大”,而后者本身只是一个较松散的文艺团体,集合了一些积极引介西方文化、亦不忘宣传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留学生和文艺界人士。“发扬固有文化,表现时代精神”这个相当宽泛的宗旨,摩社也一并沿用。摩社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社章并未在《艺术》和其他媒体上发布,无从作进一步的分析。细分该社的构成,基本上由三方面组成: 由刘海粟领导的上海美专师生(刘海粟、倪贻德、王济远、傅雷、庞薰琹、张弦、关良、潘玉良)、决澜社部分成员(倪贻德、王济远、傅雷、庞薰琹、周多、段平右)和新闻媒体友人(张若谷、周瘦鹃)。其中,倪贻德、王济远、傅雷、庞薰琹四人,既在美专任职,与刘海粟关系密切,又同为决澜社的重要成员,属于二者叠合部分。而这三方面人员对于艺术的基本主张应是一致的,即尊重本国的历史传承,同时对西方现代派艺术抱以肯定和欢迎的态度;但各自怀抱的具体艺术观念,在激进程度上却呈现出分歧和差异,既揽括了周瘦鹃这样带有旧式文人气息的人物,也包含了艺术态度最为激进、反学院派最决绝的决澜社领袖。有意思的是,检索《艺术》的全部要文篇目,出自倪贻德、傅雷和庞薰琹三人之手的文章,竟约占半壁江山——倪与庞同是决澜社的发起人,傅则是决澜社的支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名义上作为摩社“喉舌”的《艺术》,实际上更像是决澜社核心成员同心协力、精心耕耘的园地。而办刊的经济支持,从上段关于摩社成立经过的描述来看,虽未详细说明办刊经费来源,但刘海粟及其领导的美专应是主要赞助人(《艺术》也因此易被误解为美专校刊),这一层微妙的不对称关系,可能是导致《艺术》只维持半年便遽然告停的原因之一;当然,最本质的生存难题,还是先锋艺术杂志不容于商业市场的先天障碍,即便背后有雄厚资金的长期支持,又无碍于杂志的独立性,编辑集体能否保持其叛逆的激情和不断突破的性质,也是一个极难预料的因素。
创刊号是开宗明义、发布办刊目的和宗旨的必然之地。在第一期末尾的“编辑者言”中,编者说明了为何创办《艺术》: 首先,是为“艺术”的重要性进行辩护,驳斥“艺术太空洞而不切于实用”论,表示“我们固然应提倡科学,但同时也不可忘记了艺术”。科学的实用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艺术的功用表现在哪里呢?编者以奥林匹克竞赛和日本的文化宣传为例,指出:“在现代,一个国家在国际地位的高低,不单在财政军备的强;文化的优劣也有极重要关系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同法国政府艺术部门合作,多次举行交换展览,并分别于1930年、1931年在法德两国举办了精心筹划的日本画展,以彰显其跻身世界强国的文化传统和实力;富于东方情调的日本艺术,也确实一度令欧洲人大开眼界,啧啧称赏。可想而知,日本政府这一来势汹汹的文化宣传攻势,极大地刺激了敏感的中国人,尤其是长期自生自灭、犹如一盘散沙的中国艺术界。正在欧洲游学的刘海粟目睹了日本画展在巴黎的盛况,他的反应和态度很有代表性:日本文化史极短,绘画亦袭吾国之皮相而已。然近年来欧人大呼日本新兴美术,一般浅见者流,每谈东方艺术,且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日人且挟其数笔枯淡无韵之墨线,称雄欧洲艺坛。欧人好奇,观其画面细弱之线条,每相惊告曰,此具有东方人单纯怡静之趣味者,非欧人所能为也!其实数笔优柔之墨线,在吾国画坛任何人皆能为之,何奇之有?真正刺痛了国人神经的,倒不是日本艺术本身的高低,而是日人通过政府行为,趁机推行文化策略,大张旗鼓地树立自己东方文化之代表的形象,又恰好迎合了一战后欧洲知识界、艺术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与想象,而这无疑令向以东方文化古国和老大自居的华夏民族自尊严重受损,国人在震惊、鄙夷之余又心犹不甘,迫切要求以同样的方式自我澄清和证明——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个衰落民族自信不足的症候?《艺术》特别提出这个在当时普遍激起“民愤”的事件,以明证“艺术”的“实用”,理直气壮的同时亦有几分无奈: 不把艺术和政治、国家、民族捆绑到一起,似乎就无从落实其自身价值了。单从开头的这层辩白,已经能看出,在当日情境下“艺术”及其衍生物《艺术》杂志“合法身份”的来之不易了。
那么,《艺术》的职责和任务是什么呢?中国艺术界当前的问题,不在量而在质。读书不求其解,只学得一点皮毛便津津自足,这是我们民族性上最大的缺点。我们的艺术之在质的方面没有进步,怕也是这个原因吧。……我们只希望: 在艺术的质的方面,再优秀一点,再深进一步。……本刊的产生,可以说就是为了这一点动机。我们不想视艺术为至上万能的东西,也不想宣传以艺术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更不欲高唱民族主义艺术的高论。我们只想脚踏实地地,灌输一点新鲜的,切实的知识于一般爱好艺术的青年,给开辟一条研究的道路,同时也企图使大众能渐渐和真的艺术接近起来。这段宣言的语气看似谦逊低调,其抱负却是何其远大!他们希冀的是,能克服“民族性上最大的缺点”,在“质的方面”推进艺术的深入发展;同时,他们又和三种时下流行的艺术论调撇清关系,将自己放置在艺术知识输入和普及的初级阶梯上;然而,“开辟一条研究的道路”、“使大众能渐渐和真的艺术接近”,这岂是简单的“灌输知识”所能实现的目标?正如当初筹办之时倪贻德踌躇满志的言语:“我们的学识虽然尚属有限,但我们不来干,更有谁来干呢”,字里行间都是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概。不难看出,从一开始,《艺术》的编撰群体就满怀对“真的艺术”认识在握的自信: 所谓“真的艺术”,与世俗的几大意见截然不同——既非至上万能的神话,亦非阶级斗争的工具,更不囿于民族主义的狭隘——在这三者以外,另有“真的艺术”在,而他们急于做和最想做的,就是将这种艺术理念加以彰扬、推广,将惯于蒙蔽大众耳目的各种成见谬议一一剥落,引领大众走近“真的艺术”,从而使得中国现代艺术发生质的变化。至于这种“真的艺术”究竟如何,我们将在《艺术》刊载的主要论文中去作进一步的辨识和分析。
最后,编者列举了内容编排上的规划,一共有五个方面:“现代艺术的介绍”首当其冲:艺术不能离开了时代精神。20世纪的艺术,在随了时代思潮激急地进展着,而我们的艺术界还好像一个跛行者落在人家数百码之后。我们纵不能作一个时代的先锋,也应当加紧脚步追上去了。其次是“古的艺术”,但强调,“须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去估衡古艺术的真价,使读者作为研究上的参考”。
第三是“国内艺术界的批判”,“今后当尽我们的力量,以公正的态度,加以严格的批判,以期引得艺术界于纯正的本道”。
第四是“方法论”,主要指“技法上的修养”,“本刊以后每期拟另辟新美术讲座一栏,特约各科专家,以最新之各种技法论,介绍于读者”。
最后,“多载名作”。针对一般研究者与西洋名作基本隔绝的最大“憾事”,“本刊以后每期当尽量登载各时代的世界的代表作品,制版务求精确,以引起读者的兴味”。
实际上,纵观各期《艺术》,其用力最勤的就是“现代艺术的介绍”、“国内艺术界的批判”和“多载名作”三项。而这三项工作,归根结底,都是围绕阐明和倡导现代艺术精神展开的,直接导向“真的艺术”之本质。
创刊号末尾的“本刊征稿规约”,则明确表示了不欲成为同人杂志的立场: 欢迎来稿,范围界定在“关于艺术之评论,译述,随笔,杂感,及文学创作,艺术界消息等”;不过,“来稿发表后暂以本刊为酬”,又注定了来稿人只能是不计物质回报的志同道合者。事实上,《艺术》只在读者来信栏目中发表过外稿,基本上还是维持了同人杂志的性质,尽管这并不是编辑者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