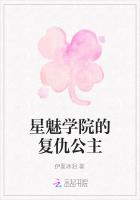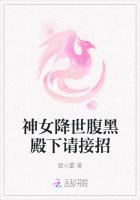1919年1月,曾“时刻警觉着,寻觅大有潜力的新作者与任何可能的突破口”的陈独秀,以“美术革命”为题,在《新青年》6卷1号的“通信”栏里刊出了一封读者来信及自己的回复。此时距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刚好两年,而陈独秀顺势“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倡导以“革新文学”为起点向“革新政治”进发,亦不过是一年多以来的事。从文学改良、文学革命进而“建设的文学革命”、“人的文学”,这场讨论已逐渐激起社会尤其是青年的热烈反应,“革命”一词的出现日见频繁——是怎样的来信,让陈独秀“不胜大喜欢迎之至”、继而迫不及待挂出“美术革命”的旗帜呢?
来信人是二十三岁的吕澂,名画家吕凤子的胞弟,两年前留日学习美术归国后,曾担任私立上海图画美术学校(1920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务长,从事美术史和美学研究。正是在《新青年》“改革文学”热浪的鼓舞下,吕澂提出了美术“尤极宜革命”的主张,并从学理和现实要求两方面申明理由。在学理上: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唯一,势自不容偏有荣枯也。同时,现实生活中“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姑就绘画一端言之: 自昔习画者,非文士即画工,雅俗过当,恒人莫由知所谓美焉。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业;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乃俗士骛利,无微不至,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驯至今日,言绘画者,几莫不以此类不合理之绘画为能。充其极必使恒人之美情,悉失其正养,而变思想为卑鄙龌龊而后已。乃今之社会,竟无人洞见其非,反容其立学校,刊杂志,以似是而非之教授,一知半解之言论,贻害青年。吕澂对本国艺术传统中美学研究的缺失、西画东输后流于庸众、趋向低俗的传播混乱,以及民间美术学校教育的浅薄谬误、误人子弟诸情形,表示出最大的忧虑,“诚不可不极加革命也”。而关于“革命之道”,如同当年胡适在通信中简拟的“八事”,吕澂也提出了“四事”:革命之道何由始?曰: 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使恒人晓然美术所以为美术者何在,其一事也。
阐明有唐以来绘画雕塑建筑之源流理法(自唐世佛教大盛而后,我国雕塑与建筑之改革,亦颇可观,惜无人研究之耳),使恒人知我国固有之美术如何,此又一事也。
阐明欧美美术之变迁,与夫现在各新派之真相,使恒人知美术界大势之所趋向,此又一事也。
即以美术真谛之学说,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得其真正之是非,而使有志美术者,各能求其归宿而发明广大之,此又一事也。吕澂所主张的美术革命路径,首先从阐明西方的美术概念入手;以此为新的认识基础,重新整理中国传统美术史,同时引介欧美美术演变历程,特别是辨别五花八门的现代美术潮流之实质;在“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之后,总结出美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即如研究者所识,这种探索不是针对具体而微的种种现实弊端,而是要“对不同系统的艺术问题作本体论的探究”,欲取镜古今中西,在开阔宏大的世界性视野下建立现代美术史学。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吕澂在信中对于《新青年》杂志领导新文艺运动方向的期许——他是以20世纪初意大利未来主义策源地《诗歌》杂志为《新青年》之前辈楷模的:窃谓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尤极宜革命。且其事亦贵杂志所当提倡者也,十载之前意大利诗人玛黎难蒂氏刊行诗歌杂志,鼓吹未来新艺术主义,亦但肇端文词,而其影响首著于绘画雕刻。今人言未来派,至有忘其文学上之运动者。
方今习俗轻薄,人事淆然;主持言论者,大率随波逐流,其能作远大计,而涉及艺术问题者,独见于贵杂志耳。贵杂志其亦用其余力,引美术革命为己责,而为第二之意大利诗歌杂志乎?其利所及实非一人一时已。吕澂极有可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1915—1916年)接触到了未来主义思潮。《东方杂志》11卷2号(1914年8月)刊出的一篇“未来主义”专题报道(章锡琛编译自日本《新日本》杂志),可说代表了当时日本学界对于未来主义的一般认识(文末还在“日本之未来主义”小标题下,简要说明了未来主义在“近来日本一部青年文士画家之间”的盛行)。文章在介绍“何谓未来主义”时称:五载以前,有意大利诗人玛利涅智,倡未来主义于弥勒那市,主张革新现代社会各方面,而未来派于是乎时始。其初为此运动者,非仅限于艺术而已。凡形成今日文明之要素,如文学经济社会学上一切之人类根本问题,皆欲加以根本之革新。探究未来主义兴起之因,“实受现代文明生活刺激之新意大利人对旧意大利人革新之声也,实厌弃过去之古董文明树立进步的新文明之声也”。对古老文明因袭重负的反抗、对全面革新国家社会的呼吁,以及从文学入手扩张到其他艺术领域、企图最终撼动政治经济思想基础的相似规划,都很容易让吕澂将眼前的《新青年》和十年前的意大利先锋杂志《诗歌》联系起来、并置起来;而革命旗手陈独秀,在“文化的鼓动者、世风的革新者、毅力的激发者”方面,也无疑大有希望成为有“欧洲的咖啡因”之称的马里内蒂在中国的接班人。
陈独秀读信后的反应,也许既在吕澂意料之中,也在他意料之外。
首先,这封标榜“革命”的来信,果然引起了陈独秀的惊喜和重视。他拈出“美术革命”四字,作为该期通信中极醒目的一个标题。回信开首即表示:本志对于医学和美术,久欲详论;只因没有专门家担任,至今还未说到。现在得了足下的来函,对于美术(特于绘画一项)议论透辟,不胜大喜欢迎之至。接下来,陈独秀发表了自己对于国内绘画“早就想说”的意见: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这是什么理由呢?譬如文学家必用写实主义,才能够采古人的技术,发挥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抄古人的文章。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传统文人出身的陈独秀,显然熟悉中国画远甚于洋画。他所深恶痛绝的,一是清初以降“四王”画派所代表的专事复古模仿、不重创造的画风: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内中有画题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临”、“摹”、“仿”、“抚”四大本领,复写古画,自家创作的,简直可以说没有,这就是王派留在画界最大的恶影响。二是社会上无独立见解、盲目吹捧、陈陈相因的观赏习气:谭叫天的京调,王石谷的山水,是北京城里人的两大迷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许人说半句不好的。……像这样的画学正宗,像这样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在陈独秀的眼里,中国画界的这些弊端,又无一不与文学界及整个思想界死气沉沉、陈旧腐败的现状相通连,而疗救的药方自然可以彼此借用。既然“文学家必用写实主义”,“才能做自己的文章”,既然文学革命“三大主义”之一便是“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既然西方先进的洋画最重写实精神,那么,写实主义便当仁不让,成为改良中国画的绝佳利器。这里凸显出陈吕二人关注点和思路的极大差异: 虽然出发点都是对现实不满、要求美术(特别是绘画)革命,但吕澂作为美术教育界人士,忧虑的是中西美学观念混淆不辨、教育研究毫无章法、欺世盗名者坐享渔利,因而急切希望从本体论入手,正本清源,建立科学的现代的学科机制;陈独秀则以国画摹古派的反对者身份,聚焦传统中国画写意不写实、仿古不创新的问题,主张引进西方油画的写实技法加以改良,至于写实是否为洋画的根本精神、如何将写实技法引入中国画、改造后的中国画又将呈现出何种面貌,陈独秀并未进一步探究。其实,从艺术史学者的角度来看,要调和东西方艺术,具体技巧的变化仅在其次,“更重要的还是审美感情和视觉观念的变化”。限于这种偏重个人印象的、略显狭隘的艺术视野,陈独秀对于吕澂提出的不够“具体”、难以实际操作的“四事”,便无法像面对胡适文学改良“八事”那般一一作兴奋的评说了;更何况文学革命方兴未艾,影响日隆,与美术相比,文学作为最鲜明的“传导思想的工具”,无疑享有更大的实用性和优先权,这是以思想和政治改革为根本目标的陈独秀再清楚不过的了。
至于吕澂以未来主义先驱马里内蒂和《诗歌》杂志为号召,对陈独秀和《新青年》寄予的“艺术先锋”期待,则似乎完全没能引起陈独秀的注意或共鸣。或许,未来主义这一在20世纪初期美术史上影响远大过文学史的新鲜思潮,尚未进入陈独秀的视界。在他《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里对“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所作的进化论式介绍中,最后仅止步于自然主义而已,连象征主义都一字未提,更遑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云变幻的各种现代派运动了。由此亦可见,在对欧洲文艺界最新动态的了解、关注及取舍这层“敏感度”上,陈吕二人也存在着一个“时间差”。
从陈独秀的回信里,吕澂一定明白无误地读懂了两人的差异与分歧。所以,尽管陈独秀客气地表示:“足下能将对于中国现在制作的美术品详加评论,寄赠本志发表,引起社会的讨论,那就越发感谢了”,但之后吕澂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新青年》上——具体评论某部作品,绝非吕澂“美术革命”蓝图中最紧要的基础工作;与此同时,他的学术兴趣正日益为佛学研究所吸引。虽然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在美学上的探索并没有停顿,但当年希冀搭乘“文学革命”的顺风车、再掀“美术革命”波澜的激进姿态和理想,就在这次通信后戛然而止——满怀热情正欲迈出全面艺术“革命”的第一步,却发现找不到落脚之地,也难觅知己同伴,茕茕孑影,孤掌难鸣,只好退回自己的书斋,埋头于学术撰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