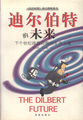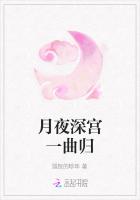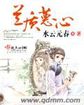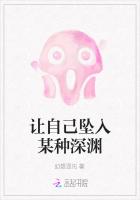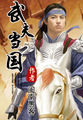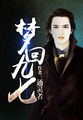我得到我爷爷过世的消息是在五月十六日。
晚间新闻的播音员说,今天是大陆“文革”三十周年纪念日。还有几个旅美的“文革”研究专家讲了话,我恍恍惚惚听着,他们好像说要把“文革”研究进行到底。等到新闻转向了一起贩毒案,我又觉得他们不可能说那样的话。
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生命中开场的三十年和我爷爷生命中落幕的三十年同时结束了。
我没能在战争的炮火中出生,这使我生当为英雄的激情不可避免地一天天消失;我也不是和共和国的红旗一起长大的,在幸免了种种磨难的同时也失掉了因饱经沧桑而增添成熟魅力的机会;但我无论如何也是在炮火一样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在一个硕大无比的红的烂漫红的执着的摇篮中呱呱坠地……
我爷爷活了八十几岁。我知道我无需太过悲痛的,有的人在花一般的年龄刹那间就零落成泥碾作尘,而他称得上寿终正寝了。但我竭力想把记忆中关于他的所有断片粘贴起来,仿佛那样我会得到一只刻着神秘花纹的瓦罐,就像藏在我爷爷家阁楼上的那只一样。
我不知道这样的粘贴算不算是一种纪念。
我翻箱倒柜找出了保存的那张我爷爷和我爸爸的黑白合影。我现在只有寥寥几张黑白照片了,因为它们大多属于遥远的过去,而我是不情愿把遥远的过去带在身边远渡重洋的,但这张合影我还是带上了,因为照片上的我爸爸那么年轻,而我爷爷似乎显得比我爸爸还年轻。
应该说我爷爷是风流倜傥的。当然我也只有到了今天这个年代,今天这个年纪,当脑子里关于我爷爷的形象消失殆尽的时候,我才会不费斟酌地这样描述的。
在我上小学的那些年里,如果说我憎恨过什么人的话,那么首当其冲是当时还没见过面的爷爷,因为他使我在接连不断的填表格行为中一次次无比羞愧无比颤抖,使我在学校组织的苦大仇深讲用会上抬不起小小的头,也使我当时虽不白皙倒也光滑的脸蛋频繁领受了唾液的冲洗和石子的锤打。
照片上的我爷爷穿了一件白色的丝绸短衫,钮扣是盘花绊儿的那种。他没系领口处的第一粒纽扣,这使他流露出了一股少爷气。我看过时下正走红的表现烟土、烟花女、绣花鞋的电影,从主人公身上我很高兴地发现了同样的少爷气。
尽管照片表面因为年深日久早已粗糙了,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抚触那丝绸光滑的质地。我想我爷爷当年在湘江岸边那个曾繁华一时的戏园子里,捧那个红极一时的小芸仙,很可能也穿这样的衣服,白色丝绸的确使他显得气质不俗。
我爸爸身上的那件学生装就不免有些粗重了,但它也恰到好处地衬托了我爸爸的书生气。据我爸爸讲这是他大学期间唯一的一件外衣,他穿着它背过《古文观止》,也背过《叶甫盖尼·奥涅金》。
这张照片是他们在五十年代中,也就是他们在分开六七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时拍的。
我爷爷在我爸爸六七岁的时候独自一人进了城,且谋得了一官半职,很快又娶了唱花鼓戏的小芸仙。我知道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故事,但为了我的瓦罐的完整我不愿放弃这个带些脂粉气的片断。
我爷爷好几年也没回家看过一眼,我奶奶和我爸爸的生活就完全陷入了困顿。那一年,当留守在祖屋里的我奶奶把家里稍微值点钱的东西典当尽了以后,就带了我爸爸去要饭。
我对我爸爸说过,谁想得到在他的剥削阶级后代的华丽外衣下,居然还藏着乞丐的褴褛衣衫。
我对我奶奶始终是抱有深深同情的,正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949年以后,政府要求一夫一妻了,我爷爷又回到了我奶奶身边。我至今不清楚是小芸仙提出离开我爷爷的,还是我爷爷幡然悔悟,执意要回到自己的糟糠之妻身边的。
但这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奶奶又接受了我爷爷,要知道我奶奶家祖宗三代劳动人民,我不明白我奶奶为什么就不能在翻身解放妇女独立的新社会争一口气,带着我爸爸改嫁一个劳动人民呢?那样我们家的历史就会完全被重写了。
当然我爸爸也许就不会千方百计地远离我爷爷跑到省会去念书;也不会在毕业分配时拿着格尺在地图上认真地丈量一番,然后诚心实意地要求到东北边疆去,揽一遍“八千里路云和月”;自然也就不会遇上我妈妈,那么我也不可能在冰城“文攻武卫”全面拉开战幕的日子不太情愿地发出第一声啼哭……
终于我不得不承认,把我爷爷从我生命的视线中抹去,这纯粹是一种徒劳。
我爸爸和我爷爷拍这张照片时正意气风发,他在读中文系,而且刚刚得了一个省级的斯大林文学奖。这时他想起了曾轻视、抛弃过他的我爷爷,我爷爷无形中施加给他的心灵压力超过了我奶奶的爱的动力,这使他对我爷爷竟然有了一些无法言喻的感激。
所以他和我爷爷在分离了六七年之后第一次握手言和,当然我也不排除其中包含的血浓于水的成分。
于是就有了这张二寸的照片,于是他们就把同一瞬间的微笑留给了我,使我能在若干年后,在听了关于我爷爷的消息和那个棕黄头发的播音员对“文革”的毫无感觉的讲述后浮想联翩。
我爷爷和我爸爸的微笑只维持了一瞬。相对于他们后来分别度过的漫长的监禁和劳改生活,他们微笑的日子只能被称为“一瞬”。
我爸爸说当他一次次站在广袤的田野上仰望天空时,他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他那么希望忘记的我爷爷,使他顿然产生挫败感的事实就是他一刻也不曾远离过我爷爷。
北出山海关,跨跃八千里,也只是抽刀断水。
一年多以前,我在北京机场的海关入口处看到了一张蔚蓝色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国际航线图,我发现从北京到纽约几乎是最长的一条了。这个发现给我当时被离愁的浓雾笼罩的心打开了一道缝隙,一缕云霞般的窃喜照射进来。
我窃喜于我比我爸爸当年走出得更远。
如今浓雾消散了,云霞也流失了,我的心是冬日里平淡的天空。我开始问自己,究竟该用哪一种尺度来衡量大西洋两岸的距离。
我毕业时曾和我爸爸一起回湖南看望过我爷爷和我奶奶。他们仍住在那座青灰色的祖屋里,祖屋坐落在一个封闭的小山村里。我们从县城坐长途汽车,下了长途汽车又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二十多里,才望见了小村的斑斑竹林和赤裸红土。我跌坐在村口的池塘边。
我的先人们就是喝这个池塘的水过了一辈子的,但这是一汪死水,天旱的时候太阳吸走一部分,下雨的日子老天爷再还回一些,这是它年复一年所经历的轮回。
远远地我看见一个三十左右年纪的农夫走过来,用池塘里的水冲洗了几下沾满了黄泥的锄头,顺便又涮了涮自己的脚。随后又有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女孩挑着一对水桶走过来,她很快把水桶装满了水。我爸爸和他们打招呼,高声地聊几句家常。后来那男的说地里的活儿还没有做完,女孩说要回家烧饭,他们就急急地离开了。
我爸爸告诉我那男的应该算是我的远房堂叔,而按辈分论,那女孩必须叫我表姑。那一瞬我发现我和这个小山村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茫茫然不知是喜是忧了。
我爸爸又指指我们刚刚走过来的那条土路,说当年他就是在那儿攀上一辆卡车进城的。第一次他没有抓紧卡车车尾的拦板,结果摔到了地上,摔掉了一颗门牙。他爬起来不顾一切地又去追赶那辆奔驰的卡车,他张大血肉模糊的嘴艰难地呼吸着,终于又一次抓住拦板,而且跳进了车厢。
逃离总是有代价的。
我爸爸的逃离,且不再回头,使我避免了和我堂叔以及表侄女同样的生活,所以我当时暗暗感谢他的那颗早已沦入泥土的门牙。
我爷爷我奶奶对我们进行了隆重的招待,他们把那块在屋檐下风干了一年的咸肉摘下来蒸了。饭后我爷爷踩着一个颤微微的梯子登上了挂满蛛网的阁楼,从里面捧出了一个青灰色的瓦罐。
那一夜我爷爷的兴致很好,也许是多喝了几杯水酒的缘故;也许因为我对他过去的一切表现出的平和甚至带一点好奇的态度鼓励了他。
我爷爷从瓦罐里先抓出了一捧干草,它们曾拥有过碧翠的生命,就像它们所遮盖的往事。随后他拿出了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又从信封里掏出了一叠泛黄的白纸、几张照片和一札信。
白纸上是他在许多年里填写的古体诗词,那些诗词显露出了他非同一般的文学功底和对生活颇有深度的理解。他的字龙飞凤舞,力透纸背。我从没练过书法,我的字基本上可被归入令人不忍目睹的那一类。
所以我在对我爷爷的感觉中破天荒地添了一些敬佩成分。
我就是在那天第一次见到了我爷爷和我爸爸的合影,而且征得我爷爷的同意把这张照片带走。
我还见到了小芸仙的照片。这个多年来我奶奶的乃至我们整个家族的“敌人”,我无论用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眼光,无论以局外人还是局内人的角度来审视她,都不得不承认她拥有打不倒的美丽。
我爷爷说小芸仙读过一些书的,当然在唱戏过程中又多学了许多字,我爷爷的话没有说完,我猜得出下文,自然也多了许多情。
那天晚上我费了许多想象的周折,才把眼前的头发花白,面容衰老,穿着厚重宽档裤的我爷爷和拥有过小芸仙的那个潇洒的少爷结合起来。我平生第一次对他抛弃我奶奶和我爸爸的行为给予了一些理解。
我爷爷保留的信大多数都是我爸爸零零散散写给他和我奶奶的,另外还有一封五十年代初政府通知我爷爷到城里工作的信。那时我才知道我爷爷曾是南方一个交通重镇的火车站的站长,当他的上级准备带他一道去那个“高山青,溪水长”的海岛时,他却选择了留下。
此刻当我坐在远离我的出生地,也同样远离我的祖屋的公寓里,我仍旧和当年一样惶惑:人到底要面临多少次“去”与“留”的选择?
1949年后我爷爷在老家赋闲了一阵,每天吼骂我奶奶和我爸爸,我想这是导致我爸爸离家出走的直接原因。后来政府鉴于我爷爷完整地保存了火车站的军用物资,也算戴罪立了功,就给他重新安排了工作。不过从1957年开始我爷爷就失掉了这份工作,当然同时还失掉更多,这是他在二十几年后接到的一封平反书所不能补偿的。
最后的一叠白纸是我爷爷整理的家谱。他对我列数了家族中出现过的状员进士,文人墨客,原来我的家族还颇有出彩的几笔,这使我饥渴了许久的虚荣心得到了小小的满足。而且我还极荣幸地因为得到了文学硕士学位而成为长长家谱中寥寥无几的被记录名字的女性之一。
高校恢复招收研究生时我爸爸已超龄,所以自然由尚有青春资本可向文学象牙塔不断投资的我来拿下这个学位,他要我一生一世做文学中人。
我曾经在一封家书中说过,我爸爸的“殷殷期望交织成网,我是多么快乐地束手就擒呵”,但我在“快乐”了一段时间后就执意要挣脱这张期望的网。
“且叠沧海一袖间,聊把樊篱当家园。”这两句诗是我爷爷写的吗?还是我在祖屋那张摇摇晃晃的大木床上,因为蚊虫的叮咬,或者因为月光的恼人而无法入睡时随口念出来的,不得而知了。
几年前我爸爸在我奶奶去世后把我爷爷接到了东北,我爷爷住了不到三个月就又回到了祖屋。他说两代人因为多年远离已无法兼容。
不能兼容了就离开,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一种胆怯还是一种勇气。
当我浮冰一样漂上这片新大陆,在一番骨肉震痛的消融和重塑之后,我又回到文学的怀抱寻求归依,续做我爸爸的梦。
也许该拥有的,就不能割舍;该背负的,就无法放弃。
我知道我回不到旧日家园了。我只能在异国划一方小小的清潭为樊篱,让心中的音乐幻为清潭中的波纹,不时等待熟悉的惊鸿来作意味深长的一瞥。
我爷爷被十六个红脸膛的健壮杠夫,披麻戴孝的我爸爸,以及全村百十号老老少少送入了他生前相中的那块墓地,据说那块墓地背后有一片新生的竹林。
从此他安定下来了。
但我们的家族,仍然继续着“永远都在逃避,从来也不曾远离”的故事。那座祖屋被留了下来。即便它在某一天坍塌了,还有这个被我用记忆的断片粘贴起来的文字瓦罐留下来,还有印在这张我爷爷和我爸爸的黑白小照上的泪痕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