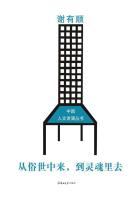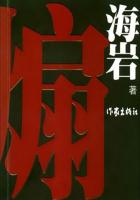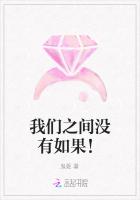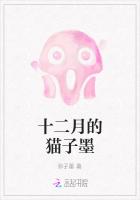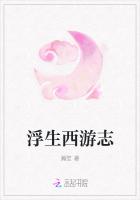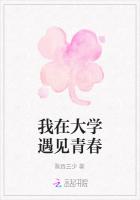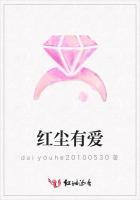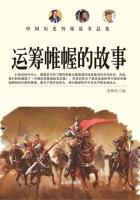重庆旧书铺
茅盾
从重庆这些街道的旧名称看来,可知旧时重庆各街也颇“专业化”。例如“鸡街”、“骡马市”、“打铁街”之类,单看名目便可想象从前这些街的特殊个性了。我不知道旧时重庆有没有一条旧书铺集中的街道,但照今日重庆还保存着旧日面目-那一小段连街对宇的旧书铺集团看来,这或者也就是从前的书街了。不过这段街的旧名称却叫做“米亭子”。
这里的旧书铺集团,共计不过六七单位(连摊子也在内),说多呢实在不多,可是说它少么,似乎今日重庆市内也还找不出第二处有这样多的单位集中起来的旧书市场。当然不是说这里的旧书最多,比这里各单位所有旧书的总数还要多些的大旧书铺,我想重庆市内也不是绝对没有,可是单位之多而又集中,俨然成为小小一段的“旧书街”,则恐怕除此以外是没有的。
至于决然独处的大大小小的旧书铺,-或文具而兼旧书之铺,则在今日重庆市内外,几乎是到处可见的了,可是也得说明:无论是“米亭子”或其他单独的旧书铺,旧书诚然是旧书,可能用抗战前我们心目中的所谓“旧书”来比拟,今天的旧书,只是“旧”书而已。战前一折八扣的翻版书,今天也在那些旧书铺内,俨然珍如宋椠元刊;1930年香港或上海印的报纸本小说(其实也有土纸本在发售),也成为罕见之珍品。合于往日所谓“旧书”的标准的旧书,自然也不是没有;只是太少了,说不上比例。差可说是琉璃厂一角渊蒋建国作冤约占百分之一二的,是木板的线装书(这比一折八扣的版本自然可以说是“旧”些了罢),然而这又是医卜星相之类占多数,我曾在两处看见两部木板线装的,-一是《曾文正日记》,一是《诗韵今璧》,---那书铺老板视为奇货可居,因为这两种是在医卜星相之外的。
但是千万请莫误会,今日重庆的这些旧书铺对于读书人是没有贡献的,比方说,从沦陷区来的一位青年,进了这里的某大学,他来时身无长物,现在至少几本工具书非买不可了,那他就可以到那些旧书铺去看看,只要不怕贵,他买得到一部十年前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这是现在此地可能买到的最好的英文字典。又比方说,一位写作者如打算随便“搜罗”一点旧材料,破费这么几天工夫,上城下城,上坡下坡,出一身臭汗,总也可以略有所获,十年前的旧杂志有时竟能淘到若干,但自然,怕贵是不行的。
当真不是夸大其词,这些旧书铺有时真有些“珍贵”的书本。原版的外国文书籍,极专门而高深的,也会丢在报纸本的一折八扣书之间,有一位朋友甚至还找到了一册有英文注释的希腊古典名著,因此竟引起他学习希腊文的兴趣。不过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罢了。有些英文或法文的原版丛书,虽只零落数册,而亦非难得之书,可是扉页上图记宛在,说明这是战前某某大学或某某学术机关的故物。这样的书,如何颠沛流徙了数千里,又如何落在旧书铺中,想象起来真不能叫人不生感慨;这样的书,放在家里虽不重视,但在别一意义上,可实在算得是具有“藏珍”资格的“旧书”了罢?可喜而又可怪者,是这样的书,近来愈见其多,常常可以遇到了。这一件小事,如果推想开去,却又叫人觉得可忧而又可悲。
旧书价是跟着粮价走的,有人在“米亭子”某铺看到了一部《综合英汉大辞典》(袖珍本),索价二千六百元,买不起,隔了两天再去看,却已涨为三千元了。问何以多涨四百,则答曰:“这几天粮价涨了呀!”书是精神食粮,书价跟着粮价走,似亦理所当然。但是今日重庆的旧书铺老板计算他的货价尚有另一原则,此即依纸张(白报纸或道林纸)及书之页数为伸缩,即使是极不相干的书,只要纸好,页数多,则价必可观,这简直是在卖纸了!自有旧书铺以来,这真是历史的新的一页。对于这样的“现实主义”,版本权威只能摇头叹息。所以今日重庆跑旧书铺的人,决不是当时在北平跑琉璃厂,在上海跑来青阁的人们了。
不过,旧书铺的内容虽然变了,但从“市上若无,则姑求之于旧书铺”这一点看来,今天重庆的旧书铺还是“旧书铺”,只是所有者是现实意义的“旧”书罢了。可以说旧书铺也染上了战时的色调了,这也是“今日重庆”之一面。
记马德里书市
戴望舒
无匹的散文家阿索林,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将法国的书店和西班牙的书店,作了一个比较。他说:在法兰西,差不多一切书店都可以自由地进去,行人可以披览书籍而并不引起书贾的不安;书贾很明白,书籍的爱好者不必常常要购买,而他之走进书店去,目的也并不是为了买书;可是,在翻阅之下,偶然有一部书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买了它去。在西班牙呢,那些书店都是像神圣的圣体龛子那样严封密闭的,而一个陌生人走进书店里去,摩娑书籍,翻阅一会儿,然后又从来路而去这等的事,那简直是荒诞不经,闻所未闻的。
阿索林对他本国书店的批评,未免过分严格一点。法国的书店也尽有严封密闭的,而西班牙的书店,可以进出无人问,翻看随你的,却也不在少数。如果阿索林先生愿意,我是很可以列举出巴黎和马德里的书店的字号来作证的。
公正地说,法国的书贾对于顾客的心理研究得更深切一点。他们知道,常常来翻翻看看的人,临了总会买一两本回去的;如果这次不买,那么也许是因为他对于那本书的作者还陌生,也许他觉得版本不够好,也许他身边没有带够钱,也许是他根本只是到书店消磨一刻空闲的时间,而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不理不睬,由他翻看一个饱。如果殷勤招待,问长问短,那就反而招致他们的麻烦,因而以后就不敢常常来了。
的确,我们走进一家书店去,并不像那些学期开始时抄好书单的学生一样,先有了成见要买什么书的。我们看看某个作家是不是有新书出版;我们看看那已在报上刊出广告来的某一本书,内容是否和书评符合;我们把某一部书的版本,和我们已有的同一部书的版本作一比较;或仅仅是我们约了一位朋友在三点钟会面,而现在只是两点半。走进一家书店去,在我们就像别的人们踏进一家咖啡店一样,其目的并不在喝一杯苦水也。因此我们最怕主人殷勤。第一,他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使你不得不想出话去应付他;其次,他会使你警悟到一种欠意,觉得这样非买一部书不可。这样,你全部的闲情逸致就给他们一扫而尽了。你感到受人注意着,监视着,感到担着一重义务,负着一笔必须偿付的债了。
西班牙的书店之所以受阿索林的责备,其原因是不明顾客的心理。他们大都是过分殷勤讨好。他们的态度是绝没有恶意的,然而对于顾客所发生的效果,却适得其反。记得1934年在马德里的时候,一天闲着没事,到最大的爱斯巴沙加尔贝书店去浏览,一进门就受到殷勤的店员招待,陪着走来走去,问长问短,介绍这部,推荐那部,不但不给一点空闲,连自由也没有了。自然不好意思不买,结果选购了一本廉价的奥尔德加伊加赛德的小书,满身不舒服地辞了出来。自此以后,就不敢再踏进门槛去了。
在文艺复兴书店也遇到类似的情形,可是那次却是硬着头皮一本也不买走出来的。而在马德里我买书最多的地方,却反而是对于主顾并不殷勤招待的圣倍拿陀大街的迦尔西亚书店,王子街的倍尔特朗书店,特别是书市。
书市是在农工商部对面的小路沿墙一带。从太阳门出发,经过加雷达思街,沿着阿多恰街走过去,走到南火车站附近,在左面,我们碰到了那农工商部,而在这黑黝黝的建筑的对面小路口,我们就看到了几个黑墨写着的字:LAFERIADELOSLIBROS,那意思就是书市。在往时,据说这传统书市是在农工商部对面的那一条宽阔的林阴道上的,而我在马德里的时候,它却移到小路上去了。
这传统的书市是在每年的九月下旬开始,十月底结束的。在这些秋高气爽的日子,到书市中去漫走一下,寻寻,翻翻,看看那古旧的书,褪了色的版画,各色各样的印刷品,大概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乐吧。书市的规模并不大,一列木板盖搭的、肮脏、杂乱的小屋,一共有十来间。其中也有一两家兼卖古董的,但到底卖书的还是占着极大的多数。而使人更感到可爱的,便是我们可以随便翻看那些书籍而不必负起任何购买的义务。
新出版的诗文集和小说是和羊皮或小牛皮封面的古本杂放在一起。当你看见圣女戴蕾沙的《居室》和共产主义诗人阿尔倍谛的诗集对立着,古代法典《七部》和《马德里卖淫业调查》并排着的时候,你一定会失笑吧。然而那迷人之处,却正存在于这种杂乱和不伦不类之处。把书籍分门别类,排列得整整齐齐,是会使人不敢随便抽看的,为的是怕捣乱了人家固有的秩序;如果本来就这样乱七八糟,我们就毫无顾忌了。再说,如果你能够从这一大堆的混乱之中发现出一部正是你所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书来,那是怎样大的喜悦啊!这里,我们就仿佛置身于巴黎赛纳河岸了。
书价便宜是那里最大的长处。我的阿耶拉全集、阿索林、米罗等现代作家的小说和散文集,洛尔迦、阿尔倍谛等当代诗人的诗集,都是从那里陆续买得的。我现在也还记得那第三间木舍的被人叫作华尼多大叔的须眉皆白的店主。我记得他,因为他的书籍的丰富,他的态度的和易,特别是因为那个在书城中,张大了青色忧悒的眼睛望着远方的云树的,他的美丽的孙女儿。
我在马德里的大部分闲暇的时间,甚至在发生革命,街头枪声四起的时间,都是在书市的故纸堆里消磨了的。在傍晚,听着南火车站的汽笛声,踏着疲倦的步子,臂间挟着厚厚的已绝版的赛哈道的《赛房德思辞典》或是薄薄的阿尔多拉季雷的签字本诗集,慢慢地踱回寓所去,这种乐趣恐怕是很少有人能够领略的吧。
然而十月在不知不觉之中快流尽了。树叶子开始凋零,夹衣在风中也感到微寒了。马德里的残秋是忧郁的,有几天简直不想闲逛了。接着,有一天你打叠起精神,再踱到书市去,想看看有什么合意的书,或仅仅看看青色的忧悒的眼睛。可是,出乎意外地,那些木屋都已紧闭着了。小路显得更宽敞,更清冷,而在路上,凋零的残叶夹杂着纸片书页,给冷冷的风吹了过来,又吹了过去。
伦敦有家野诗籍铺冶
朱自清
伦敦有家“诗籍铺”真是米米小,在一个大地方的一道小街上。“叫名”街,实是一条小胡同吧。门前不大见车马不说,就是行人,一天也只寥寥几个。那道街斜对着无人不知的大英博物院;街口钉着小小的一块字号木牌。初次去时,人家教在博物院附近找。问院门口守卫,他不知道有这个铺子,问路上戴着高礼帽的老者,他想没有这么一个铺子;好容易才找着那块小木牌,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铺子从前在另一处,那才冷僻,连斐歹克的地图上都没名字,据说那儿是一所老宅子,才真够诗味,挪到现在这样平常的地带,未免太可惜。那时候美国游客常去,一个原因许是美国看不见那样的老宅子。
诗人赫洛德·孟罗在1912年创办了这爿诗籍铺。用意在让诗与社会发生点切实的关系。孟罗是二十多年来伦敦文学生涯里一个要紧角色。从1911年给诗社办《诗刊》起知名。在第一期里,他说,“诗与人生的关系得再认真讨论,用于别种艺术的标准也该用于诗。”他觉得能做诗的该做诗,有困难时该帮助他,让他能做下去;一般人也该念诗,受用诗。为了前一件,他要自办杂志,为了后一件,他要办读诗会;为了这两件,他办了诗籍铺。这铺子印行过《乔治诗选》,乔治是现在英王的名字,意思就是当代诗选,所收的都是代表作家。第一册出版,一时风靡,买诗念诗的都多了起来,社会确乎大受影响。诗选共五册,出第五册时在1922年,那时乔治诗人的诗兴却渐渐衰了。1919到1925年铺子里又印行“市本”月刊登载诗歌、评论、木刻等,颇多新进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