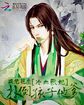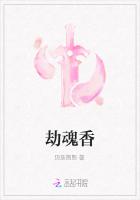读诗会也在铺子里,星期四晚上准六点钟起,在一间小楼上。一年中也有些时候定好了没有。从创始以来,差不多没有间断过。前前后后著名的诗人几乎都在这儿读过诗:他们自己的诗,或他们喜欢的诗。入场券六便士,在英国算贱,合四五毛钱。在伦敦的时候,也去过两回。那时孟罗病了,不大能问事,铺子里颇为黯淡。两回都是他夫人爱立达·克莱曼答斯基读,说是找不着别人。那间小楼也容得下四五十位子,两回去,人都不少;第二回满了座,而且几乎都是女人-还有挨着墙站着听的。屋内只读诗的人小桌上一盏蓝罩子的桌灯亮着,幽幽的。她读济兹和别人的诗,读得很好,口齿既清楚,又有顿挫,内行说,能表出原诗的情味。英国诗有两种读法,将每个重音咬得清清楚楚,顿挫的地方用力,和说话的调子不相像,约翰·德林瓦特便主张这一种。他说,读诗若用说话的调子,太随便,诗会跑了。但是参用一点儿,像克莱曼答斯基女士那样,也似乎自然流利,别有味道。这怕要看什么样的诗,什么样的读诗人,不可一概而论。但英国读诗,除不吟而诵,与中国根本不同之外,还有一件:他们按着文气停顿,不按着行,也不一定按着韵脚。这因为他们的诗以轻重为节奏,文句组织又不同,往往一句跨两行三行,却非作一句读不可,韵脚便只得轻轻地滑过去。读诗是一种才能,但也需要训练;他们注重这个,训练的机会多,所以是诗人都能来一手。
铺子在楼下,只一间,可是和读诗那座楼远隔着一条甬道。屋子有点黑,四壁是书架,中间桌上放着些诗歌篇子,木刻画。篇子有宽长两种,印着诗歌,加上些零星的彩画,是给大人和孩子玩儿的。跨角儿上一张小账桌,坐着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和蔼可亲的,圆脸的中年妇人。桌前装着火炉,炉旁蹲着一只大白狮子猫,和女人一样胖。有时也遇见克莱曼答斯基女士,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孟罗死在1932年3月15日。第二天晚上到铺子里去,看见两个年轻人在和那女司账说话;说到诗,说到人生,都是哀悼孟罗的。话音很悲伤,却如清泉流泻,差不多句句像诗;女司账说不出什么,唯唯而已。孟罗在日最尽力于诗人文人的结合,他老让各色的才人聚在一块儿。又好客,家里炉旁(英国终年有用火炉的时候)常有许多人聚谈到深夜才去。这两位青年伤感不是偶然的。他的铺子可是赚不了钱,死后由他夫人接手,勉强张罗,现在许还开着。
城隍庙的书市
阿英
我说到上海城隍庙里去“访书”,这多少会引起一部分人奇怪的,城隍庙那里有什么书可访呢?这疑问,是极其有理。你从“小世界”间壁街道上走将进去,就是打九曲桥兜个圈子再进庙,然后从庙的正殿一直走出大门,除开一爿卖善书的翼化善书局,你实在一个书角也寻不到。可是,事实没有这样简单,要是你把城隍庙的拐拐角角都找到,玩得幽深一点,你就会相信城隍庙不仅是百货杂陈的商场,也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区域。有很大的古董铺、书画碑帖店、书局、书摊、说书场、画像店、书画展览会,以至于图书馆,不仅有,而且很多。对于这一方面,我是相当熟习的,就让我来引你们畅游一番吧。
我们从小世界说起,当你走进间壁的街道,你就得留意,那儿是第一个“横路”,第一个“弯”。遇到“弯”了,不要向前,你首先向左边转去,这就到了一条“鸟市”;“鸟市”,是以卖鸟为主,卖金鱼、卖狗,以至于卖乌龟为副业的街。你闲闲地走去,听听美丽的鸟的歌声,鹦哥的学舌,北方口音和上海口音的论价还钱,同时留意两旁,那么,你稳会发现一家东倒西歪的,叫做饱墨斋的旧书铺。走进店,左壁堆的是一直抵到楼板的经史子集;右壁是东西洋的典籍,以至于广告簿;靠后面,是些中国旧杂书;二十年来的杂志书报,和许多重要又不重要的文献,是全放在店堂中的长台子上,这台子一直伸到门口;在门口,有一个大木箱,也放了不少的书,上面插着纸签-“每册五分”。你要搜集一点材料吗?那么,你可以耐下性子,先在这里面翻;经过相当的时间,也许可以翻到你中意的,定价很高的,甚至访求了许多年而得不着的,自然,有时你也会化了若干时间,弄得一手脏,而毫无结果。可是,你不会吃亏。在这“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不曾见到、听到过的许多图书杂志,会像过眼云烟似地温习现代史的许多断片。翻书本已是一种乐趣,而况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中意的书已经拿起了,你别忙付钱,再去找台子上的。那里多的是整套头的书,《创造月刊》合订本啦,第一卷的《东方杂志》全年啦,《俄国戏曲集》啦,只要你机会好,有价值的总可以碰到,或者把你残缺的杂志配全。以后你再向各地方,书架上,角落里,桌肚里,一切你认为有注意必要的所在,去翻检一回,掌柜的决不会有什么误会和不高兴。最后耗费在这里的时间,就是讲价钱了,城隍庙的定价是靠不住的,他“漫天开价”,你一定要“就地还钱”,慢慢地和他们“推敲”。要是你没有中意的,虽然在这里翻了很久,一点不碍的,你尽可扑扑身上的灰,很自然地走开,掌柜有时还会笑嘻嘻地送你到大门口。
在旧书店里,徒徒的在翻书上用工夫,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书不一定放在外面,你要问:“老板,你们某一种书有吗?”掌柜的是记得清自己的书的,如果有,他会去寻出来给你看。要是没有,你也可以委托他寻访,留个通信处给他。不过,我说的是新书,要是好的版本,甚至于少见的旧木板书,那就要劝你大可不必。因为藏在他们架上的木板书虽也不少,好的却百不得一。收进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好书,这些好书,一进门就会被三四马路和他们有关系的旧书店老板挑选了去,标上极大的价钱卖出,很少有你的份;但偶尔也有例外。说一件往事吧。有一回,我在四马路受古书店看到了六册残本的《古学汇刊》,里面有一部分我很想看看,开价竟是实价十四元,而原定价只有三元,当然我不买。到了饱墨斋,我问店伙,“《古学汇刊》有吗?”他想了半天,跑进去找,竟从灶角落里找了二十多册来,差不多是全部了。他笑嘻嘻地说:“本来是全的,我们以为没有用,扔在地下,烂掉几本,给丢了。”
最后讲价,是两毛钱一本,这两毛一本的书,到了三四马路,马上就会变成两块半以上,真是有些恶气。不过这种机会,是毕竟不多的。
从饱墨斋出来,你可以回到那个“弯”的所在,向右边转。这似乎是条“死路”,一面是墙,只有一面有几家小店,巷子也不过两尺来宽。你别看不起,这其间竟有两家是书铺,叫做葆光的一家,还是城隍庙书店的老祖宗,有十几年悠长的历史呢。第一家是菊店,主要的是卖旧西书,和旧的新文化书。木板书偶尔也有几部。这书店很小,只有一个兼充店伙的掌柜,书是散乱不整。但是,你得尊重这个掌柜的,在我的经历中,在城隍庙书市内,只有他是最典型,最有学术修养的。这也是说,你在他手里,不容易买到贱价书,他识货。这个人很欢喜发议论,只要引起他的话头,他会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意见。譬如有一回,我拿起一部合订本的《新潮》一卷:“老板,卖几多钱?”他翻翻书:“一只洋。”我说:“旧杂志也要卖这大价钱吗?”于是他发议论了:“旧杂志,都是绝版的了,应该比新书的价钱卖得更高呢。这些书,老实说,要买的人,我就要三块钱,他也得挺着胸脯来买;不要的,我就要两只角子,他也不会要,一块钱,还能说贵么?你别当我不懂,只有那些墨者黑也的人,才会把有价值的书当报纸卖。”争执了很久,还是一块钱买了。在包书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地开起口来:“肯跑旧书店的人,总是有希望的,那些没有希望的,只会跑大光明,哪里想到什么旧书铺。”近来他的论调却转换了,他似乎有些伤感。这个中年人,你去买一回书,他至少会重复向你说两回:“唉!隔壁的葆光关了,这真是可惜!有这样长历史的书店,掌柜的又勤勤恳恳,还是支持不下去。这个年头,真是百业凋零,什么生意都不能做!不景气,可惜,可惜!”言下总是不胜感伤之至,一脸的忧郁,声调也很凄楚。当我听到“不景气”的时候,我真有点吃惊,但马上就明白了,因为在他的账桌上,翻开了的,是一本社会科学书,他不仅是一个会做生意的掌柜,而且还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呢!
于是,我感到这位掌柜,真仿佛是现代《儒林外史》里的异人了。
跑到护龙桥再停下来。护龙桥,提起这个名字,会使你想到苏州的护龙街。在护龙街,我们可以看到一街的旧书店,存古斋啦,艺芸阁啦,欣赏斋啦,来青阁啦,适存斋啦,文学山房啦,以及其他的书店,刻字店。护龙桥,也是一样。无论是桥上桥下,桥左桥右,桥前桥后,也都是些书店、古玩店、刻字店。所不同于护龙桥者,就是在护龙街,多的是“店”,而护龙桥多的是“摊”;护龙街多是“古籍”,护龙桥多的是“新书”;护龙街来往的,大都是些“达官贵人”,在护龙桥搜书的,不免是“平民小子”;护龙街是贵族的,护龙桥却是平民的。
城隍庙的书市并不这样就完。再通过迎着正殿戏台上的图书馆的下面,从右手的门走出去,你还会看到两个“门板书摊”。这类书摊上所卖的书,和普通门板摊上的一样,石印的小说,《无锡景》、《时新小调》、《十二月花名》之类。如果你也注意到这一方面的出版物,你很可以在这里买几本新出的小书,看看这一类大众读物的新的倾向,从这些读物内去学习创作大众读物的经验,去决定怎样开拓这一方面的文艺新路。
经过二十几处的翻检,你的精神一定是很倦乏了。
琉璃厂寻梦记
姜德明
现在,北京东西琉璃厂的一些老店铺是正在拆除了。我并不感伤,我期待着新的琉璃厂快快建成。旧的总要被新的代替,琉璃厂的确古旧破败得可以了,人们要寻觅它新的梦。
一
琉璃厂旧书肆形成于清乾隆年间,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古往今来,记载琉璃厂书肆盛况的有多少著作啊,而我记得最真切的还是当年鲁迅先生在这里留下的脚步。翻开《鲁迅日记》,你可以看到当他1912年到北京的一周以后,便去逛琉璃厂了。从此时有所至,往往隔几天便去一趟,说起来总有几百次之多吧。
1932年鲁迅最后一次北返探亲,他还留连于琉璃厂书肆,并发现那儿的笺纸的可贵,鼓动郑振铎同他合编了一部《北平笺谱》。我常想:鲁迅先生写《中国小说史略》,整理《嵇康集》,拟编汉唐石刻,很多零散的原始材料都是琉璃厂供给的,而鲁迅先生回赠于琉璃厂的却是千古不朽的研究成果,包括目前世界各大图书馆珍藏的《北平笺谱》在内。只有鲁迅先生的眼光才能发现这些行将湮没的民族文化精华。他还预言这部出自琉璃厂书肆的笺纸,可以走向世界而无愧,到三十世纪“必与唐版比美矣”。琉璃厂应该以接待过鲁迅这样的知音而感到荣耀。
当时身在北京的郑振铎也承认,他的目光的确不如鲁迅先生:“至于流行的笺纸,则初未加以注意……引起我对于诗笺发生更大的兴趣的是鲁迅先生。”又说《北平笺谱》的印成:“全都是鲁迅先生的力量---由他倡始,也由他结束了这事。”这些话都见于郑振铎写的《访笺杂记》。
当我还没有到过北京而先读到《访笺杂记》这篇散文时,我便向往琉璃厂,作着畅游厂甸的美梦了。“留连到三小时以上。天色渐渐地黑暗下来,朦朦胧胧的有些辨色不清。黄豆似的灯火,远远近近的次第放射出光芒来。我不能不走。那么一大包笺纸,狼狈不堪地从琉璃厂抱到南池子,又抱到了家。心里是装载着过分的喜悦与满意……“那一天狂飙怒吼,飞沙蔽天;天色是那样惨淡可怜;顶头的风和尘吹得人连呼吸都透不过来。一阵的飞沙,扑面而来,赶紧闭了眼,已被细尘潜入,眯着眼,急速地睁不开来看见什么……”
鲁迅先生以为郑振铎的这些描写“是极有趣的故事”,也许引起了他当年漫步于琉璃厂的回忆吧。
鲁迅先生是忘怀不了琉璃厂的。不知今天琉璃厂的人们,当你们骄傲地向外国顾客展示《北平笺谱》的时候,可曾想到正是鲁迅先生,以及郑振铎先生完全依靠了个人的微薄力量来发掘和抢救这些国宝吗?
二
三十多年前,当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琉璃厂。我要沿着鲁迅先生的脚步,去重温那些迷人的旧梦。有一天,我终于来到琉璃厂,推开了一家家店铺的门。
这条名街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陋巷,一片荒败破落的景象。顾客不多,房屋低矮而阴暗,线装书散发出一股霉气,连荣宝斋也空荡荡的,店员闲得正在下象棋……我的梦幻破灭了,琉璃厂的盛况何在?多彩的文化宝藏何在?
这破败的景象是日伪和国民党摧残的结果,而我们刚刚进城,百废待兴,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正在进行着,一时还顾不上琉璃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