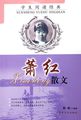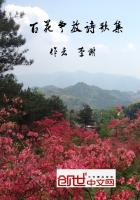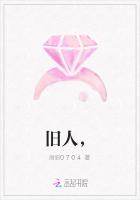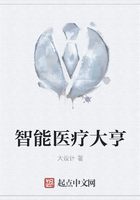朋友赠书,我照例投桃报李,回敬自己的作品。有时也会主动伸出友谊之手,先赠己作。但愿我送出去的书,不必再三致意便好了!
租书
徐少康
我被小城的人们推崇为“藏书家”,人们看到我那三大架上千册的书,无不露出惊讶和赞许的目光,而我自己有时却袭上一缕遥远的内疚和感伤。
我小时住在小城的一条巷子里,巷子口不远处,有一爿租书店,用一分钱便可以租到一本小人书。从小学到初中,我在这里读完了全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书里那些故事给了我无数美丽的幻想。租书的老人姓陈,戴着一副老花镜,天天总是坐在书架里看书,每次都要喊他好几声,他才如梦醒般抬起迷茫的眼睛,将你要的书递给你。后来,老人的租书店不开了,我便到他家里去租书。老人住在一个昏暗的小阁楼上,他的四周,是一堆堆一架架的书,就像一张密密的蛛网,他就是蹲在网中的老蜘蛛。渐渐熟了,他任我随意挑选。我对他的书很熟悉,知道他有哪些书放在什么地方。
我初中毕业那年,开始了“文革”,在一次红卫兵的战斗队会上,我一时冲动说了一句“我知道有个地方有很多书”。当我吃惊地发觉自己说溜了嘴,已经来不及了,正被狂热的邪火燃着的少年们,已一阵风地冲到了老人的小阁楼上,老人双手颤抖,僵立在书堆中,被这突来的灾难吓坏了。藏书一堆堆地抛到了街道上,火舌疯狂地吞噬着这些书,一片片纸灰飘满天空。突然,身后的小阁楼上传来“嘭”地一声,像是什么重物砰然倒地,接着就听有人说老人摔倒在地上了。从那以后,我从老人门前走过,再不敢看一眼他的家,但担心的事终于传来:老人死了。
一年后,我上山下乡到一个偏远地区插队,心里稍微透了一口气,正好借此摆脱心头的一块沉重阴影。但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因没有书读而日益生长的空虚和慌惶心情,使我常常怀念起老人和他的那些书,怀念那租书读的好时光,一种内疚和愧恨的感觉更浓更重。我在一瞬的冲动里毁掉了一个人一生勤勉的收藏,毁掉了这个人生存的依托,使他结束了生命。我难道能够因为自己年轻而推卸自己的罪责吗……我回到小城已是春深似海的年代,书籍就像春花般烂漫,于是我便开始拼命地买书,每买一本书,就仿佛减轻了一点点心中的承负,时间一长,形成了一种爱书买书读书的习惯,书架上也就日益充盈起来。每当我坐在书房中摆弄抚摸这些书时,便会感到人生真是难以逆料:人生中有些微小的偶然事件,往往会毁掉一个人,也会造就一个人。我毁掉了一位老人和他的所有的藏书,现在我已是一个老人,倒却成了一个“藏书家”。
换书
谢兴尧
跑书店成了习惯,选书买书成为嗜好,买书需要钱,书价贵了,需要更多的钱。钱是维持生活的,买书多了,势必影响生活,不能两全。褚人获《坚瓠补集》二,有《贫士买书为室人所谪》云:“张无择(抡)贫士也,所得馆谷,悉以买书,每为室人之谪。”刘武城戏成《如梦令》云:“万卷百城相亚,滋味浑如食蔗,急切不逢时,时至黄金无价,休骂、休骂,浊酒没他难下。”将仅有一点薪水买书,当然会遭到妻室的反对。又清人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二:昆山徐懒云茂才买书无钱,自嘲云:“尘成书癖更成贫,贾客徒劳过我频,始叹百城难坐拥,从今先要拜钱神”。读书人无钱买书是古今寒士不能解决的憾事。
近十年来,书价急剧飞涨,许多钱买不了几本书,于无法中想办法,以书易书,以古物换书,即是以木刻古书换新排字的平装本,我常用的《九朝东华录》及《清史稿》,看后没有归架,几次搬迁,缺失很多,又因待用,由中国书店雷梦水先生选购一部《东华录》价数百元,以旧书易之。又中国书店老友郭纪森先生亦帮忙换得一些用书,文化中人互相关怀协助,其热忱可感也。
文物、图书、字画,本来同源,以文物换书,自古已然。宋人《道山清话》云:“张文潜常言,近时印书盛行,而鬻书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负担。有一士人,尽掊其家所有,约百余千,将以入京鬻书。至中途遇一士人,取书阅之,爱其书而贫不能得,家有数古铜器,将以货之。而鬻书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见喜甚,乃曰毋庸货也,我将与汝估其值而两易之。于是尽以随行之书,换数十铜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讶夫之回疾,视其行李,但见二三布囊磈磊然,铿铿有声,问得其实,乃詈其夫曰,你换得这个,几时近得饭吃,其人曰,他换得我那个,也几时近得饭吃,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张文潜是苏东坡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讲笑话,有时以笑话讥讽王安石。这个寓言式的笑话,当然不一定是事实,然而说明当时已有以古物换书的情况,是带有警惕性意义的,说明爱书和好古的两个书呆子,不如一个妇人聪明有见识,图书文物虽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吃饭。
以书易书,以文物换书,在文化界是普通事。封建社会还有以人换书者。《碧声吟馆谈尘》卷四记《美婢能诗》云《静志居诗话》载:明华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书,访得吴门有宋椠袁宏《后汉纪》,经陆放翁、刘次溪,谢叠山手评,饰以古锦玉签,遂以一美婢易之。婢临行时题诗于壁云:“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吉士见之惋惜,未几捐馆。这位朱学士真是书痴书愚,不惜以美婢换一部宋版书,一时高兴作错,及见婢诗,后悔莫及,怏怏而逝。读之令人感慨,戏剧中常儆人“莫怀古”,实针砭之言也。
扔书
韩少功
出版印刷业发达的今天,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书刊哗啦啦冒出来,一个人既没有可能也毫无必要一一遍读。面对茫茫书海,择要而读,择优而读,把有限的时间投于自己特定的求知方向,尽可能增加读书成效,当然就成了一门学问。笼统地说“开卷有益”,如果导向一种见卷即开凡书皆读的理解,必定误人不浅。这种理解出自并不怎么真正读书的外行,大概也没有什么疑义。
在我看来,书至少可以分为四种:一是可读之书。这些书当然是指好书,是生活经验的认真总结,勃发出思维和感觉的原创,常常刷新着文化的纪录乃至标示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峰。这些书独出心裁,独辟生面,决不会人云亦云。无论浅易还是艰深,都透出实践的血质和生动性,不会用套话和废话来躲躲闪闪,不会对读者进行大言欺世的概念轰炸和术语倾销。这些书在专业圈内外的各种读者那里,可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作广读或选读、急读或缓读的不同安排,但它们作为人类心智的燃点和光源,是每个人精神不可或缺的支撑。
二是可翻之书。翻也是一种读法,只是无须过于振作精神,殚思竭虑,有时候一目数行或者数十行亦无不可。一般来说,翻翻而已的书没有多少重要的创识,但收罗和传达了某些不妨了解一下的信息,稀释于文,需要读者快速滤选才有所获。这些信息可使人博闻,增加一些认识世界感受人生的材料;或可使人娱心,作劳作之余的消遣,起到类如跳舞、看杂技或者玩花弄草的作用。这些书在任何时代都产量极丰,充塞着书店的多数书架,是一些粗活和大路货,是营养有限但也害不了命的口香零食。人们只要没有把零食误当主粮,误作治病的良药,偶有闲时放开一下杂食的胃口,倒也没有坏处。
三是可备之书。这类书不必读甚至不必翻,买回家记下书名或要目以后便可束之高阁。倒不是为了伪作风雅,一心以丰富藏书作自己接待客人的背景。也不是说这些书没有用处,恰恰相反,它们常常是一些颇为重要的工具书或参考资料,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之所以把它们列于眼下备而不读甚至不翻的冷僻处,是因为它们一时还用不上,是晴天的雨伞,太平时期的防身格斗术。将来能不能用,也不大说得准。在通常的情况下,它们不关乎当下的修身之本,只关乎未来的谋生之用。它们的效益对社会来说确定无疑,对个别人来说则只是可能。对它们给予收集和储备,不失为一些有心人未雨绸缪的周到。
最后一种,是可扔之书。读书人都需要正常的记忆力,但擅记忆的人一定会擅忘记,会读书的人一定会扔书-把一些书扔进垃圾堆不过是下决心忘掉它们的物化行为而已。不用说,这些书只是一些文化糟粕,一些丑陋心态和低智商的喋喋不休,即便闲置书架,也是一种戳眼的环境污染,是浪费主人以后时光和精力的隐患。一个有限的脑容量殊可珍贵,应该好好规划好好利用,不能让污七八糟的信息随意侵入和窃据。古人说清心才能治学,虚怀才能求知。及时忘记应该忘记的东西,坚决清除某些无用和无益的伪知识,是心境得以“清”“虚”的必要条件,是保证思维和感觉能够健康发育的空间开拓。
因为“文革”十年的耽搁,我读书不多,算不上够格的读书人。自觉对优秀作品缺乏足够的鉴赏力和理解力,如果说还有点出息,是自己总算还能辨出什么书是必须丢掉的垃圾。一旦嗅出气味不对,立刻调头就走。每到岁末,我总要借打扫卫生的机会,清理出一大堆属于可扔的印刷品,包括某些学术骗子和商业炒家哄抬出来的名作,忙不迭地把它们赶出门去,让我的房间洁净明亮许多。
我的经验是,可扔可不扔的书,最好扔;可早扔也可迟扔的书,最好早扔。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时间已经相对锐减,该读的书都读不过来,还有什么闲工夫犹疑他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印刷业日渐发达的年代,也是扔书的勇气和能力更加显得重要的年代。
毁书
徐鲁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名著丛书》中的第二百八十种,是一部《现代英国小品文选》。其中有两篇美文,谈的是书太多了,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一篇是GilbertNorwood(1880-?)所作,题目就叫《书太多了》。大意是说,人类有史以来,已经出版了数不清的书,现在仍在逐年地增多,越来越多,不可能停滞。如此下去,其结果是:“我们被书压倒了,憋死了,埋葬了。”那么,如何对待这么多的书,怎样才能尽可能地把它们看过来,作者列举了几种人的读书以及处理书的办法,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毁掉一部分书---不要那么多的书。
另一篇谈书太多的文章,题目干脆就叫做《毁书》。作者是C.C.Spuire(1884-?),写的是作者自己因为书太多了,没地方搁了,便采取措施,亲手毁掉一部分书的经过和心理活动。
可是,作者写道,“书这东西,毁起来也不是很容易……我没有厨房里的大炉灶,我不能把它们放在小煤气圈上烤,或者把它们撕开,一片一片的放进我书房里的小火炉里烧,因为不把一本书拆开就想烧掉它,就跟要烧掉一块花岗石一样难。我也没有垃圾桶,我的垃圾倒在楼梯拐角的一个活门里,顺着一条管道往下走。我的困难是有些书的开本大,会把管道堵住……”
他首先要毁掉的那一部分书,是一堆不太高明的诗集。而且要紧的是,他根本不想让这些诗集“囫囵着出去”,免得让哪位倒霉的清洁工家里人从这些书里对英国的诗坛得出错误的印象。想来想去,作者决定采用“许多人对付小猫的办法”来处理这些诗集:把它们捆起来扔进大河里去!说干就干。他缝了一个很大的口袋,把那些平庸的书装上,趁着黑夜,走出了家门……接下去作者就写自己怎样背着这些蹩脚的诗集,在黑夜里,在巡夜的警察的怀疑的目光下,怀着事涉嫌疑般的心理,拐过宁静的街角,又蹑手蹑脚地走上郊外的大桥,迅速地、惊恐地把书倒进河水里的过程和心理状态。“可怕的蹩脚的书,可怜的无辜的书,”作者最后这样写道,“你们现在还躺在那儿;现在已经盖上一层淤泥;也许,还有那么一小块麻布片儿从装你们的麻袋里伸出来,在浑浊的河水里飘荡……你们也许不该遭遇这样的命运。我待你们太狠了。我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