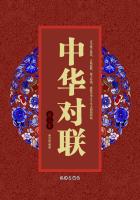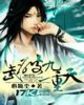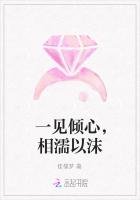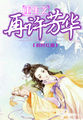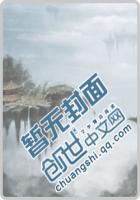册数最多的一套线装书是《东周列国志》,计有二十四册。这一套也是我的线装书中最老的一套,是乾隆年间的版本,纸张已呈浅褐色,订书的丝线也多断绝,致有一册残阙失页,另一册的封面也不知去向,却难得全套书都没有受到蠹鱼之害。我略略翻览,觉有书香扑鼻。那书香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清朝,遂不免有历史的联想。仿宋的字体紧密排列,朴拙可爱。至于首册中的几张插画,更透露着俚俗的趣味。严格说来,这些人物图像线条松散乏力,恐怕连“匠气”都谈不上,但每个人物依其个性、背景,倒也看得出煞费苦心的用意。比如褒姒与西施画得都不美,但衣饰繁富,颇见其衬托美人之旨。董狐执笔,范蠡泛舟,荆轲手握匕首诸图,也都能表现他们的故事。
《古文辞类纂》共十六册,仅次于东周志,是我所有线装书中面貌最完整的一套。这是民国初年在上海石印的。虽然纸张难免也有一些斑驳的褐黄痕渍,但整齐的欧体,字与字间的密度也较松,看来甚是宜人;尤其可贵的是眉批也都排印整齐。这是集合众先贤智慧的“百大家批评新体注释”版,书面有钮君宜署书。
我从前遇着研究版本学的人,见他们翻书,每每不太注意书的内容而偏于字体、版面、序跋等等年代印处之考查,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今日曝书,在书房之外翻弄这些旧籍,竟也有类似的好奇。大概线装书的迷人处即在此,总是令人分心。
其实,这些线装书大部分是民国初年的上海石印本,其中尤以扫叶山房发行者居多:《诗经集传》、《郭注尔雅》、《孙子十家注》、《亭林诗文集》、《烟霞万古楼诗集》、《仲瞿诗录》及《壮悔堂文集》均属此。印行的时间,则自民国二年到十五年不等。我如何得到这些线装书呢?是母亲十余年前送给我的。
有一套也是扫叶山房石印的《庄子》四册。杂陈众书间,貌不惊人,却为我所最珍爱。因为这套书里面有外祖父的朱笔圈点阅读的痕迹,又有一些眉批,可以令人想见他当日的感慨与心得。例如在外篇“胜箧”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有眉批:“愤言,痛言,至精之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云云。”不仅每字旁边都有朱圈,上又有眉批:“一部二十四史皆作如是观。”这四册线装纸张泛黄的老书,一度曾在他的掌中翻展摩挲过,当时圈点眉批之际的心境,仿佛可以想见。则书籍在握,已不仅止于版本年代之好奇与关心,而依稀有血肉亲情的温暖感受了。
这些线装书之中,只有一本是我自己在大约十年前于东京旧书店购得的《三谢诗》。虽然是影印本,但系印自宋代善本,而且有蓝底散碎金箔的封面,又有藏青布制的书箧包裹,所以也是我自己十分喜欢的。我曾经请台老师题字,那函套上有毛笔字迹:“景宋本三谢诗,文月女弟藏乙卯冬初静农题”。
另有一本封面较粗糙简单,而内容与此完全相同的《三谢诗》,则是十三年前在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游学时认识的匈牙利青年汉学家,于三年前辗转托人带自布达佩斯特。关于其人其事,一言难尽,此不拟细述,但其情谊可感,对于我来说,保留这重复的影本线装书,当然也纯粹是由于纪念的心理。
三大本《离骚图》的影印线装书,是若干年前静农师见赠的。除了屈原诸篇的文字,这套书的精华是在每篇前面的插图。计卷端合绘三闾大夫、郑詹尹、渔父为一图,又有《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清人萧云从画天上人间诸形象,有极丰富的想象力。风格虽也保留俚俗的民间趣味,却较《东周列国志》为可赏。
我一边铺排书册,一边随手翻阅,身体也跟着一本本的书移动,不觉地已在院子里来回过几度,背后感觉到暖洋洋舒畅极了。
曝书的末端是两种日本的线装书,一是三册一套的《富岳百景》,另外一本是日本的《变态刑罚史》。都是多年前静农师所赠送。其实,他送的书不止这些,另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旧书,但因这两种是线装本,所以与我其他线装书归类在一起,平时也冷藏“高阁”间。
久蹲着翻弄书籍,忽然起身,竟觉有轻微的目眩头晕,但片刻而愈。
我看到眼前院中是红砖、绿草与微黄的书皮覆地,三色相间,甚可欣赏。而台北居大不易,虽非大庭广宅,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庭院,已足堪安慰,又有线装书若干,未必善本名版,能这般偶尔玩赏,更是何等幸运。
举首,正见白云悠悠,三月的阳光煦和温暖。今日无风,正宜曝书。
托翁的书斋
〔日〕德富芦花
太阳已经西斜,剩余的时间,一刻抵千金。今天托尔斯泰看样子很累,我来后给他增添麻烦,实在过意不去。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出了小屋。正房的楼上,响起弹钢琴的声音,亚小姐在安慰父亲吧。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地踱着步子,托翁下楼来了,他把我领到书斋的阳台上。
阳台的椅子上摊开着正在阅读的英文书,是关于缅甸的著作。谈话提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日文翻译。我对托翁谈起了以《我之宗教》为主的他的所谓再生后的各种著作的日译本,谈了有关“无我之爱”的运动。托翁提到一位受迫害的波斯觉醒者的事,询问了日本基督教的现状。他说,泛神教不该舍弃。过一会儿,他拿出一部俄文书,说:
“这是我编纂的,集合了日日服膺的金言,一天一个问题。你看,这里有福音书上的句子。这里有哈伯特·斯潘萨,再加上自己的见解。我天天打开来熟读默思,这是我的祝愿。等着吧,你的生日是十月二十五日吧?很遗憾,这书还只有上卷,到六月三十日为止。”托翁颔首,一边翻书,一边阅读:
六月三十日
马尔他啊,马尔他啊,你为这么多事情忧思烦神,理当得以实现的只有一个。
(《卢卡传》第十一章四十一、二节)
人若不去救世,而是一心寻找自我救助的办法;不去解脱人类,而是一味寻求自身的解脱,那么为拯救世界人类而尽力这句话,又怎能得以实现呢?
人若由解决一切外在的问题转向解决人类当前的大问题,也就是思考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生这个大问题,那么其他一切外部问题自然就会获得解决。
“最后是我的话。”托翁合上书本。这对于我真是最美好的赠言。阳光薄薄地照在阳台上,书斋已经昏暗。托翁问我今后的行程,他说要为我开具介绍信,随之扭亮蓝色的中型台灯,坐到了书斋的桌子旁边。得到他的允许,我呆在他的书斋里,看了看周围。托翁的书斋约有十铺席大,两张黑漆的红木桌子,两把椅子。屋角放着黑皮沙发,墙壁间有一架小书橱。桌上散乱的书籍里,有法文的《社会主义心理》著作。四壁挂着好多画像,西边的墙上分别挂着五幅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白木的地板,对于病后的老翁,这是个安乐的书斋。尤其是夫人离开莫斯科在这里夫妇共居以后。透过灯光望着托翁的面孔,头顶微秃,头发灰白,稀疏,低垂的前额,刻满了深深的皱纹。他蹙着眉,一边叹息,一边运动着鹅毛水笔。算起来,托翁明年就到虚岁八十了。这位暮年的预言家,形骸日渐衰弱,然而内心却烈火方炽。他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甚至使我潸然泪下。托翁分别写了到圣彼得堡和到莫斯科的介绍信。写完,他把笔插进笔套。他一手擎着灯,站起身来,对墙上的画一一作了说明,这里有亨利·乔治的像,有前年故世的托翁的哥哥的像,有北美合众国不抵抗主义的先驱、已故葛里森的像,据说是他的孩子送的。在葛里森下边,是一位画着怡然自得的农民的油画。我问托翁,托翁说:“这是一位未读过一本书的大彻大悟的农民,名字叫做什么来着,-近来一到晚上,脑子就不顶事了。”“挂这些圣母像,是因为喜欢拉斐尔吗?”“不,这是我姐姐赠送的,姐姐如今在尼姑庵里,她说我的见解是错误的。”托翁笑着说。
谈话又从拉斐尔转到了托翁的《艺术是什么》上来。“您现在仍然坚持那些见解吗?”“然。”托翁答道。“这么说,真正的艺术来自最善良的人性。”托翁接着我的话补充说:“而且必须为普通人所能接受。”他熄了油灯,又来到薄暮冥冥的阳台上。
我深深感谢托翁的盛情。我不懂托翁的祖国的语言,而使用了极拙劣的英语,提出了一些愚昧的问题,打扰了托翁。我握着托翁的手说:
“先生善自珍重,前天先生谈到死是一种解脱,然而我希望不必如此急于解脱,依然要永远活在世上,永远工作下去。先生放心吧,即使在和俄国作对的流血的日本,也有不少是闻先生之风而奋起或正在奋起的人们,通向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前天先生说自己28岁,先生如果是28岁,那么像小生一样的人或许只能是刚出世的小孩,或者是正在出生的婴儿。生命在发展,先生和后生一起努力奔向光明,祝先生健康。”
五日。四时起床,五时乘上马车。早晨很安静,家里一片沉寂。马车离开这个家庭,向绿叶扶疏的坡下驶去,出了大门,向左拐,登上斜坡。回头一看,银白的晨雾包裹着雅斯纳亚·波里亚纳的山林。村鸡未醒,鸣声依然带着睡意。再见吧,雅斯纳亚·波里亚纳!我在马车上,摘下帽子,鞠了一躬。当然没有一个人看到。马车驶过前天我曾困惑地伫立过的十字路口,直向北边的查塞克车站奔驰而去。
看到了托翁书斋的火光,有谁知道照耀世界的光芒,就是这位老翁窗内的灯光?
陈德文译
我的书房
〔法〕蒙田
我在家的时候经常躲进自己的书房里。我就在书房主管家中的一切事务。我坐在门口处,下面的花园、饲养场、院子,以及本寓所的大部分地方尽收眼底。我在书房里有时翻翻这本书,有时看看那本书,不作严格的安排,也无一定的计划,多方涉猎,随兴之所至。时而沉思默想,时而一边踱步,一边将自己所想的记录下来加以组织,便形成如下的文字。
我的书房设在塔楼的三层。底层是我的小礼拜堂。第二层设置一个房间,其旁为附属的居室。为了安静,我经常在那里歇息。卧室之上有一个藏衣室,现已改做书房。从前那是屋里最无用的地方。现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日子,我一天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消度。晚上我是从来不上那里去的。附于书房之侧的是一个工作室,相当舒适,冬天可以生火,窗户开得挺别致。要不是我担心破费(这种担心使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便不难建一条长一百步、宽十二步的与书房相平的长廊,将各处连接起来,因为全部围墙已现成存在,原先是为其他用途而筑的,高度正符合我的要求。隐居之处都得有散步场所。如果我坐下来,我的思路就不畅通。我的双腿走动,脑子才活跃。凡是不凭书本研究问题的人都是这个样的。
书房呈圆形,只有我的桌子和座位处才成扁平面。全部书籍,分五格存放,居高临下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在四周围了一圈。书房开有三扇窗户,窗外一望无际,景色绚丽多彩,书房内有一定的空间,直径为十六步。冬天我上书房不如平时勤:因为我的房子建于山丘之上,就像我的名字所指的那样,没有别的房子比它更招风的了。我倒喜欢它位置偏僻,不好靠近,无论就做事效果或摆脱他人的骚扰来说都有好处。书房就是我的王国。我试图实行绝对的统治,使这个小天地不受夫妻、父子、亲友之间来往的影响。在别处,我的权威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并不可靠。有一种人,就在自己家里,也身不由己,没有可安排自己之处,甚至无处躲藏。我认为这种人是很可怜的。好大喜功的人,像广场上的雕像一样,无时不爱抛头露面。“位高则身不由己。”他们连个僻静的去处也没有。某些修道院规定永远群居,而且做什么事情众人都得在场。我认为,修士们所过的严格生活,最难熬的要算这一点了。我觉得经常离群索居总比无法孤独自处要好受一点。
如果有谁对我说,单纯为了游乐、消遣而去利用诗神,那是对诗神的大大不敬,那么,说这话的人准不像我那样了解娱乐、游戏和消遣的价值。我禁不住要说,别的一切目的都是可笑的。我过着闲适的日子,也可以说,我不过为自己而活着,我的目的只限于此。少年时候,我学习是为了自我炫耀;后来年岁渐长,便为了追求知识;现在则是为了自娱,而从来不曾抱过谋利的目的。
梁宗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