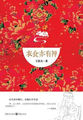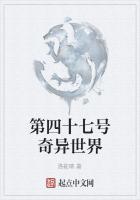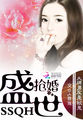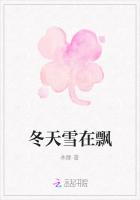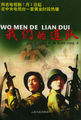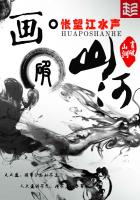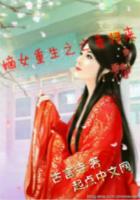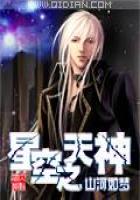怀念北大图书馆
冯至
我在北京大学当过6年学生,也当过18年教师。在那里既读书又教书,若说跟那里的图书馆没有什么关系,这不可能,若说我跟它有难解难分的情谊,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北大图书馆以及它的“分支”都历尽沧桑,有过不少变化,我也就跟它有时疏远,有时亲近。
我当学生的时候,北大图书馆主体设在北大一院红楼的底层,书库和阅览室都是利用与课室没有区别的大大小小的房间。所谓“分支”,我指的是那时各系办有自己的图书室,供本系师生使用。我从1923年至1927年在本科德文系学习,曾充分利用红楼三层东北角德文系的图书室。这图书室非同小可,它具有德国大学里日尔曼学研究室的规模。二十年代初期,德国战后通货膨胀,马克贬值,用少数外汇可以购得大批德文书。北大校当局有远见,不仅买书,还请来一位颇有声望的教授。这位教授著有德国文学史,出版过研究莱辛的专著,编过浪漫派女作家贝蒂娜·封·阿尔尼姆的全集,他的姓,译为中文为欧尔克。那些书主要是在他的建议下选购的。他热心指导编目,把图书安排得井井有条,从古德语文献到当代文学,名家的作品应有尽有,也有少量历史、哲学书籍以及德语翻译的其他国家的文学名著。这些书放在约20座高高的书橱里,钥匙由一位年老的工友掌握。图书室也是系办公室,上午教师们在里边休息聚会,下午学生可以自由进去阅读,要看什么书,工友就打开橱门取出,当然不准带出室外。德文系的学生人数很少,走进去不愁没有北京图书馆新貌渊蒋建国作座位。我在那里度过无数有意义的下午。除了温习功课、整理笔记、读教师指定的参考书外,也翻阅课业以外的书籍,如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裴多菲的诗集等都是我在那里首次读到的。面对丰富的图书,只怨自己德语根底浅,有些名著还读不懂。我有时也在这幽静的环境里干些旁的事,写点诗和散文,或给朋友写信。我常常一坐就是几小时,直到工友要关门了,才走出来。在返回宿舍短短的路上,不管天气是好是坏,总觉得一身轻快,欣庆从书本上又获得了一些知识,懂得了一点道理。
十九年后,1946年,我又回到北京大学,在外文系教德语。这时北大图书馆早已不蜷伏在红楼的底层,而是有独自的建筑了,它的“分支”也大都回归主体。馆内有比较宽敞的阅览室,有几层楼的书库,底层东西两侧有两列研究室,供教授使用。我分得靠西边的一间,自己掌握钥匙,我在里边工作,有时一直到夜里闭馆的时候。那时北平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十分尖锐,岁月沸腾,群情激愤,我也参与一些活动,但一走进这间小小的研究室,就好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外来的干扰,容许我全心全意做我最喜欢做的工作。我的教学任务是教德语,但我自己给我的一个迫切任务是给杜甫写传。我在四十年代后期写出《杜甫传》初稿的主要部分,不能不感谢北大图书馆给了我许多方便。图书馆领导不仅分配给我研究室,还准许我走进书库去找我需要的参考书。我找出杜集各种重要的版本,还有关于唐代地理、历史、制度的典籍袁都是先从书库里取出,然后才办借书手续。那些书放在研究室里的书架上,使用时可以信手得来,真是一种享受。在书库里翻阅书籍,时而也有意外的发现。有一次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罗振玉编的《芒洛冢墓遗文续补》,不料其中收有一篇洛阳出土的《杜并墓志铭》。杜并是杜审言的次子、杜甫的叔父,死于为父报仇。《旧唐书·文苑传》里说“审言子年十三”,可是墓志铭里写着杜并“春秋一十有六”,相差三年,虽不重要,却也足以纠正史书上的一个错误。我记忆中还有一件小事。一天我在书库最上层一些未编目的书籍中见到一本德文版的《反杜林论》。我取下来翻阅时,里边掉下来一页信纸,是一个苏联人用德文写的。收信人的姓名从拼音可断定是罗章龙。据说罗章龙曾经是德文系早期的学生,也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我认为这页信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把它交给当时讲授博物馆学并计划在北大建立一个小型博物馆的韩教授(韩寿萱,陕西人,时为史学系副教授)。后来博物馆的设想没有实现,韩教授也逝世了,那页信也不知下落如何了。
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到城外,这座图书馆楼不知后来派了什么用场。我常常怀念它。
我是1964年离开北大的。如今北大校园内建立了一座规模更大的现代化图书馆,我无缘享用。有时因事去北大,路过那里,只是从外边望望而已。
甬江藏书有名楼
徐柏容
浙江宁波在二三十年代曾以巨贾辈出而闻名,如今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又以商业发达而驰誉全国了。除此之外,宁波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天一阁更是名闻中外的一座藏书楼。
这座天一阁,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始建的,五年后建成。范钦是进士出身,好学耽读,藏书丰富。天一阁为藏书而建,到今天已经有400多年了,是我国现存的一座最古老的藏书楼。解放后,天一阁被国务院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曾多次拨款加以维修,所以,现在看起来,仍然整齐宏伟,令人感到一股书香气。
范钦当年建成天一阁后,阁中有其私人藏书7万余卷,其中不少是宋刻珍本、孤本以及抄本等善本。范钦是个十分爱书的人,他不仅根据藏书需要而规划楼的格局,而且在建楼时就考虑了防火、防蠹之类问题。为了防火,阁前修有蓄水池。天一阁原名东明草堂,其所以改名,也暗寓有防火之意。因为《龙虎山天一池记》中有“天一生水”之句,改名天一阁,就是要以水制火。在防蠹方面,历来相传天一阁的书是不生蠹虫的。原来它采用的是所谓“英石芸香辟蠹法”,具体做法是在书柜脚下放置能吸潮的英石,在书页中夹进能避虫的芸草。但是,后来在好几个书柜里还是发现过蠹虫,说明这种防蠹法也并非万无一失的。但从这些地方,却都可以看出范钦护书的苦心孤诣。
除了火、蠹之类天灾外,藏书更怕人祸。范钦这样爱书的人,自然不会不考虑到这方面。所以又制订了一套严格的禁例,以加强管理,包括规定子孙后代永不得分书;阁中之书只能在阁中阅读,不准携出阁外;非范氏子孙不得入阁……这些规定,使藏书难以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我们今天也许还可以批评它有着浓重的私有观念。但是,为了藏书能长远保存,聚而不散,当日悬此禁例,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建阁以后百年之间,天一阁藏书得以基本保持完整,不能不归功于范钦之深谋远虑。
但是,到了乾隆年间开始编修《四库全书》时,朝廷广征天下藏书,限期上交,天一阁的祖先禁例也就无能为力了。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被迫不得不多次“献书”,前后共“献”出了600余种,居全国“献书”数之首。加以在此前后,官吏盗贼交相侵取,禁例也日渐松弛,其后藏书散失很多。到宁波解放时,只剩下13000余卷了。但是,比起其他藏书名楼如铁琴铜剑楼、海源楼来,总还是更胜一筹。
周恩来一向关怀文物古籍,于战火硝烟、戎马倥偬中亦未或忘。宁波解放前,他就曾指示南下部队保护天一阁。我们今天徜徉在天一阁中饱嗅书香,免不得还要涌上对周恩来的感怀之情。解放后几十年来,天一阁不仅扩建、充实,规模更大了,而且,还回收了失散的原有藏书3000余卷。加上增添的新藏,现已有30多万卷,远远超过了范钦原藏之数。
走进图书馆
舒乙
居然,要提这么一个口号。其实,这是完全必要的,此时此刻,是既现实又需要的。话要分两边说,一是从读者来说,二是对图书馆本身来说。对前者,是呼吁他们走进图书馆来;对后者,是打开图书馆大门,不要设置层层障碍,把读者全挡在外面。眼下,这两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很有必要大声疾呼一下,重提口号:走进图书馆!
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是它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得如何,越发达的国家,图书馆事业也相应越发达,几乎没有例外。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完成的。鲁迅先生长期在教育部任佥事,分工是专门负责管图书馆、博物馆和通俗教育的。李大钊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员。这些都是近现代名人和图书馆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例证。近几十年以来,建图书馆更是成了一桩公认的最好的公益事业,历届美国总统下台后都兴建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大图书馆。香港邵逸夫先生十几年来为国内学校捐资兴建了100多座图书馆。图书馆事业确实得到了全人类的普遍关注,它是人类智慧的储存所,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展厅、载体和交流站。图书馆成了现代人类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其价值完全和空气、水、食物一样。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1949年之后,发展得相当好,发达的区县都有大图书馆。而且1978年以后,差不多又都有新一轮的馆舍兴建或改装,应该说,从硬件投资上说,在国家眼中是有图书馆“这一号”的,情况是不错的。问题出在日常经费上,近年来,财政口的图书日常经费拨款普遍不足,进书量日趋减少,呈现一种滑坡,这种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读者的光顾。
不过近年来,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在读者身上,在主观上,读者大大冷淡了图书馆,进图书馆的读者人数直线下降,这倒是问题的真正症结。现在的问题是有图书馆而不懂得利用了。
人们,包括一部分年轻在校学生在内,似乎兴奋点不在读书上,大家纷纷为想办法急功近利地挣钱而忙碌,把取得知识和利用知识放在一边了。这种浮躁一旦形成气候,风气便随之而变,图书馆的冷清也就渐渐出现了。
所以,图书馆的兴衰首先是和人们的认识有关。终究,人们会认识到,财富和进步不会产生于投机,而只能产生于科技,产生于知识,产生于老老实实坐图书馆和人们的生产、社会实践。
人们回归图书馆是早晚的事,大势所趋,必然如此,别无他路,放心好了。
关键是要把图书馆办好,坚守这块阵地,使它们越来越开放,敞开大门,欢迎大家去利用。当前,图书馆事业的一大弊病恰恰是“不开放”。譬如:进门就要钱,环环节节都要,把人要怕了;手续很繁琐,耗时耗力,把人等怕了;资料封闭,层层设障,把人吓怕了。一句话,仿佛怕别人去利用似的。应该说,眼下我国的图书馆管理和国外先进国家的同行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差距主要不表现在有没有电脑,有没有缩微,而表现在管理模式陈旧,封闭保守,把读者拒之门外。要把立足点转到开放上来。图书馆要重提“改革开放”,即改革管理,向读者开放。要大胆地提:进图书馆不要钱(复印收成本费等等规定是正常的);
报纸、杂志、一般图书要开架;
图书馆不出租馆舍卖衣服、卖家具;图书馆要办讲座、办展览、办座谈会、办观摩会,想尽办法用知识、用文化招引人;图书馆原则上出入自由,简化手续,包括善待儿童。图书馆大有可为,还是那句话,立足点要变一变。事情往往是如此,观念一变,全盘皆活。
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
丘颖
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大楼与国会大厦毗邻,可与苏联列宁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并列,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图书馆大阅览室的拱形圆顶以及四周的墙壁都镶嵌着精美的壁画,一排呈弧形的目录架上有21332个抽屉,内有1800万张目录卡。目录卡每年以100万张的速度递增。国会图书馆创立于1800年,现有藏书1800万册,收藏图书语种为468种,照片800万张,地图300余万幅,手稿3100万件,乐谱400万篇。现在馆内书架总长度已达到851公里,图书还是塞得满满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很有特色的。首先,它注意收藏可能再现历史的展品。国会图书馆的大展厅内陈列着标志现代西方使用印刷术开端的格登伯格《圣经》中的《创世纪》,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初稿,华盛顿第一任就职演讲词的原件,甚至还保存有卡尔文·柯立芝写的“我决定不参加1928年总统竞选”的小便条。这些收藏给人们以强烈的历史感。而整个善本阅览室则充满了另一个时代的气氛,那里甚至珍藏着1604年出版的马萨诸塞圣经诗篇。1604年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算不上久远,但对美国来说,这是殖民地时期最早印刷的图书。所有的善本图书都放在地下书库,这里常年保持在恒温20摄氏度和50%湿度的环境之中。
其次,美国国会图书馆又是版权图书馆。19世纪70年代国会图书馆设立了版权处,从此它就成了保存所有版权的版权图书馆了。这意味着出版商必须把在美国出版的每一本登记版权的书交给图书馆。这对于图书馆是一个极大的资料来源。据统计,仅一年免费提供给国会图书馆的出版物价值就达550万美元。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这使国会图书馆能够完备地收集到各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