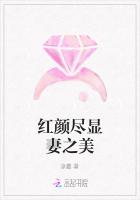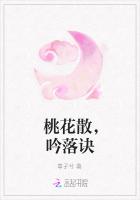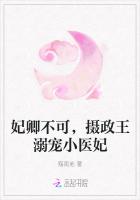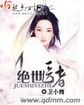《无名桥》对中国现代农民生活的文化解析意义
读韩向阳的长篇小说《无名桥》,总会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小说,特别是他在变形、夸张日常生活的某些现象和有意打乱时间顺序等手法的运用上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
《无名桥》以深刻的思想内涵、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狂欢有余而节制不足的语言风格,表现了一个小山庄——大沟村所承载的社会进程中人性嬗变的文化记忆,折射出中国农民在改朝换代中均贫富、共患难的思维方式和在太平盛世的历史助推中笑人贫、恨人富的人际间的微妙心理。当然,还有对蛮横、无知、狡黠、自私、嫉妒、趋同、盲从等劣根性的有力鞭挞以及对集体无意识的警醒。
当前,中国农民占到国人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而且即便是城市人,上溯三代基本还是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所以,了解了农民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也就基本上了解了中国国民的性格特征。长篇小说《无名桥》深刻、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的喜与乐、悲与欢、思与忧、想与盼,对当下国人的品性作了文学意义上的诠释,为我们进一步正视中国社会、反思人类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提供了深度的思考空间。从文本上看,他的作品主要显示如下特点:
首先,作品的一些戏仿、黑色幽默和拒绝平铺直叙的特点,弥漫出浓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味道。韩向阳统揽小说的思想观念显示了他在哲学层面充分认可事物不确定性和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语言狂欢和较为复杂的叙事上,更表现在他所呈现的生活及人物的荒诞行为上。叙事是以萧大春三十多年前的修桥事件为切入点,在当下和过去视角的交替闪回中,来审视和回味新中国成立初期敌我斗争和“文革”政治狂热的一些经典片段,以戏仿、黑色幽默等艺术形式来表现人与自我特别是人与他人在政治斗争中的异化和无奈。
在以萧大春病的缘由而当下的商战竞争、官场争斗中回望、反思“文革”运动及土改历史。在土改时,写出了那种社会阶层更迭的大颠覆带给人们的兴奋、振荡和不安,以及观念剧变、是非标准特别是阶级价值体系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在“文革”中,主要表现出那种对当权派、造反派、革命派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政治意义消解;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则入木三分地描摹了某些暴发户的炫富特点和农民的种种复杂心态。从家长里短说到世事变迁,又以人物成长连接大沟村史,使时空在叙事的变换中延展,让事件在人性的嬗变中贯穿。向阳的一些看似荒诞的描写其实最真实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已经或正在并且将来还要注定继续上演的惊人相似的命运,在对中国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呈现中,充分揭示政治经济文化对个体的私生活的强烈干涉,从而生发出文化命题中的另外一些新的更为宽泛的阐释意义。
其次,语言幽默风趣、机警智慧。文本的最大特征是语言的狂欢,无论叙述、议论还是对话都很到位。《无名桥》的语言使每一种议论、每一个描摹、每一句话语都向文本的主体负责,使繁复的叙事显得有条不紊而且整体格局明朗清晰,也使得话语在故事推进中产生的多维性、开放性、奇异性、歧义性的一些特点更加鲜明地跃然纸上。
可以说,语言是向阳这部特立独行作品的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他的语言风格是以叙事语言的能指向着所指进发,由人物而产生事件、由事件而表征性情、由性情而反映人性、由人性而阐释文化,在悖论的笼罩映射下向着被文化观照着的人性的隐秘地带前行。在行进中裹挟枝节叶蔓、阐发思维空间、承载乡愁别绪、书写春华秋实,使大沟村人情世故的纠葛摆上文化的祭坛;在浴火重生中再现庸常人生的灵魂仪态,进而张扬性情、彰显人格,使作品显得厚重、内敛而不张狂,幽默、风趣而更为卓然。语言的狂欢使他的话语方式不仅形象、生动地表述了故事,而且引领了叙事并最大限度地开启语言与阅读的间离效应,使读者对真实产生怀疑,进而拉大语言的能指与所指间对应关系的不确定性,从而来包容更多不相关联的伦理和文本的形式意义,增强错位的滑稽感和幽默感。
再次,人物个性鲜明、活灵活现且有些人物的言行给人很强的荒诞感。如萧大春这个贯穿始终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人物塑造,是在修桥这一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叙述场和叙述主线中完成的。于是,萧大春被赋予了具有种群延续精神的开掘意义。当然,文本更多的真实则是塑造了一个既反映时代又消解崇高的人物形象群。这些人中:有机会主义者和小农经济意识的代表;有群氓无赖;有体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有整天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何时打起来,好排兵布阵以显神威的“军方人士”五爹;有最早把握了国家政策动向、顺应潮流却难逃厄运而不得善终的暴发户;有意欲制造飞机飞到美国的幻想狂国生;有心态失衡而歹毒阴狠的精神分裂者国铭;还有以皮肉赢得权力换取金钱的烂屁股女人。这些人物鲜活、自然、真实、可信,他们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甚至被极端化了的缺点,但他们的某些心理活动、思维方式、价值判断、行为习惯无不体现我们民族文化中那些更有现实意味的共有属性。
当然,《无名桥》所塑造的代表人物萧大春的现实理想就是要造一座便民桥,为此,他舍弃工作、甘当农民,一心一意、无怨无悔、不屈不挠、一如既往,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念念不忘修桥使命,这与别人千方百计捞取私利形成鲜明对比。其实,中国永远都需要这种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于是,在这里,桥的形而上的意义成为沟通理想与现实社会的一种联系的象征,尽管萧大春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悲壮依然没能消解宗教般的受难感。与此对应的另一个当权人物村支书的玩弄权术和他传承政治的想法颇有意味,显示出国人或多或少都有当家理事的政治野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在强化、助长“官本位”和全社会努力塑造“人上人”思想的结果。在中国社会,一个丝毫没有达则兼济天下理想的人,其素质高低一点也不妨碍他的进取意识乃至最终的成功。
所以,这种无名桥的乌托邦,实质上是把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意识与现代文明对接的不协调性显露出来,进而把传统文化与民主意识的错位造成国人劣根性放置在现代空间,更显现文化共时性与历时性在交织点上坍塌、断裂的无奈。因而我们说,《无名桥》的叙事是一种纳入文化视野、反思传统文化和反映人性嬗变的写作,是一种在历史血脉相连的悖论呈现中折射人的不屈精神的写作。这种写作能够把人物写得内敛内在,收放自如,即便是对于极端化的人物国铭的行为,也处理得恰到好处,把那种仇富心理和富裕之后带来负面影响的象征意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现实的我们,可以不顾及无名桥是否能够架设成功,也可以不用思考能否实现社会大同,因为身处滚滚红尘中的我们是非常现实和渺小的。但作为一个中国的现代人,如果要想继续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就不能不警醒一些人格缺失、道德沦丧、集体无意识带来的负面因素,切记国际间竞争是必然存在且永远没有公理可言的,落后和民族精神缺失是必定要挨打的,无非人家不一定再用血腥的狂轰滥炸而改用温文尔雅的文化侵略或以经济手段进行资源掠夺罢了。在适者生存的法则面前,麻木不仁的后果很可能会是“温火煮青蛙”般那种不期然的意料结果。
由此,我们看到,《无名桥》这种对人性的开掘力度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警示作用振聋发聩、令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