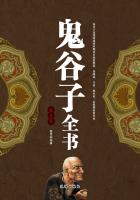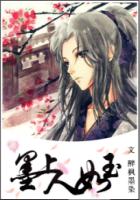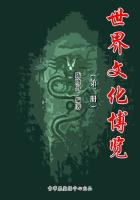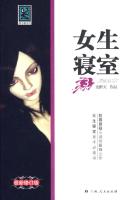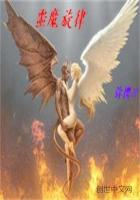在清华平静任教的5年时光里,闻一多虽然没发表过一首诗,但是,他完成的论文包括《诗经》、唐诗、楚辞、神话、甲骨文、金文和文字考释等多方面领域,冯友兰评价说他的学问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诗歌批评方面,闻一多仍寄寓着对中国新诗的设想。1933年7月,他在臧克家的诗集《烙印》的序中,从以往对形式的关注转到了对内容的重视,他引用诗集中的诗句说明“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并说“作一首寻常所谓的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作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好诗,却大不相同”。而且他举例,认为将这种创作取向引申到古典诗歌传统中,臧克家继承了孟郊的传统,而批评苏轼的传统,“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来的力,像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蛰吻涩齿’或‘如嚼木瓜’……”在新诗的追求中,闻一多依旧保持着《红烛》时代的激情,有着如他当年经历五四运动时希望打碎一切偶像的浪漫主义情怀。不过,随着年纪和社会阅历的增进,闻一多也日渐明白,浪漫主义较之理性主义是缺乏自信的,更需要一种外在的新偶像,作为激情的依附对象。不管是年轻时代的诗歌创作,还是中年时期的学术研究,无疑都是作为他狂飙情感的一种介质,是能让他的精神获得归宿感的真实载体。
闻一多出生楚地,古代的楚国不仅诞生了一位躬耕不食、佯狂不仕的楚狂接舆,而且也出了屈原这样的浪漫主义大诗人。对这些远古先人,闻一多一直视其为楷模。在早年的诗篇《李白之死》开首,他就引用李白的诗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作为自己的精神白描。后来,他在世人的面前多了“学者”、“民主斗士”等诸多形象,这不过是以他诗意的精神,去实践他的人生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现实生活里,构建尼采哲学精神中的浪漫主义理想王国而树立的形象。不管他如何“三变”,贯穿他整个生命体系的依旧是诗的浪漫,诗的激情,诗的色彩。从书斋隐士到“革命斗士”的转变
当年,学者罗隆基对闻一多的一生归纳为“三变”:第一变,希望在诗坛上大有作为的闻一多选择了国家主义;第二变,30年代不再写诗,转而成为书斋隐士;第三变是在40年代,从一个学者变成革命斗士。在许多同时代的在政治上认可闻一多的人所写的回忆录里,包括对他的评价,其实并没有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闻一多。在他们笔下,营造出的闻一多并非是知识分子,而是战士。
然而,曾在古典文学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获得极高赞誉的闻一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其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思想形态出现这样反差很大的转变?他变得有话说,要闹,当他有机会去美国讲学时,却偏偏留在国内这个“是非地”继续斗下去。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住宅附近被枪杀后,他的清华同学浦薛凤对此叹息不已:“予深信一多之性格、信念与作风,殆亦为此种构成因素之一。”这就是让我们需加以重新审视、深思的问题了。
性格说:理想主义浪漫激情
年轻时的闻一多,性格里被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充斥,这有他出生楚地,受乡土文化和家族观念影响有关,还有很大一部分与青春时代的五四思潮有关。闻一多从13岁考取清华学校到23岁毕业赴美留学,在清华园里整整度过了10年光景。这10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足以影响一生。而这10年,正是中国社会新思潮萌芽,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时期。而闻一多在北京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五四时期,从新文化运动到爱国学生运动的全过程,并手抄岳飞的《满江红》,表达内心的想法与情绪。到了1922年北京教师的索薪运动,他不再是个仅靠诗词呐喊的局外人,而是参与清华学生组织的集体罢考,支持抗议。即使在后来清华、外交部对罢考事件的处置问题上,他也表示出不妥协、不配合的态度。
似乎这个阶段的闻一多和40年代的“革命斗士”的形象相符。可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是,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强调科学,推崇理性,而实际上却是一群人热血沸腾的盲目追求。就五四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反叛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骨子里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作为五四精神产儿的闻一多,同样也逃不过与其他知识分子类似的宿命和选择。在西方启蒙思潮的理性作用下,他们主张“研究问题”,剖析现实,由于知识和视野的匮乏,又必须找到一种“主义”支撑思考模式,急于让所有的思考都有答案。这就促成了闻一多选择国家主义。
闻一多从美国归来之后的一段时间,还带着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他早年在清华接受了西方自由和民主观念的影响,他的民主观念是早熟的,对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也是以理想主义态度对待,加上他对社会底层有着天然的同情,很容易促成他对政治问题上的关心。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活动形形色色。闻一多却表现出令人奇怪的低调,他是新月社的成员,却没有新月社成员对社会现实的那种关注。闻一多初回清华时,对朋友罗隆基在政治上的一些理想抱负不以为然,一直持有自己的看法。闻一多是真正的诗人,出生楚地的他对屈原、庄子等人十分崇拜,楚人特有的浪漫主义激情影响他终生,也使他对社会政治抱有热情,但对于现实中的政治,他是既没能力参与也没有兴趣的。
在大学生活里,闻一多极少接触政治,即使是他在40年代参与的那些政治生活,也是以单纯的态度去对待,没有任何功利性,只是他为理想而奋斗的激情正好与某个政治团体的目的吻合。而这些政治团体,为实现预设的结果,也非常欢迎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加入。
进入40岁后,闻一多越来越看不起做官的人,体现出传统知识分子对权贵的傲视态度,总体上说,他的性格比年轻时更加偏激。对于闻一多的性格,许纪霖这样分析:“随着走出象牙塔,闻一多又重新燃起了浪漫主义的激情,激情的持续需要信仰的激励,一个斗士不能为斗而斗,他还需要奋斗的目标,需要某种乌托邦的理想。”
闻一多在40年代所追求的东西,或许连他都只有一些朦胧的意识,未必就清楚自己追求的东西会如何落到实处。他在那个阶段所写的文章,除了激情外,不少演说和言论中只提结果,缺少过程,甚至是简单和抽象的,难以探寻到实践的办法。显然,对于闻一多这样从少年时期就接受自由和民主教育的学者来说,没有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是不能适应的。当社会变得动荡,执政党的行为中越来越专制,他就会做出本能的反抗,在另一种精神依托上重新寻找一种“主义”,好让那股为理想奋斗的激情有依托和方向。
经济说:生活贫困和党政腐败
1940年后生活的巨变,是闻一多变成“战士”的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年,大后方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战争缩减了教授们的薪水,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闻一多家中子女多,负担重,每月薪金不足负担全家十天半月开支,最后只能靠变卖家用,透支、借债等办法勉强维持,就连他从北平好不容易带出来的几部线装古籍也忍痛卖给了清华图书馆。为了贴补家用,闻一多不断增加劳动强度,写文章,做报告,昼夜不停,堂堂大学教授干起了第二职业,除了刻印,还在中学兼课,可生活水平还是一降再降。为了节约,每顿吃的面粉,不得不靠买来小麦自己磨自己筛,闻一多甚至还亲自挽起袖子参加农耕劳作,所吸的纸烟也改成了自制的旱烟叶。对比30年代平静而物质优裕的生活,如今这般落魄的景象,不可能不使闻一多的心理产生微妙的变化,他的性格由此变得偏激也是难免的。
过去在北平,闻一多不仅是精神贵族,还身居大学这个世外桃源,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知之甚少,对他的冲击不大。抗战爆发之后,闻一多随学校徒步南迁昆明,一路上对大后方社会的落后和底层人民的贫困有了感性的认识,激起了他的同情。1940年以后,他沦为物质的贫民,整天忍饥挨饿后,那种困苦感和不公平感就变得直接和切身。再加上闻一多亲眼看见了统治阶层的种种腐败作风,达官显贵们在物质匮乏时代还大发国难财。闻一多虽然不懂政治,但哪怕再单纯的人,也都知道腐败与不公正所造成的民生凋敝,此后他就再也不能保持往常的超然,语气开始变得激奋起来。
倘若贫困尚可忍受,精神上的高压则让人忍无可忍。陈立夫主管教育后,加强了对大学的思想控制,他要求各大学校长以上的负责人都要加入国民党,还要统一交差等,引起了教授们的不满。闻一多和那些教授一样,都是出身清华、北大,然后留学欧美的,一直深知民主的好处,在思想上多数信仰自由主义。但不满情绪暂时还没有发展到反对的程度,毕竟在抗战时期,一般知识分子总认为国民党是国家的中心,蒋介石更是最高领袖。当时“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闻一多认为“只觉得那真是一个英勇刚毅的领导,对于这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