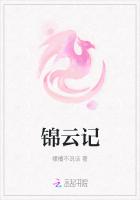1927年5月开始,闻一多经常参加新月社的聚会。徐志摩在上海筹建新月书店,打算出一刊《新月》杂志。闻一多买了书店的一支大股,书店开张时,他还特意绘制了“一个女人骑在新月上看书”作为开幕纪念册的封面。
当年7月,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刊登了闻一多的论文《诗经的性欲观》,在学术界引起不小轰动,武汉大学向闻一多发来聘书,请他担任中文系教授兼学长。1928年9月,闻一多终于实现了他年少时的梦想,站在文学的讲坛上分享他多年来的心得。
为了这份工作,他几乎放弃了诗歌绘画,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研工作去。除了讲课外,他在杜甫和庄子的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收集大量素材,写出了几篇不同凡响的论文来。可惜的是,他在任职的第二年,又陷入了学校人事矛盾的苦恼里,派系斗争愈加激烈,竟然有人煽动学生不去听闻一多的课。悲愤交加的闻一多干脆贴出告示,表明自己对这个职位如“鹓雏之视腐鼠”,宣告辞职。
辞去武汉大学工作的闻一多,再次来到上海,与朋友聚集。梁实秋的朋友杨振声正奉南京政府的派遣筹建青岛大学,于是便请他们去青岛大学任教。他们经过考察,认为青岛是个宜人的好地方,接受了聘请,闻一多担任中文系主任兼教授,梁实秋担任外语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在青岛大学,闻一多大胆创新,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唐诗”、“名著选读”、“英诗入门”等课程,同时对《楚辞》、《庄子》等中国古代文学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他不仅继承了清代文人运用音韵训诂的治学方法去研究《诗经》,还借鉴西方科学方法去解剖、诠释,对现代《诗经》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梁实秋称赞他“指示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说他的论文是“划时代的作品”。在此期间,他还挖掘与培养文学人才,对于一个语文得了98分,数学却是鸭蛋的学生,他坚持破格录取,这名学生最终成了著名的诗人,就是臧克家。
好景不长,青岛大学也出现了人事斗争和学潮。1930年11月,学校发现有一批学生报考本校时用的是假文凭,决定全部取消他们的学籍。全校学生罢课,表示抗议,教务长潘道光打电话找警察来维持秩序,并将一半的学生开除,此事算平息。然而一年后,潘道光将找警察一事推到闻一多身上,导致他成了学生们的攻击对象。1931年9月,学生响应北京学潮,又发生了一次闹学,不仅在本地游行,还一批批地要去南京请愿。10月,青岛大学成立了反日救国会,179名大学生不顾老师的反对坚决南下请愿,强行爬上火车,强迫司机开往南京。
南京政府要求青岛大学采取措施,阻止学生来请愿。闻一多作为学校的重要领导之一,也认为这种行为不能容忍,建议开除为首的学生。结果闹学潮扩大,学生都把矛头对准闻一多,学校的一些教员也怪他处置此事不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青岛大学学生又因对《青岛大学学则》里的条例不满,第三次大规模的闹学潮又起,把学校领导闹得疲惫不堪。杨振声校长主动向教育部请辞,学校陷入了无人管理的地步,最终教育部干脆下令把学校解散了。
1932年,闻一多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又回到了他熟悉的北京。回到清华,他吸取曾经的教训,决定向内发展,不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不担任行政领导一类的工作,关起门来埋头读书,做学问,搞研究。他很清楚自己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是破格的,这所高校特别看重资历,而他既不是中文或者中文相关专业毕业的,又没硕士、博士学衔(留美时学的是美术,美术专业没硕士、博士学衔),因此非下苦功夫不可。
在清华任教期间,是闻一多的文学研究硕果累累的时期。他策划了一项宏伟的工程,打算用5年的时间编写一部《诗经字典》,注明每个字的古音、古义、古形体,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部伟作没能完成。闻一多深入研究《诗经》,还间接研究了战国以前的原始社会、古代神话、古代民俗和文字学、音韵学等领域,他甚至破了千百年来儒学家们解释《诗经》的传统框架,用西方科学的办法去剖析,在当时开拓了研究《诗经》的新途径。而诗歌却没一篇问世,在清华的5年时间里,他已把兴趣从艺术政治活动转向学术研究。
1937年,闻一多执教清华已满5年,按规定可休假一年,进行考察、调研、进修或者搞研究都行。闻一多打算回老家进行《诗经词典》的研究,正巧弟弟要回乡见亲眷,就让妻子和两个孩子随弟弟先走。
不久,发生“七七事变”,北京被日本兵包围,形势危险。闻一多只好带剩下的孩子离开,仅带得两部古书和一些手稿。事变过后,清华大学奉命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合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于南下教师少,学校就让闻一多推迟休假,先到长沙的临时大学来任教。
刚在武昌与家人团聚的闻一多又动身去长沙,当年10月末抵达长沙。由于市内地方狭窄,临时大学的文学院转到了衡山脚下的圣经学校分校里。由于物质匮乏,当地生活习惯差距大,闻一多颇感不适,却没停止过古籍研究。
1937年冬天,上海、南京相续沦陷,日军又沿平汉线和长江两岸推进,直指武汉,长沙也成了危险之地。临时大学经国民教育部同意,前往昆明。迁移办法是,教职员发给路费津贴,身体强健的男学生统一组成旅行团,徒步去昆明。女同学或者身体弱的,学校安排车船前往。
闻一多与家人商量,让他们也转往昆明。这时老朋友顾毓琇来访,告诉闻一多他已担任民国教育部次长,正在筹建战时教育研究会,希望闻一多能参与。可是闻一多认为去政府工作就是“做官”,断然谢绝了老友的邀请。此事让妻子非常不满,埋怨他舍近求远,又要与家人分离,并带着孩子们与他怄气,一直不给他写信。
由于家庭人口多,开支大,为了省路费,闻一多参加了旅行团,徒步去昆明。师生们听说后都十分惊讶,杨振声还嘲笑他说:“一多参加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冯友兰等几位教授约好先游桂林,再从广西从安南去昆明,最后还是因“费用过巨之故,仍改偕学生步行”。
此次徒步去昆明,历时68天终于抵达。一路上,闻一多游览了大批名胜古迹,看到了沿路的少数民族风情,他还用绘画写“日记”,记录下所见的美景,并指导学生开展收集当地歌谣的工作,苦中作乐地和教员们蓄胡须,给妻子的回信中他说:“你将来不要笑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
4月28日,旅行团抵达昆明,学校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闻一多在昆明收到了四封家书,十分高兴,连忙给妻子回信说:“你说以后每天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每星期回你一封。”一场因他不愿留下做官而引起的家庭风波就此结束。困守昆明的烽火岁月
临时大学的文学院设在云南省的一个边陲小镇——蒙自,租用了法国人修建的一座小洋楼。闻一多到了蒙自,觉得这小地方偏僻安静,打算安住下来,进行研究。
每天除了吃饭、上课、如厕外,他从早到晚都不愿下楼,同事们都劝他何妨下楼来,最后落了个别名,叫“何妨一下楼先生”。而他不愿出行的原因还是因手头拮据,他在给妻子的信里说:“蒙自的地方很小,生活很简单。因为有些东西本地人用不着,我们却不能不用的,这些东西都是外来,价钱特别贵,所以我们初到此需要一笔颇大的‘开办费’。但是这些东西办妥了,以后恐怕就有钱无处用了,归根的讲,我们住蒙自还是比昆明省。”
南京沦陷后,日军继续进攻武汉和广州,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浠水巴河老家里,那里是日军攻打武汉的必经之路,情况十分危险。闻一多决定把家人接到昆明来,但面对的压力、阻力不小。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日来正为此事踌躇,同事们也都劝我接你们来,所苦者只有两事不易解决:一、我自己不能分身,而家中又无人送你们。二、你们全来,盘费太大,今天接到陈文鉴来信,其意甚愿来滇复学,万一决定来,你们可以同他一路走,我只需到香港或海防来接你们,既可省点路费,又不多费时间,岂不甚好。至于你们的路费,我计算起来,少则五百元,多则六百元,数目实可观,然而为求安全起见,又有什么办法呢?”
为让妻儿来昆明,闻一多费尽心思,想了许多办法都无计可施时,他开始十分后悔当初没把妻儿们带出来,想到战乱,他也只好在信中求上天保佑了。1938年6月下旬,临时大学聘请他的弟弟到外语系任教,终于在他弟弟的带领之下,一家人带着心惊肉跳的心情,从长沙几经辗转到贵阳,然后抵达昆明。那个暑假,临时大学的文学院也迁回了昆明,一家人终于团聚,在小西门内武成路福寿巷3号住下,开始了平静而拮据的生活。
过了一个月后,就在9月28日下午,昆明遭遇日军轰炸,闻一多被炮弹残片擦伤了脑袋,幸好没有大碍,仅在医院缝了几针就回家休养。可是,他并未停止研究工作,对《尚书》、《左传》、《论语》、《吕氏春秋》、《山海经》、《史记》中的古字句进行了考解和训诂,还做了一段时间的戏剧工作,在这些方面各自都取得了成果。
抗战之初,昆明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虽然有,却做得不理想,声势不大。联大的师生到昆明后,一些热心戏剧的师生就筹划话剧,借此进一步推动抗战宣传工作。第一部剧是外文系教授陈荃改编的《祖国》,邀请到昆明的著名演员凤子担任主演,请闻一多负责舞台设计。《祖国》首演大获成功,给全体演职员极大的鼓励,接着他们又筹划了规模更大的演出,排练曹禺的名剧《原野》,而且还请到了曹禺担任导演,还未演出就获得全城关注,一经演出就轰动全城,大受欢迎,原定演出9天,应观众要求又加了5天。朱自清在回忆中这样说:“这两个戏先后在新滇大戏院演出,每晚满座,看这两个戏差不多成了昆明社会的时尚,不去看好像短了些什么似的。这两个戏的演出确实是昆明一件大事,怕也是中国话剧界的一件大事。”
此外,闻一多还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战宣传工作,对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由于宣传对象是农民居多,他提出宣传内容不要以文字为主,改成音乐、绘画、戏剧的形式,要把“胜任的人才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1939年的暑假,闻一多获得清华的同意,补休一年的假期。为了避免飞机轰炸和减少家庭开支,他决定全家搬到滇池南端的晋宁县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好好地进行研究工作。这一年,他给自己制定了新的研究方法,用清代学者的考据办法,结合敦煌残卷、殷墟卜辞、商周铜器等有关资料,对先秦两汉时古书中一些字音、字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古代文学的时代背景、思想潮流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解说,完成并发表了《乐府诗笺》、《周易闲话》、《姜嫄履大人迹考》、《易林琼脂》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述与论文。
随着战争加剧,闻一多一家不停地搬家。到1940年9月搬到陈家营时,生活已十分艰难,基本上靠举债、变卖衣物来维持,并且还有同事一家人来避难,住房简陋而紧张,他们只好选择搬走。好友吴晗在回忆中如此描述闻一多这段生活的窘态:“他住在乡下司家营时,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用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口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
闻一多全家在司家营煎熬了三年多,等他们搬到文科所时,已耗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就连他做研究用的重要工具书都卖掉了,他在给兄弟的信中感叹,“书籍衣物变卖殆尽”,仍“时在断炊中度日”。
在饥寒困苦的生活折磨下,多年来深居书斋、埋头于古书的闻一多开始关注政治,变得要讲话,要闹,对社会现象表现出不满,而且不满情绪越来越重,这时他的文艺观也发生了质变。那些唯美的文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政治色彩颇强的意识形态分析。他自觉地将文学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公开宣布“新文学是要和政治打通的”。而且,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学会了以历史来影射和论证现实,写出题为《关于儒?道?土匪》等这类文章来。而且闻一多还深深忏悔自己身上的奴性,发誓要“向人民学习”,坚信“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才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他在杂文《愈战愈烈》中说:“抗战是大家的抗战,国家是大家的国家,谁有权利来禁止我发问!”并宣布:“从今以后,我不打算有清闲日子了!”他就如吴晗在《拍案而起的闻一多》讲的那样:“一多的拍案而起,有两教员,一个正面教员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反面教员是国民党反动派,就时间说,反面教员在前,正面教员在后。”
1943年夏天,联大的英国籍教授罗伯特?白英约闻一多与他合作编辑一本《中国新诗选》。在编辑的过程中,闻一多对田间的作品非常赏识,将他的诗称赞为“鼓的声音”。后来,他特地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进行评论。这期间,闻一多的思想转变得厉害,他开始关注关于共产党思想的书籍,读相关的报纸,他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说:“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经过10余年故纸堆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1944年5月,闻一多接受了昆华中学让其兼任国文老师的聘请,全家搬进了昆华中学提供的宿舍里。在那所中学前后住了7个月,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著作。在联大历史学会举行的“五四”25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一位教授强调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过问国家大事,不免幼稚,是国家的不幸,闻一多反常地站起来辩驳:“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大事。”讲到学生闹事,他说:“我们就是要闹……五四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的,一二?九也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的,现在我们还要闹!”
从此,不管是校园里的活动还是昆明街头的群众性集会,都会有闻一多的声音,他那热情奔放的话语往往获得台下阵阵掌声。闻一多甚至在国民党第五军召开的时事座谈会上,当着众多军长和教授的面,公然发言:“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1944年初秋,吴晗突然登门拜访闻一多,他给闻一多带来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内容大致为: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吴晗此次拜访就是来介绍闻一多加入民主同盟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