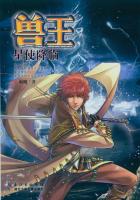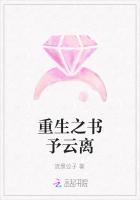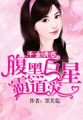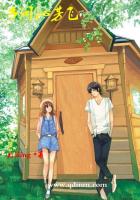一个人的素质,往往表现在对陌生人的态度。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好是自然的,也是应该的,问题是你对陌生人如何。苏东坡有一颗大慈大悲之心,表现在他对陌生人特别地关心。
在黄州期间,苏东坡的生活自然是比较艰难的,属于变相劳改,不过好在还有一点行动的自由,也可以和各种人来往,虽说是犯官,但多少还是官。
有一天傍晚,外面刮起大风,大雪纷飞,天渐渐暗了下来,苏东坡独在驿所取酒解寒,突然从外面闯进来一个人,头上的竹笠已经积雪盈寸,看不清脸。他早已浑身僵硬,进了门就向苏东坡要吃的,说是饿坏了。苏东坡二话没说,就叫人赶快备饭备酒,同时让这个人擦洗干净,换上他的干净衣服。开饭时,苏东坡就拿出自己藏着的好酒,与这个陌生人对饮起来。这个陌生汉子也许实在累了,一吃完就呼呼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陌生人急着赶路,不打声招呼就走了。苏东坡甚至还来不及问他的名字。
苏东坡就是这样对待陌生人的。
从黄州北归时,发生了一件令苏东坡悲伤的事,他与朝云生的孩子经不起路途的辛劳,生病死了,只有十个月大。苏东坡痛苦万分,心灰意冷,对仕途更加没兴趣。他向朝廷打了报告,要求在常州安居,朝廷批准了。
于是他托了好朋友邵明瞻在常州买房子,准备将来在那里养老。邵明瞻帮苏东坡物色了一个很好的宅基,有后花园,有前庭。苏东坡很高兴,一日傍晚他与邵明瞻出去散步,突然听到路边一间破屋里有人在哭,苏东坡是个菩萨心肠,听不得别人的哭声,就走上前去看个究竟。
原来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妇人在哭,苏东坡问,为什么哭啊,老妇人说: 我儿子没出息,赌钱输了,把我们家祖传的老屋也卖了。苏东坡问: 你们家的老屋在哪儿?这一问可问出了大事: 原来那就是苏东坡买下的房子。他看老妇人哭得可怜,便让她把儿子叫来。先是训了他一顿,接着当面把买房屋契约烧了。也不要他们还钱。还正告老人的儿子,要他发誓: 从今以后,再不赌钱,再不让老母亲流离失所。
关于这件事,听起来好像是故事传说,但它确确实实不是道听途说,在当时就有记载。
一个人对自己家里的人好、对自己的亲人好、对朋友好,这是完全应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比如父母生你养你,辛苦了一辈子,反过来你对他好,孝敬,这是很自然的事,这是做人的底线。对朋友也如此,既然是朋友,就有感情的往来,别人对你好,你也应该对别人好,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难就难在也对陌生人要好,看起来陌生人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你要知道,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需要的东西都是陌生人为你提供的,离开了陌生人,你几乎寸步难行。你住在家里,房子是谁盖的?粮食是谁种的?你每天出门,马路是谁打扫的?因此,你一切的一切,都是陌生人在为你服务。这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素质高低的标尺。
苏东坡在黄州,平时十分清闲,他完全可以不管事。但是,凡是他看到的,他都要管。
黄州这地方,有一种坏风俗,就是生了二男一女后就把再生的孩子全部浸在冷水里溺死。这当然是因为穷。苏东坡实在不忍,打报告给当地政府,请求解决这个问题,要用法律形式规定溺婴是犯罪的,并且广为宣传。他一面还自己组织了一个慈善基金会。要有钱人出钱、捐钱,并让一个懂会计的和尚来管账目。给生孩子的家庭以补助,他自己当时也很困难,但也每年拿出一笔钱,带头捐助。如果谁肯领养,就给以奖励补贴。
他写信给朋友说,只要在生出来时不把孩子害死,几个月后,父母就会爱上孩子,有了感情,这时,再叫他去害也不会干了。
多年后,苏东坡有一次经过这一带,发现路边跪了一群一群的小孩、青年,有男有女,向他磕头。苏东坡问是怎么回事,路上人告诉他,这些人都是你当年救下来的,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如果没有苏东坡,你们早就在马桶里淹死了!
以后,他无论到哪里,都会做这个工作,到徐州,看到有很多没爹没娘的孩子,就组织大家领养。凡领养的就给以补助。到海南也如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东坡是一个慈善家。
苏东坡的爱陌生人,不但是对穷人、对好人,就是对囚犯也是大慈大悲的。他36岁那年在杭州做通判,到了除夕这一天,按照衙门的旧例,要把牢里的犯人一个一个提出来点名。那年除夕,别人都回家过年了,苏轼却在衙门值班,眼看那些铁索锒铛的犯人一个个过堂点名,一直忙到天黑还没点完,不能回家。他心里想,我和他们有什么两样,大家都是可怜的人,他们为了生活触犯了法律,我不过也是为吃饭才贪恋这份工资,做这样违心的事。他的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冲动。很想学学古人把这些囚犯暂时释放,让他们各自回家过个团圆年。可是他终于没有这个胆量,为此,他感到深深的惭愧,便在监狱的墙上题了一首诗,题目就叫《除值直都厅》。
他还提出要给囚犯治病,宋朝法律有一个规定,不能随便殴打犯人,特别是不能把犯人打死,但是如果是病死,也就不管了。因此很多犯人因为有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去。苏东坡对此非常不满,他上书要求给犯人治病,他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便首先这样做了。
当然,他的这种悲悯情怀是因为他生性善良,但也不是凭空来的,而是有源头的。他从小读儒家的书,懂得民为贵的道理,他读佛经,赞成“众生平等”。他本质上是一个有平等意识、有博爱情怀的人。
他十分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和为人,有一次他读陶渊明给他儿子的信,里面有这样几句话,令他十分感动。
陶渊明家里有个仆人,陶的儿子对他态度不好,很生硬,陶渊明说: 此亦人子也,当善待之。意思是这也是“人”的孩子,你要好好地待他。
把穷人当人,把坏人当人,把敌人当人。这就是苏东坡的博爱情怀。特别是表现在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
苏东坡对穷苦人关怀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我们再讲一件关心农民子女的事。王安石的青苗法实行以后,在青黄不接时,借钱给农民,农民还不出,只好到城里来打工。孩子没人带,也跟着到城里。城里人就设法赚他们的钱,苏东坡很为他们忧虑,写了这样一首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意思说,农民到城里什么也没得到,只是让孩子学会了一口城里话。这首诗后来成了苏东坡反对朝廷政令的罪状之一。
总之,这种对别人理解、关怀、尊重的思想深深地刻在苏东坡的心里,并处处表现在行动中。所以苏东坡到任何地方,都是平等待人,什么地方都有朋友,在什么地方都生活得开开心心。一个人为别人做了好事,心情总是愉快的。
苏东坡说,自己为别人做好事,并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能利人济物,他就高兴。他说自己有两个嗜好,一是合药,一是酿酒。他的合药,不是给自己治病,而是为别人治病,他看到有人生病,就想怎么给他治好,一旦治好了,他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他喜欢酿酒,自己酒量很小,酿酒主要是招待客人,看到别人喝得醉醺醺的,他就高兴,仿佛是自己喝醉了。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书东皋子传后》,其中有这样的话: 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余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这“劳己以为人”说得如此轻松,仿佛为别人活着成了他做人的底线。
因此,每到一地,不要几天,他的身边就围拢了一批朋友。有朋友,就有人想着,生活就丰富多彩,就活得滋润。没有朋友即使钱再多,生活也是枯燥无味,精神空虚的。而要有朋友,就要对人真心,就要善待人,苏东坡曾对他弟弟说: 在我眼里,上至玉皇大帝,下至田院乞儿都是朋友;在我眼里,世界上没有一个不是好人。幸福的人眼里的世界都是好人,不幸福的人眼里到处都是坏人,都是与他作对的人。这也许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一份精神遗产吧。
因为当时连年灾荒,路边经常有倒毙的人,还常有枯骨。苏轼每到一地,就收集枯骨,把他们一起掩埋,并为他们写铭文以祈祷。最有名的是《惠州祭枯骨文》: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伤残,蝼蚁穿穴,但为丛冢,罕致全躯。幸杂居而靡争,义同兄弟;或解脱而无恋,超生人天。这段话大意是: 你们这些可怜的人,尸骨暴露在荒郊野外,不知道有多少年。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不是士兵就是平民百姓。朝廷本来就有法令,有掩埋尸骨的文书,官方应该切实实行,不应有吝惜财物的念头。因此,我们建造了这座新居,好让你们永远安居于此。所遗憾的是,因为猪狗的伤残,蝼蚁的破坏,今天我们只能为你建造这个集体的坟墓,而且难以找到你们完整的尸骨。希望你们和睦相处,不要因杂处而相争,你们互相之间要像兄弟那样。我相信你们最终能够得到超脱,或重新做人,或升入天上。
这篇铭文写于惠州,当时他自己在流放中,可还是如此关心百姓。虽然相隔九百多年,当我们读着苏东坡的碑文时,都不能不被他那大慈大悲的心地深深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