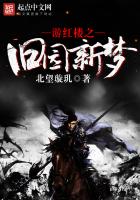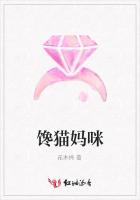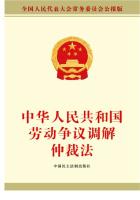群众的色眼也是雪亮的,美女果是征收局局长唐豫桐之妻、田征葵的千金。堂堂局长夫人被人公开骚扰,而且居然围堵不去,看热闹,说“咸”话。唐豫桐愤怒之下,命令保安驱散人群,但无效。他一发急,下令开枪警告,但在保路运动几个月的荡涤下,官府的地位早已十分低下,人群根本就不在乎,依然哄闹着并不散去。如此,开枪警告数番无效,唐豫桐居然下令平射。
枪声过后,人群中倒下了一批起哄者。这下激起了众怒,正在兴头上的民众,没想到近来很窝囊的官府居然还敢动硬的,群情汹汹,立时就把征收局给砸了。混乱之中,护花失败的唐局长躲进了隔壁的县署,逃过一劫,但他那美女夫人却宣告失踪,3天后才被找回。这3天中,田美女究竟发生了什么,史无记载,但其父田征葵本是政府中主张强势的官员之一,从此添加了“家仇”,更是恨透了保路运动,成为日后镇压保路运动的主力。
彭县的突发事件,半夜传到了成都,赵尔丰立即召见川路公司的高层彭芬等人,商议对策。田征葵“愤恨不可遏”,要求当场逮捕川路公司这些煽风点火的领导人,但彭芬辩解说,县署与征收局紧邻,闹事者只砸了征收局,而没有砸县署,且所有公款都安然,其中必然另有隐情,非派人实地调查后不能下论断。赵尔丰听了,觉得有理,就让彭芬等人离去。各个阵营的回忆录都认为,这一事件令田征葵成为保路运动“最凶恶的敌人”。辛亥革命后,倒霉的田征葵带着女儿、女婿试图逃回湖南老家,半道上在九层岩江面上,被重庆的“蜀军政府”抓获,未经审讯就直接枪杀在督军大院内,“传首城中”,莫名其妙地成了时代的牺牲品。美女被骚扰乃至被掳3天的幕后真相,成了一个永远的迷。
2、机关报 机关枪
大清国林立的报刊,无一不是某一机构或组织的喉舌,是与枪杆子同样重要的笔杆子,是投枪与匕首般的政争武器。在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只能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与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
人们已经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就在枪声响彻四川总督府之前的数小时。当天上午出街的川路公司机关报《西顾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政府“倒行逆施,任一般人之奔走号呼而卒不之恤,是亦实行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故智也”,提出“罢市罢课抗租税等手续,不过对横暴政府之一种方法耳,实则吾川人今日所当共表决心者,莫外乎死之一道”。这篇社论公开宣称:“与其独死,毋宁同死,与其死于异日,毋宁死于今日。”号召读者与政府同归于尽。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报纸的运作规律,当日的报纸最晚已在前一晚完成了所有的编辑和印刷作业。一切都太蹊跷了:
9月5日,突然出现带着颠覆倾向的《商榷书》;
9月6日,《西顾报》号召“同归于尽”的社论开始进入印刷程序;
9月7日,在官方逮捕保路运动首领们的同时,民众冲击总督府,警卫开枪;
而9月8日,就有近10万武装黑帮,打着“同志军”的大旗,将成都城团团包围,粮食不让进,粪便不让出……
难道,这都是巧合吗?绝难相信,这幕后没有一个严密的计划,在推动着局势一步步发展到刀兵相向的地步。而官方的逮捕行动,正好为这个可能的计划补上了最为完美的一根链条。
投枪与匕首
赵尔丰下令开枪后,第一道指令就是立即查封《西顾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保路派的宣传机器。
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缴除敌人的“武装”是很正常的行为,而除了那些租界内洋人办的报纸外,大清国林立的报刊,无一不是某一机构或组织的喉舌,是与枪杆子同样重要的笔杆子,是投枪与匕首般的政争武器,从来就没出现过真正的独立新闻媒体——尽管也有人高喊新闻自由和独立,真实与真相从来就不是大清任何媒体的使命,不择手段的政治攻击、舆论引导(无论“正导”还是“误导”)才是其第一任务,相互之间的区别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距离、“胜者王侯”与“败者贼寇”的分野。
大清帝国的第一波办报高潮是在戊戌变法期间,第二波则是在辛丑变法(1901年),尤其在清政府明确宣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开禁的同时,清政府试图以法制化的方式加强管理。1906年7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由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制定颁行。1908年3月,《大清报律》经宪政编查馆审核议复后,正式公布。该法律几乎完全套用了日本的报律,限制性的内容也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主要涉及司法独立(禁止旁听或未经宣判的案件不得报道)、军事机密、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其中,最有大清特色的是将大清国的社会制度作为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严禁报刊刊登“淆乱政体之语”。1911年,《大清报律》做了修订,颁布了《钦定报律》,减轻了处罚力度,但丝毫没有放松对“淆乱政体”等言论的处罚。
国家机器对于新闻媒体进行限制和管理,也是当时的国际惯例,而对于大清国而言,更为符合朝野上下对新闻媒体的定位。在时人眼中,媒体的作用首先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说得很透彻:“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之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盛世危言?日报》)。同时,媒体也是救亡图存、打击敌对势力的武器,郑观应说:“东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
在当时的政府、立宪派及革命派之间,媒体工具论成为极少数他们能实现共享的认识。康梁自戊戌政变流亡后,便将报刊作为武器,发动了针对慈禧、荣禄等的宣传战,梁启超晚年曾明确承认,当时的不少文字,毫无事实可言,不可采信。革命派的报章,更是将辱骂与恐吓当成了战斗,对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尸山血海的推崇,不绝于书。
在这些不同的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只能是政治斗争所需要的“机关报”,与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各方的手法也如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清政府全力动用公权力,胡萝卜加大棒,确保喉舌发出该发的声音,不允许随意打嗝、喷嚏或叹息,即使弄得千报一面,“摭饰浮词,雷同附合”(宣布停办《时务官报》的上谕);另一方面,反对者在“机关报”上猛打“机关枪”,“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双方竞相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对方打扮成魔鬼,“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郑观应语)成为笔杆子热战的主流,至于民众的知情权、参政权,无非是广告词而已。而高唱新闻自由动听旋律的在野者,一旦自己登堂入室,首先做的便是严禁他人克隆,转而认真总结旧政权在控制与垄断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鸿章在1896年访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陈:“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在大清国,党同伐异成为各种政治派系共享的主流思想,诚信和公理则成为全社会的稀缺资源,民意便成为群雄追逐的“鹿”,媒体就只好成为投枪与匕首。
信息战
那份在惨案前夕号召民众与政府“同归于尽”的《西顾报》,诞生于1911年7月26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的一个月后。
在此之前,一份名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的日报已经创刊,作为“同志会”的机关报,而这份《西顾报》则作为川路公司的机关报。办报是一件“烧钱”的买卖,这对这两份“机关报”来说并不是问题,经营混乱、建设迟缓的川路公司在这方面十分大方,拨出了巨额专项经费,当然,并没有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尽管他们总是指责政府的决策没有征求股东们的意见。
《西顾报》从创刊到9月7日被查封,历时44天。这44天中,每日出一大张,除第四版刊登广告外,其余三版大部分都是有关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内容分为社说、京外纪事、本省纪事、要件、时评、文苑等,还间插漫画。《西顾报》的发行量日均8000余份,罢市罢课后增至14000余份,而8月5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时,次日的报纸印量超过15000份,仍供不应求。在一个波云诡谲、变化频繁的非常年代,信息的饥渴是一种通病,即使提供的是“鸩酒”,人们也照样饮鸩止渴。而恰恰在信息的供给方面,政府的庞大身躯难以灵活应对,“舆论阵地”成为反对者们占压倒优势的主场。
川路公司从来就不屑于掩饰自己与同志会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关系,在同志会成立的首日,经费拮据的川路公司拨出了4万两白银作为这个“独立的群众社团”的活动经费,这在当时绝非一笔小数目。同志会迅速用这笔经费中的一部分,创办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后来考虑到“政治法律之观念不能尽人而具。至于条约解释,更不能望于众人;若非白话报浅明剖晰,不能尽人皆知,若无杂志日报,亦不能收罗宏富,印证明确”。因此,“邓慕鲁、朱云石之杂志,池汝谦之《西顾报》,江叙伦之白话报,乃应时而起焉”。仅在6、7两个月之内,保路同志会就创办了《保路同志会报告》、《白话报》、《蜀风杂志》、《启智画报》和《西顾报》5份报刊,“干枝相扶,严整成阵”,保路同志会成立仅半个月,“文犊部则发出印刷刊物十六万有余件”,“机关报”的效率与机关枪相仿,进行大面积的信息饱和轰炸。
对于《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主办者、保路同志会文牍部宣称,将以“尽笔墨之能,从种种方面,以期贯彻本会破约保路之目的”,其主编就是因发表《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而著名的邓孝可。这份“机关报”创办于6月26日,同志会成立的第九天,仅创刊号就印了三千张,随后印刷量不断攀升,到7月中旬已增至15000份,最多时达五六万份。从创刊到7月22日,日出一期,但随后因纸张匮乏,改成双日出版,直到9月7日被查封。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分纪事、著录、报告、诗歌、附件等专栏,每张四小版,约数千字。它在为“破约保路”做宣传时,也从来没有忘记为自己摆功,它曾经报道说四川妇孺们“每日望本报几如望岁,及得报展读,涕泪横流,且阅且哭……每读令人欲哭耳”(第13号),甚至连保宁(属阆中县)这样“距省七百余里”的偏远地方,“该地绅商闻盛奴夺权卖路事,愤恨如烧,立欲知其详情。特专捷足,兼程星驰三日有半,抵成都购买保路同志会出版、报告各件”(第13号)。
《西顾报》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自己报道说,有老者读《西顾报》,“于街口演讲……闻者为之愤恨……闻者又为之凄怆而流涕。报纸感人,如此之甚……”
赵尔丰同时查封的,还有份真正的“机关报”《蜀报》,四川咨议局的机关报。《蜀报》创刊于1910年8月19日,由咨议局议长、日本回来的蒲殿俊兼任社长,朱山任总编辑,吴虞、叶治钧、邓孝可等任主笔,集中了当时四川的一批笔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