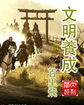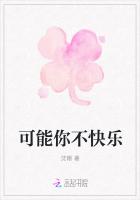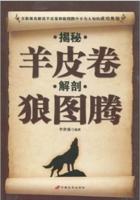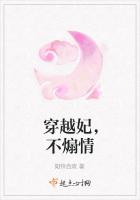这位朱山总编辑,就是在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猛拍桌子表决心,不小心拍碎了茶碗,伤了手,却在自己的报纸上描写为“写血书”的那位。他主动要求到川东负责宣传,到了重庆却投奔了端方,做了幕僚,令郭沫若大为怀疑这些绅士们的动机与真诚。他的妻子李朱也是风云人物,老公成了端方的幕僚后,这位“花木兰”也同样神奇地从运动中消失。
《蜀报》是继《四川官报》之后,四川的第二家报纸,每期50双折页,半月刊。四川虽穷,但咨议局是个权力很大的机关,在这些方面很舍得花钱,《蜀报》纯用白皮纸,印刷精美,定价高达4元8角,绝非普通读者所能问津的,多数还是机构消费者公款购买。报纸当然是亏损的,但堂堂立法机构为自己的喉舌拨点专款,还是很轻松就能搞定。
《蜀报》实际上是第一份党派控制下的机关报,当然,这个“党”是很松散的所谓“立宪派”,或者,干脆就是掌握咨议局实权的少数人及围绕他们的一群人。“党”的喉舌,自然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只为“党”说话。《蜀报》的言论因此极其大胆出格,对于任何自己不满的人和事,帽子扣得很大,不以危言,何能耸听呢?
“小说日报”
在保路运动中,《蜀报》吹响的第一声冲锋号就是邓孝可的《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在只掌握极其微量信息的前提下,邓就大胆假设、不需求证,将盛宣怀定了“卖国”的罪名,这成为保路运动乃至日后各种群众运动中动辄上纲上线、党同伐异的滥觞。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慨叹:“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纭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这些“投枪”与“匕首”,被报纸、同志会的“演讲员”及罢课回乡播撒“种子”的学生们,带到四川的各个角落,几乎完全、彻底、干净地占领了舆论阵地。在这种宣传战中,真相与信息公正都已经退居到第二位,多占地盘、不择手段地压倒对方才是最关键的。至于新闻的客观、公正、真实,就绝对不是作为喉舌所需要去关注的。细细查看这些报纸,除了转载的公文、电报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新闻”,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艺术”再加工,而且套话、假话、空话连篇,简直成了“小说日报”或“废话日报”。
为了吸引民众,危言耸听之外,这些媒体还都有另一个共同特点:文字浅显。如“同志会,何由成,同胞听我说原因。有一个,卖路臣,他本江苏武进人。盛国贼,现是个邮传大臣。上蔽君,下压民,借债送路太专横。借外债,甚吓人……”就是民间的打油诗,琅琅上口。
国家大事也都被简化和形象化。在各期各版的“眉边”和“脚边”,反复刊登一些口号,比如:“路是人修,钱由人管,路是白送,外带认息”;“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夺路夺款,又不修路”;“果欲保国,必先保路,保路保国,即是爱君”,真假不论,但明白易懂、效果很好。再比如:
国家把法律来散布,管得了天子和百官,管得了人民都不敢犯,立宪国精神在此间。凡事都照法律办,包管事事得平安……京城设一个资政院,各省的咨议局都设全。设这个局院为哪件,为的要把法律编,为的年年出议案,议国家的事要靠议员。既是铁路收回国办,外债又借了金镑千万元。借债收路事非浅,就该交局院议为那端。看来他(盛宣怀)是大粉脸,忘了法来欺了天。国家听他胡乱干,看看法律被摧残,看看要成假立宪,看看铁路要卖完,铁路卖了真危险,亡国就在眼面前。
在煽动仇恨和暴力方面,这些报刊的宣传手法是能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的。《西顾报》就毫不掩饰地鼓动说:“练民团制造好军火,习武艺一齐供达摩……我们又有本事又有联络,不怕官府那还怕差哥。倘有那不消官吏来捕捉,鸣锣发号我们蜂一窝。一家有事百家来聚合,他的手快我人多。钢刀砍不完七千万人头脑壳,那怕尸骨堆山血流河。有死心横竖都战得过,战胜了我们再打收兵锣。”
当然,也有文化含量稍高的作品,比如将一些经典改编为山寨版:
风萧萧兮锦水寒,铁路一去不复还,
路权失兮国土残,呜呼一歌兮蜀道难。
风萧萧兮锦水寒,合同瓜行兮债如山,
债如山兮民力单,呜呼二歌兮政策蛮。
官方自然是不能坐视宣传舆论阵地被夺的。在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力支持下,官报书局总办余大鸿匿名印行了一种日报《正俗新白话报》,为官方进行宣传,并反驳保路派的攻击。但是,中国的显规则一般认定,台上的都是坏蛋,台下的都是好蛋,虽然大家都想着上台,并且上台之后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依然是好蛋。当然,在野者为了上台,不择手段,而上了台面后,做事情就多了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必须做淑女状。尽管各方的报纸都带着八股腔,“官八股”和“野八股”如一丘之貉,但人们一般是更倾向于“野八股”的笼络与宣传。
单就发行量而言,与动辄上万的对手报刊相比,官报十分少得可怜、僵硬得可怜,只能通过政府渠道由下级认购,几乎无人愿意主动购买,这也造成官方几乎缺乏信息发布的有效渠道,处处被动,等于拿着一挺生锈无法使用的机关枪坐以待毙……
3九月围城
成都被包围了,而且就在一夜之间。电线杆已被砍倒,通讯中断,米、炭被人拦截,无法入城,粮食等价格飞涨,而郊外农家也被禁止进城清运粪便,盛夏中的成都城立即成了一座臭城。
“省城四面,团兵已集城下”,这些神奇的“快速反应部队”,“半由哥老督促,手执刀矛,身穿号褂,分执红旗牛角叉……”连军服(“号卦”)都准备好了,并且扯出了“同志军”的旗号,把“同志们”由“会”变“军”,速度之快实在惊人。
按照常理推测,如真是官逼民反,也不可能在“成都惨案”后不到一日,就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动员和调动。莫非,这些反叛者早就“预测”了即将发生惨案,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甚至,惨案的进展也完全可能在他们的导演策划之中?
“离间官民”
成都惨案之后,政府指责有人在幕后推动,造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流血冲突,以便浑水摸鱼。从武装叛乱的速度来看,这绝非虚言。
在各种利益集团的烧烤下,四川早已是一个滚烫的油锅,就等着将政府逼到绝路上去,政府一旦采取强硬措施,那就是一瓢清水倒入油锅,激起万千鼎沸。成都一声枪声,仿佛一个信号,全川立即大乱,各种武装团体迅速出现,都打着保路保民、营救蒲(蒲殿俊)罗(罗纶)名义,戕官毁衙:
川西“同志军”统领孙泽沛发布告示:“本军召集同志,原为争路保民,不日振队入省,请释罗、蒲先生。”
同盟会员熊克武坦陈:“西南附省数十州县,更迭起民团,赴省营救,防军与战,颇杀伤。革命党人遂勾结同志军,呼号而起矣。”
新津黑道老大、“新西公”龙头大爷、新津保路同志会会长侯宝斋率众围攻成都,“集者人数之多,号称十万以上”,“营屯四接,旌旗相望,大有震撼全蜀之势”。
华阳(今双流)黑道老大、“文明公”舵把子、民团“安吉团”团总秦载赓,率部“抵成都东门,为清军拒,不得入,乃遣人四路号召,羽檄交驰,四方应召者万余人”,“连营四十余里”。
广安“大汉蜀北军政府”成立后扩充部队,“不到三天的时间,便招募了三千人”,真是“兴师之顺,千古无双”。西昌县民团团长张国正率领“团众”,直入县署,砍下了县太爷的脑袋……
动员民众、因势利导、火上浇油、借刀杀人,恰恰是中国历史上“革命者”的常用手段。从保路运动一开始,同盟会就认识到机会来了,渗透到保路运动中去,“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
但是,在同盟会看来,合法斗争成本高、收益低,他们更希望通过性价比更好的秘密活动,鼓动地方黑帮或立宪派冲锋在前,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实力弱小的革命党就可以乱中取胜。同盟会认为“争路者日与清廷言法律,辨是非,清廷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于是,他们“积极部署革命,但未作公开行动”。在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同志会日益张大,演说时恒集万众,哗动一时,而不见同盟会党人于会场中有言论”。
同盟会的精力放在了幕后操纵,激化矛盾上。那份《川人自保商榷书》,就是同盟会的革命创作,逼迫赵尔丰下令抓捕保路运动的头领们,从同情保路运动的温和派成为镇压者。而与赵尔丰的抓捕几乎同时,数百名民众“巧合”地得悉消息,集体冲击总督府,逼退四道警戒线,最后在大堂前酿发血案。被逮捕的保路领袖们,指天划誓地说那份《商榷书》与自己毫无关系,而冲击总督的行为更是蹊跷。烽烟遍省的黑帮暴动,却都整齐地打出了“同志军”的旗号,让保路派们去顶缸,这毫无疑问,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借力打力的革命策划。
早在5月份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就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确定自己的定位、立场和方略。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通过“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同时,到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这次会议之后,同盟会向更多的黑道成员敞开了大门。
同盟会要推动的是两股力量,一是以立宪派为主的保路者们,他们在明处,打着冠冕堂皇的合法斗争旗号;二是黑帮会党,他们在暗处,磨刀霍霍。
保路派在同盟会眼中,“蒲(殿俊)、罗(纶)恐未足与谋”,因此,每遇会场中立宪派提出软弱无力主张时,同盟会的人就大肆反驳,鼓动群众进行反对,“极言国有弊害,政府恶劣”,使人人知清廷之不可恃,非革命不可,以高调、极左的言论博得喝彩。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情绪的激化,民众的欲望被激发出来,这种极端政治很容易与民众情绪形成共鸣,“每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群众欢迎;若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群众极为不满”,冷静、客观、公正的考量早已成了“卖国”的代名词,连那些为了川民争取最好最现实解决方案的川籍京官们,也纷纷被激进的老乡开除“乡籍”,把保路运动弄成了一种带着恐怖气息的、一言堂的零和游戏。
同盟会当然更希望着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吾人岂甘坐以待毙?必当死中以求其不死。何以得不死,则革命之策也。吾果革命,则川汉铁路吾自集股,吾自建筑。何畏他人制我死命,何用他人越俎代庖”。只有更多的流血,才能将“革命”的炉火烧得通红。
成都会议后,同盟会在随后召开的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与“会党”加强联合,伺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所谓的新津会议,其实就是同盟会主持的四川黑道大聚会。川东南哥老会四方九成团体首领聚集新津,“承谋举义”,商定“各回本属、准备相机应召,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则先据川东南,扼富庶之区,再窥进取”。
8月4日的资州罗泉井会议,更是被后来的主流史家当作是四川革命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伟大转折点,是“同盟会把保路运动转变为反清民主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具体步骤”。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据说有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等同盟会会员及秦载赓、侯保斋、张达三、罗子舟、胡重义、侯国治、孙泽沛、胡朗和等川西南各路“大爷”。
会议决定,组织同志军,利用保路名义,开展武装暴动,并详细规划了粮饷、军纪、枪弹、情报等细节,划分了势力范围:秦载赓、侯宝裔主持川东南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主持川西北起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