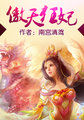端方最为主要的履历,是1905~1906年与戴鸿慈、载泽等带团出访欧美十国,历时8个月,考察政治。回国之后,端方等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编纂的《欧美政治要义》,成为中国立宪运动的奠基之作。早在出国考察前,端方就是少数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旗籍官员。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立宪”日本战胜“专制”俄国后,在中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内,同时爆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据说,端方在拜见慈禧时,太后说:“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端方立即回答道:“还有一事,尚未立宪。”慈禧问:“立宪又能如何?”端方说:“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令慈禧动容沉思良久。
端方深刻地指出,立宪与专制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不受尊重,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他指出:“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在共和的新装下,“一人一家”或许已不能将政权视为私产,但纵观民国史,“一种人”的小团体却在自我神化之后,堂皇地提出“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党同伐异,成王败寇,赢者通吃。
1909年6月28日,端方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甚至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美国各大报纷纷报道,《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题目就是“塔夫脱(总统)观察中国,从端方的任命看到伟大的商贸开放”,认为端方出任直隶总督,将极大推动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但当国内外都对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而给予热望时,端方却在半年内因严重违纪而被革职。
1909年11月20日,李鸿章之孙、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端方,理由是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大不敬”,证据有三:葬礼中沿途派人照相;迁奠礼上焚化冠服时,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其实是为了照明)。根据曹汝霖(“五四运动”时著名的所谓“卖国贼”)的回忆,李国杰参加典礼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冒广生说:“此属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国杰经他一激,即说:“为何不敢?”遂由冒广生草奏,由李国杰参劾。
奏折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而三天后,居然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
据曹汝霖记载,“伟侯(李国杰)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名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摹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端方)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沣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其实,作为大清“董事长”的载沣与有可能作为“总经理”的袁世凯,本无根本冲突,与袁矛盾很深的,其实是铁良等另一些地位相仿的满洲亲贵。载泽当国,年仅26岁,凭借的只是慈禧太后的政治遗嘱,因此,他只能也必须推行两个“凡是”:“凡是老太后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老太后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沣就很容易引火烧身。而野史表明,真正动怒的其实是当时的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清代野记》)。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著毋庸置议”。
蜀道之难
端方被革职后,过了两年的寂寞时光,这对一个年富力强、又有丰富从政经验、并对国际大势知之甚深的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
铁路国有成为他政治翻身的机会,自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后,端方就一头扎进了工作。然而,正如盛宣怀以及此后的岑春煊一样,这三个人都是久困牢笼的猛虎,放出来后,急于建功,一味燥进。盛宣怀、端方先受理路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这种雷霆手段,本是处理此类乱麻般纠葛的不二法门,广东、湖南、湖北迅速见效,却奈何四川地方官员存了私心,阳奉阴违,导致了湿手抓面团,成了僵局。而岑春煊一边倒支持商办的主张,也是另一种燥进,只是方向与盛宣怀、端方相反。
原本,端方与盛宣怀一样,都是主张强势贯彻中央精神的,但武昌暴动后,中央底气丧失,而新生的资政院又还在宪政“实习期”,把宪政这辆进口豪华车开得七倒八歪,居然压服了中央,拿盛宣怀做了替罪羊,还要求处以极刑。端方也是被攻击的靶子,但他毕竟在外手握雄兵,自然无恙。但端方很见机,随风调头,来了个“左满舵”,从坚决要求镇压闹事者,变成了坚决要求释放无辜者,而“川乱缘起”也被他改为“实由官民交哄而成”,并弹劾了赵尔丰等四川官员,中央随即下令将被弹劾者革职拿问。
端方一转舵,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就落了个里外不是人的境地,他随即多次弹劾端方“济乱”、“诡谲反复”。11月2日,赵尔丰上书中央,痛斥端方,说川路纷争还在合法、和平范围内进行时,端方不断来电,要求采取强硬措施,而等到他将蒲殿俊等抓捕后,端方却又变了脸,主张应该赶紧放人,认为首要一放,乱事就能平息。赵尔丰认为,“事理自有是非,法律期无枉纵,若竟不究虚实,旋拿旋释,不徒有伤政体,抑亦无此办法”。他认为,自己之前不拿,“因其无罪而宽之”,随后抓捕,“因其罪著而执之”。
11月5日,被端方弹劾而丢官的周善培,发表了致端方的公开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川路风云的分析,认为川路风波有三个转折点,一是保路同志会成立,正是端方与盛宣怀联合发出“歌电”,并“强迫”王人文公布“歌电”,刺激了民意;二是罢市,其原因也是端方力主保持李稷勋的宜昌总经理职务;三是9月7日赵尔丰下令捕人,原因也是端方弹劾了赵尔丰、王人文等逼迫而致。这篇言辞谦恭、却锋芒毕露的公开信,矛头直指端方才是四川动乱的罪魁。端方收到该信后,批示道“该署司(周善培)罪恶昭著”,认为这是“老奸巨猾”的周善培“嫁祸本大臣,为上欺我皇上,下愚我川民之计”。
11月8日,赵尔丰再度上奏,弹劾端方“诡谲反复,希图见好于川民谬信讹言,罔究事实”,已经安定的人心,被他又搅乱了,而且他罗织罪名,弹劾官员,弄得官员们人人自危,将领们在前线也不敢用力。赵尔丰指责端方,上任后躲在武昌,天天电报逼迫赵尔丰采取强硬手段,而带兵入川后,却又不顾成都当时正是危急,非要绕道重庆,等到武汉、宜昌失守,已无退路,仓皇失措,不顾国家利害,只考虑一己安危,“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赵尔丰甚至断言:“端方到省(成都)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端方大军到了资州后,本可以长驱直入成都,但赵尔丰在半道上陈列重兵,端方狐疑不敢前进。此时,北京失守、朝廷外逃的谣传也传到资州。端方可能的选择是:上策是顺应大势,主导并鼓动四川独立,自己就有了一块巨大的根据地,进退自如;中策是率部退居陕西,伺机勤王;下策则是孤身离军,保全性命。
显然,他选择的是上策,因此派遣了幕僚朱山及刘师培,到成都活动。这刺激了赵尔丰抢先独立。成都独立(11月22日)的消息传到资州,端方发现赵尔丰已着先鞭,遂计划离军回京。这当然是下策,但他的上策已经被赵尔丰截断,而所率部队是湖北人,在这乱世都不愿大队入陕,指挥不灵。此时,资州地方绅士们出面,挽留端方说,此时端方如何率军“反正”,成都唾手可得,众人便可推端方为都督。端方不同意,绅士们又说:“公如虑成都不能容,则即于资州树白帜(指‘大汉国旗’),某等可函至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公幸勿疑。”据“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记载,此时端方长叹一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光绪)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勿为我虑也。”于是,众人“皆太息而散”。
此时,端方如果回京,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一方面想等成都的饷银送到,另一方面还要等一名姓周的“土寇”率众来降,结果等到的却是自己的末路。
亲身经历了四川大动乱的郭沫若,日后感慨说:“岑春煊并没有入夔门一步,而入了夔门的端午桥就没出夔门一步”,端方“如果有岑春煊那样的聪明,率性把胡子剃了,一个人改装逃走或许到到现在都还活着,他的《陶斋吉金录》或许有再续三续出现了。但是他到底没有这样的幽默”。
这哪里还能算得上“幽默”呢?英国《泰晤士报》、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公开表示:“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端方的门人、湖南名士左全孝感慨道:“谓天道有知耶,神奸巨蠹多无恙,而持公理、重民权,首倡宪政如我公者,独罔善其终!”
2、总督之死
年轻的郭沫若日后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赵尔丰被四名强壮的士兵架按着,坐在地上。
1911年12月22日,冬至日的凌晨,阴冷的朔风吹拂着他满头的白发,家人已经在地上为他铺了块大红的毡子。闻讯赶来的人群,挤满了明远楼下的空地,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艰难地维护着秩序。
这位65岁的四川总督,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也不挣扎,盘腿坐在毡子上,怒骂道:“尹娃娃,你装老子的桶子啊!”
被他称为“尹娃娃”的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26岁的尹昌衡,简短地公布了他的“罪状”,然后,向着围观的看客们问:“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赵屠户,该怎么办?”看客们齐声回答:“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