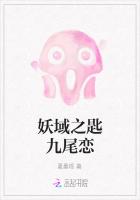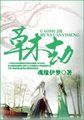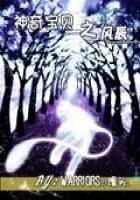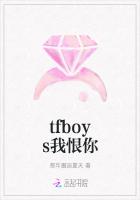尹昌衡的亲信军官陶泽锟,早已站在赵尔丰的身后,此时手起刀落,在看客们的惊叹声中,在照相机的镁光灯闪耀中,赵尔丰人头落地,并被定格在照相机中,他那花白的头发和胡子被鲜血溅得通红、通红……
兵变
一切都要从蒲殿俊的阅兵开始说起。这位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上任没几天,便执意要进行大阅兵,过过当“老大”的瘾。
这位新贵以前只在日本留学期间,短暂地接触过军队,但却同样深知枪杆子对自己的重要性。上任之后,他已经宣布给士兵们发放3个月的“恩饷”,但是,财政却囊中羞涩,一时拿不出钱了。
各种情报显示,军队可能将在阅兵这天哗变,背后有好几股势力在合纵连横,借机端掉这个刚刚诞生的军政府。前司法厅厅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之一周善培,再三劝阻蒲都督万不可阅兵,在这非常时期,只能让城里的军队赶紧退出城外,各回营区,怎么能聚集在一起呢?
正在兴头上的蒲殿俊,哪里肯听。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大阅兵在成都东校场外如期进行。军乐铿锵,刺刀佩剑闪亮,蒲殿俊正沉浸于兴奋之中,忽然,士兵们骚动起来,后边的士兵对空鸣枪,局面登时大乱。“当时如有人挺身而出,立可弹压,因前列新军并未动,后列巡防军亦只有少数异动,稍作处理,即可弥祸无形。”
站在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立即撤离。乱兵从校场上蜂拥而出,冲向藩库。藩库的保安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乱兵砸开藩库,看到了光灿灿的两座银山,这里就是四川全省的财政所在,总共约800万两白银。
士兵们疯狂地冲向银山,纷纷解开绑腿,尽力捆扎。“一人抢三锭五锭,心重的人抢十锭八锭,最贪婪的抢得多,拿布扎成包袱,背上如背两扇磨子,一步一步慢慢走”,黑吃黑,“遇黄雀(“黄雀在后”之意)”,“击毙重抢的不少”(革命党彭光烈回忆)。人人满载之后,便放起一把火来,顿时烈焰冲天。
乱兵随后冲向大清银行及各银号、票号,成都城内的主要商业街及各处豪宅,均不得幸免。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军队变乱后,警察也加入了抢劫队伍,随后是外州府县前来成都庆贺“大汉军政府”成立的人们,再就是成都本地的地痞流氓,“蜂拥而起,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枪声阵阵,火光冲天,已经200多年没有遭遇兵灾的“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亲历此事的少年郭沫若日后回忆,兵变发生时,他正好要到堂姐和大哥家中去,在东大街遇着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老爷模样的人,在他的狐皮袍子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色标记的军裤来,当人们把他的马褂、袍子剥开后,里面还有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原来是一位抢劫的士兵。
刚刚还站在检阅台上过瘾的正副都督蒲殿俊、朱庆澜,在都督府宪兵营营长汤存心(仲桓)保护下,跑到东校场演武厅,由几个士兵背着他上了城墙,避开乱兵,逃到同在城根下的周善培开办的“幼孩工厂”(童装童具工厂),才赶紧换下那身金灿灿的都督礼服,穿上蓝布衫,继续逃跑,结束了12天的都督生涯。
镇压
兵变发生后,军政部长尹昌衡飞马而出,急赴凤凰山军营,召集与他亲近的川籍军官们迅速商议。随后,尹昌衡率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新军,策马进城,搜捕乱兵。
抢劫之后的乱兵,早已成了乌合之众,难以与有备而来的尹昌衡部队交锋,纷纷逃窜出城,逃得慢的都被当场处决。街上到处可见他们的尸体。
在成都最为紧急的时候,人们又想起了那位退位的总督赵尔丰,他毕竟威望卓著,而且手里还有担任他的警卫部队的三千巡防军。于是,“商民纷纷诣尔丰环跪,吁请维持治安”。赵尔丰“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干预,绅民固请不已,此心凄恻万分;又闻军队肆扰不休,若不急行设法,更不知伊于胡底”。于是,赵尔丰发布了一张布告,要求所有乱兵必须立即回营,既往不咎,否则就军法从事。布告的落款是“卸任四川总督,现在川旗边务大臣”,没有盖印,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赵尔丰和那些恳求他出面收拾乱局的人们,绝对没想到,这会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赵尔丰刚刚开始行动后,如同事先安排好一般,数万名“同志军”突然从四门进入成都,兵力远远超过城内任何一支部队,他们开始四处搜捕乱兵,抓住就当街枪决或斩首,迅速恢复了秩序。而这些“同志军”,只听命于罗纶。逃出成都的乱兵也被各地同志军纷纷劫杀,当然,不只是“为民除害”,更是为了他们身上的银子和珠宝。
根据英国总领事务谨顺的记载,哥老会此时将成都分为几个“码头”,进行管理,恢复秩序,实际上成了真正的当家人。英国人注意到,在这场骚乱中,最为敏感的满城却风浪不惊。同志军追杀乱兵,一些乱兵逃入了满城,将军玉崑在同志会要求下,收缴了乱兵们的武器,驱逐出满城,而满族人自己的举动始终是极为小心谨慎的,因此成都没有像西安和武昌那样,发生汉人屠杀满人,或像南京那样发生满人屠杀汉人的行动。
分裂
当时,成都的军队主要是两支,巡防军与新军。新军是正规军,独立前负责清剿同志军,而巡防军相当于武装警察部队,主要负责安全警卫。因此,城内主要是巡防军。这支部队为旧军,装备训练等都不如新军,但人数总共2万多,超出新军一倍。巡防军的首领,原是田征葵,对保路运动最为深恶痛绝的官员。独立之后,他已经离开。军队都集中在新军统制朱庆澜的手中,但实际上,朱庆澜也无法有效控制巡防军。
四川宣告独立之后,深谙内情的周善培,多次规劝蒲殿俊,设法将巡防军尽快调出城外,各回防地,免得在城里滋事,但蒲殿俊迟迟不敢。巡防军的军官们也表示,希望都督接见一次,他们就好回防,蒲殿俊却多方推延。随着军饷日竭,军心开始浮动,负责管理军队的朱庆澜急了,带了巡防军的11名主要军官,去拜见蒲殿俊。蒲殿俊无奈,只好全身披挂,穿着军服佩刀接见他们。蒲殿俊站着训话不到十分钟,据朱庆澜讲,“只听见佩刀在地上夺夺的响”。接见之后,巡防军军官都笑着说:“天气还不冷,都督为甚这么夺夺地抖呢?”蒲殿俊暴露的这种紧张害怕,令这些骄兵悍将更为猖狂。
对于朱庆澜这样一个外乡人掌管军队,新军中的川籍军官们十分不满。这支陆军十七镇(师)是四川唯一的一支正规军,高级军官多是外省人,“本籍人众俱处下僚”,“每愤不平”,久之形成两个集团,而本地军官人多势众,“每于宴会场合,狂饮之后,常于外籍军人以难堪甚至指名叫骂”,如有一人向外省军官“大发脾气”,另一人就会“拔出手枪”,第三个人就“把指挥刀击在石板上”,每每能够得逞。而陆军小学堂总办、受过良好私塾教育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彭州人尹昌衡,就是他们的核心人物。
在独立之前,尹昌衡等曾向蒲殿俊提出三点要求:一、尹昌衡任军政部长;二、在第十七镇之外再另编一介镇的军队;三、参谋部内要设一个四川人任参谋。蒲殿俊只能答应。其实,川籍军官早已放风:“殿俊文治才,安知兵,必欲为都督非尹昌衡不可!”军政府成立后,尹昌衡出任军政部长,实际上成了本地官兵的真正指挥者,两位都督“令诸军不从,召诸将不至”,其实是个光杆司令。
黄雀在后
兵变当晚,成都城内的三帮人,同盟会、保路运动首领们及军官们分别召开了三个会议,商议自己帮派应如何在善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军官们的会议在四川陆军小学堂举行,十分热闹,会上有军官高喊:“匹夫可以为天子,难道尹昌衡不可以当都督?”尹昌衡毫无悬念地成为军方的候选人。
第二天晚上,各派在皇城内至公堂开会,同盟会提出民选都督,在这样的乱局下,这种超前的想法当然被所有与会者否决。其实,在四川实力很弱的同盟会,需要时间来壮大自己。对于这个自己没捞到好处的新政权,同盟会早已不满,一面联络同志,一面遣人到渝请兵,“谋即日推倒之”。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在一次以孙文的名义召集的会议上,董修武就公然提出,“人民对蒲殿俊行政当局极为不满,将必须进行二次革命”。这次会议是董修武在成都南校场召开的一次万人大会,会场上高悬一块牌,上书“同盟会会长孙文、副会长董修武代”,仿佛灵位一般,于是“孙文之名传至家喻户晓”。而直到推翻,蒲殿俊的政府还不过在位12天,不知道同盟会是如何判断“人民极为不满”及如何判断蒲殿俊不可能有作为的。
会议并没有太多的争执,实力最强、腰杆最粗的尹昌衡被公选为都督。这次会议,本来不推副都督的,但是,巡防军代表提出,罗纶应该担任副都督。此时的罗纶当然不是那个只会高喊宪政民主的副议长,而已经完全恢复了黑道老大的声势,城内数万“同志军”就是他的小弟们,实力实际与尹昌衡不相上下。而且,此时罗纶也正坐在会场内,众人当然恍然大悟,一致通过。
董修武在随后的新政府中,出任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为一切政事之总汇,凡出入文牍及发布命令皆须经过本处始为有效。”同盟会终于不用自己的一枪一弹,取得了四川“革命”的领导地位。
未雨绸缪
兵变后,看到罗纶当了副都督,有一个人恍然大悟,这就是周善培。
早在赵尔丰交权,宣告四川独立前夕,在新政权中只捞到了军事参议院院长的罗纶,大为不满。这位有着黑道背景的四川咨议局副议长并不甘心。在赵尔丰即将交印前一刻,即11月26日晚上8点,罗纶派人前往总督府,接收赵尔丰的督印,而根据协议,大印必须交给蒲殿俊。督印如果到了罗纶手里,加上他的黑道势力,四川的局势将发生巨大的混乱,赵尔丰自然不能交印。赵尔丰立即致电周善培:“现有两个人在督署官厅,说是罗纶派来的,要我把印交给他们。你们干些什么事,叫我为难。”
周善培赶紧打电话询问蒲殿俊,蒲殿俊说:“这是两个混蛋,请赵帅把他们拿下就是了。”
周善培说:“赵能拿人,他两个怎么敢去?他是要交卸的人了。你还是问下罗子青(罗纶)。”
蒲殿俊说:“罗子清没有这么荒唐。”
周善培坚持道:“局面到了今天,父子兄弟也难免各有意见,你还是问一下好。”
蒲殿俊便给罗纶挂了个电话,随后告诉周善培:“问过子青了,他没有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