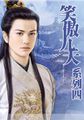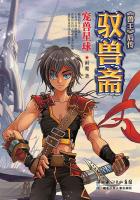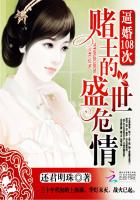铁路收归国有,取缔“租股”,严禁用公权力强迫农民以交租的方式”被”当股民,这一为农民减负的举措,以任何意识形态的秤杆衡量,都绝对堪称仁政,却被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彻底扭曲。中南海的脑部信号,无法在帝国的脸面上准确地表达出来,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面瘫”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呢?
“盛”名之下
大清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他的亨通官运、商战经历、财富传奇,无疑令他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无论对内对外,他都是个强势的人,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中国铁路这个大舞台,他开始强力推进铁路国有政策……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久未登台的盛宣怀,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赢得满堂喝彩。
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都一直是中国铁路这个舞台上的名角儿。但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赶到了上海,以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与他同样郁闷的还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前年(1909)在直隶总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砖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沿途派人照相,构成“大不敬”。端方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办川汉、粤汉铁路。
这两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同时分管铁路,两柄宝剑的寒光一同毕露,雷霆手段频出,倒也令向来软弱的大清中央,在铁路国有问题突然雄起,寸步不让。
打趴胡雪岩
盛宣怀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
首先,盛宣怀的官运实在亨通。如同那个年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他也科举场上十分失意,但自从担任李鸿章的机要秘书之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于任事,他开始在大清国的官僚体系中青云直上,最后终于成为部长级高官(“尚书”),而且,执掌的是权势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机关:邮传部。邮传部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航运等新兴垄断产业,是大清国各派政治力量PK的主战场。从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该部在六年间居然十三次更换部长,竞争十分激烈,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比部长级别更令人羡慕的是,盛宣怀从踏进机关大门的第一步开始,几乎一直都是脚踩官场与商场两只船,而且与胡雪岩那种挖空心思挤入官场内寻找靠山的买卖人不同,盛宣怀下海,几乎都是由组织任命、带着红头文件和财政资金的。当然,盛宣怀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出色的商业才干,在官方资源的强大支持下,无论“外战”还是“内战”,几乎无往而不胜。
“外战”方面,他的经典案例就是成功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在一系列两败俱伤的价格战幕后,大清国政府充分发挥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不仅授予轮船招商局垄断经营权,而且还提供财政贷款,而又正值美国资本方计划实行战略转移,从中国撤资改投美国新兴的铁路大建设,旗昌轮船上终于升起了黄龙旗,降下了星条旗。在轮船招商局将旗昌公司纳入怀中的同时,主导收购事宜的盛宣怀,也乘机将轮船招商局纳入自己怀中,以徐润为首的招商局原领导班子,或因腐败问题,或因能力问题,受到了整肃。
“内战”方面,盛宣怀最富传奇性的案例就是将财神胡雪岩彻底打趴下。严格地说,盛、胡之间的斗争,并非单纯的商战,而是两人背后的李鸿章、左宗棠的权力斗争及路线斗争。胡雪岩尽管戴着红顶子,但毕竟没真正在机关内混过,根本不是盛宣怀的对手。当胡高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依托其“阜康钱庄”里的储户资金,与外商进行生丝大战,以图获得暴利时,盛宣怀则瞅准时机,轻巧地打断了胡的脊梁骨——资金链。胡雪岩曾经出面为左宗棠借了不少洋债,这些债务的管理也是阜康钱庄的重要业务和利润点。清政府将这些债务分解落实到相应的省份,统一汇总到上海后,由上海道台交给胡雪岩;而外资银行则直接从胡的钱庄按时收取本息。上海官场恰恰掌握在李鸿章和盛宣怀手中。在胡雪岩的生丝大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盛宣怀密令上海道台暂缓向胡支付官方还款,胡的资金链立即崩紧。同时,盛再向外放风阜康钱庄银根不稳,引发了挤兑风潮,胡的资金链终于崩断,导致身败名裂。
财富防火墙
令同时代人艳羡的是,盛宣怀不仅是商战上的常胜将军,而且其聚敛起来的大笔财富,居然顺利地移交给了子孙们。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盛宣怀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而他的同时代人,如徐润、郑观应、刘学洵、刘鄂,其财富基本是昙花一现、及身而陨,而张謇等人,虽然在实业界名声巨大,却其实是个“空心老倌”,并没有多少真金实银。
盛宣怀聚敛财富的路径,与这些人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国有资产的打工者和看护者,他们的财富显然不是来自于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这些企业虽然大多是由国有资金支撑着,但打的却是“官督商办”的旗号,财政投入并不作为股本金,而是作为政府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管理者可以“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占据不少股份。二是经营中大建“老鼠仓”及进行关联交易,但凡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
但在那个年代,贪腐已是常态,官员们倘能在贪腐之外还做点实事,就已经算相当具有先进性了。盛宣怀自己在写给醇亲王的信中就说:“盖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尽趋之,办事人受谗谤而人尽戒之。”
盛宣怀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他持有大量股票的这些企业,及时地进行了“改制”,从而多少摆脱了政治力量的牵制。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张股票)股东参加,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在董事会的9名当选者中,盛宣怀以4769张得票高居榜首,当选为董事会主席。这些表明,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在这些企业中,股东开始取代政府,“商办”取代“官督”,而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力量。同样,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推举为总理,随后又被推为董事长。好歹能得到法制保护的企业股权,以及大量投资于租界内的动产、不动产,为盛宣怀的财富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抵挡来自官场的不可测的风波冲击。
与同时代大多数富豪们不同的是,盛宣怀首先并且一直都是体制内的人。与其说他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去谋求政治上的保护,不如说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与老练,造就了在经济上的成就与地位。
早在戊戌年间,作为一名改革的实际操作者,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更有影响力的改革实践者一样,盛宣怀明智地与康梁等“口水改革家”们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认为,康有为等“将尽举吾国之政教、法制而变易之,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盛宣怀是位实干者和践行者,通观《宣统朝政纪》,盛宣怀的姓名约出现70多处,几乎都是奉旨接办某项艰难的任务,比如对外谈判、对内赈灾。
但这次,盛宣怀并不知道,前方居然是一个极大的厄运在等待着自己。
众矢之的
铁路国有就是盛宣怀唱响的第一个高八度,赢得了那些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陕西巡抚恩寿,请求将西潼铁路收回官办;
山东巡抚孙宝琦,请求将烟潍路收归官办;
江西籍在京官员集会,一致赞同江西官商各界提出的九南铁路收回国有;
福建漳厦路公司打报告给邮传部,请求赶紧派人“接管经理,并召集股东开会,布告暂行由部接收”;
云贵总督李经羲致电盛宣怀:“桂蜀国有,从速宣布为宜。”他很实诚地认为“滇、黔、桂以无力,望国有”,不似湘、粤、蜀那样“为私利抗国有”……
但是掌声未息,本该对国有政策报以最大掌声的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却是嘘声一片。掌握了话语权的商办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将铁路国有看作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大侵犯,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盛宣怀和邮传部成了众矢之的。
国有政策宣布后数日(5月12日),粤汉铁路湖南公司在长沙贾公祠召开大会,到者数百人;次日,又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数千人;再后一天,继续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就达到数万人。商议的主题则是,如何以抗拒为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
会场气氛是激动的,甚至有点感人。有一名为贾武的人慷慨陈词后,居然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自言誓不与盛宣怀共戴天”。据说,一时间“满座痛哭,声震屋瓦”。在之后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我们能不断发现这种动辄千人、万人的集体哭场景象。那些在铁路建设方面成绩平平的高管们,却在动员民意、操纵集体无意识方面,显露出了出色的才华。
最后,湖南方面决议,“万众一心,恪遵先朝谕旨,及宣统二年上谕,完全商办,实力推行”,“租股、房股、薪股,照旧收集”。除了上访请愿外,他们还决定:对于那些“反对湘路之完全商办、妨碍湘路建筑”的人,“湘人认为公敌,以强硬手段对付之”,这是近代史上首次公开地因经济问题而诉诸“强硬手段”的人身威胁。他们还表态说,“外国人如来湘强事(铁路)修筑,湘人必集合全体共谋抵制,无论酿成如何外交巨案,在所不顾;若部派督办来湘,湘人亦以此法对付之”,“我辈定以死力争之,闭市、停课、抗租,均确定为最后之办法”。
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这种对抗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国家、民族、地方、股民,还是这些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靠路吃路”的高管们。
信息不对称下的群众动员,效果很好。5月16日,长沙、株洲一带铁路工人1万余人,“一概停工”,进入长沙示威游行,“沿途声称,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传单上则出现了更多的敏感词:“我们办我们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钱。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拚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的,大家闹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交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么办呢?”言辞间充满了情绪的对抗。
湖北的情况也类似。《申报》在5月15日报道说:“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咨议局各大团体,以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上谕近于政府夺民权利,将来输入外债授权他人,殊可惊惧。遂于昨日刊发传单,奔走相告。拟即日开会举代表赴摄政王府第,泣求收回成命,仍准商办。”
这对时刻准备着钻空子的革命党来说,当然是绝好的机会。在革命党的暗中鼓动下,湖北多次举行千人集会,革命党人陶勋成亲自上阵,痛斥中央政府媚外辱国,也在公开大会上断指明志,而留日学生江元吉则“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个字。
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年初才创刊,此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何海鸣则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鼓吹反政府暴动。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馆,逮捕何海鸣、詹大悲。
里程最短、筹资最顺利、铁路完工最多的广东省,本来受铁路国有政策的冲击很小,但他们也站出来对抗中央,以便为自己赢得更好的谈判地位。广东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已决定一面奏劾盛宣怀,一面质问总协理大臣”(《申报》),在6月10日的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股东表示要“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对政府的“破坏”全力反抗,甚至也喊出了“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的杀气腾腾的口号。
相反,倒是后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四川铁路公司,此时相当静谧。原因则也是“利益”二字:四川的绅商们都在等待着政府出手,将他们从极度亏损的经营泥潭中解救出去
“卖国贼”的合同
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抗中央,这显然令各省铁路公司有点害羞。
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中央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各省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