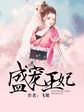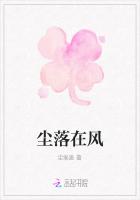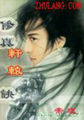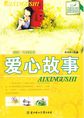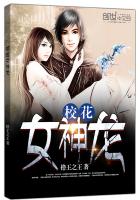风云激变
之所以桦山一行临时决定分道扬镳,是因为他们忽然得到一个“喜讯”,帝国政府终于决定启动征台计划了。于是,这帮人遂临时改变计划,决定分路行动,儿玉一行继续前往奇莱平原,桦山则留下接应远征军。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忽然又改弦更张了呢?
原来,自西乡退隐之后,日本政局就动荡不安。在野的征韩派与民权派组成强大的反政府联盟,严重威胁到维新的稳定推进。出于内部问题外部化的考虑,大久保政权转而支持出兵台湾。
明治七年一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与右大臣岩仓具视都认为时下“对生蕃兴问罪之师,实为必要的行动”。于是委托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与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联合草拟了“台湾番地处分要略”。
2月6日,在右大臣岩仓具视的家中召开了台湾议题的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出兵。
阁议作出后,日本开始落实征台事宜。在太政官内设置了台湾都督府。而李仙得也在3月13日向大隈重信递交了第二十二号备忘录“论占领及对生番之施政”和“论外国人之雇用办法”。31日,李仙得又向西乡从道提出了第二十三号备忘录“论各船舰发缆程序以及雇用外国人着手占据之各方法”。其中很多建议被采纳,为了凸显这次行动的国际性,日本除用李仙得外,还雇佣了美国海军少校克沙勒(随先锋队行动)、美国陆军中尉奥瓦逊(负责建筑阵营)、英国人布朗(负责测量台湾沿海及建设灯塔)、厦门洋行医师曼逊(担任原住民翻译)同行壮胆。
4月,三十一岁的西乡从道由陆军少将升迁为陆军中将,并被任命为“台湾番地事务总裁”——这个名称就非常不同寻常,标举了日本对台湾主权的漠视。
同时,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被任命为参军。陆军中佐佐久间左马太、少佐福岛九成为参谋。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出任台湾都督府事务局总裁。
4月6日,天皇召见了西乡从道等三位将领,并发布敕书,称:日本人受到暴杀,应该兴师问罪,给予相当处分。彼等如不服罪,则临机以兵力讨之。尔后日本臣民一到当地,应思防制土人暴害的办法。此外,天皇还赐给西乡从道西洋马具一套和短枪一组。
4月9日,西乡从道率领日进、孟春两艘军舰从品川港出发至长崎。抵达长崎后,和大久保进行了协商,并致函其兄隆盛,请求支援。西乡隆盛自然大力支持,派出了300名精锐士族,以及由士官为中心组成的信号队(45人),由大仓喜八郎带领的500名各行业工匠前往支援。西乡隆盛还亲自到港口送行,以示激励。
此外,日本远征军还带去了和尚、记者等各色人物,以及182种西洋植物,不仅殖民而且殖植物。表达了日本要长久占领的目的。
此次行动日军总计投入兵力为正规军3658人,另“征集队”295人,“义勇兵”51人。其中“征集队”由为参战而辞职的警保寮官员和巡警组成,“义勇兵”
则以志愿征台的士族为主。整支部队对外自称“台湾生番探险队”,真是荒唐莫名。
覆水终难收
就在日本箭已上弦的时刻,外交领域忽然起了波澜。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在4月13日致函日本外务省,禁止日本雇用英国人和英国船。威妥玛甚至将日本即将行动的消息通知了清总理衙门。四天后,《日本每日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又惹毛了美国。原来,此时的驻日公使已经换成平安。《先驱报》妄称这次行动得到了平安的默许,美国政府也“容许雇用美国士兵,可谓终于承认日本征讨之举了”。而这次行动的目的也被露骨地说出:“欲在台湾岛东部开辟居住地,永久占领。”平安认为这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所以在第二天向日本外务省发出了表示不支持日本此举的照会。此外,西班牙也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表示中立。意大利和俄罗斯公使则对日本外务省提出询问。至于大清国,那就更是要提出质疑了——虽然,质疑晚了一点。
结果,不仅已经签约的英美轮船全部被强制解约,无法给日本运输人员物资,李仙得也被强制召回,而无法踏上台湾的土地,自然也就更无法做他的总督大梦了。
现在日本政府算是明白了,不仅洋人与洋政府是两回事,原来具体的洋官员的言论也不等于洋政府的政策。看来,帝国政府希望拉几个洋人狐假虎威震慑大清国的企图是难以达到了,搞不好还会引发列强落井下石的反制。
外交上的孤立使日本政府一度动摇。三条实美一面通知西乡从道暂缓出发,一面派遣权少内史金井之恭去长崎命大隈重信速返东京。但西乡从道却说了一番大道理:前此从道领都督之命,约定不可变更。今后断无空耗日时,等待命令之必要,若听之任之,只有坐失军机。从道虽不才,但出征事乃圣断。假令太政大臣亲自前来阻止,也断难听从。近来政府之命朝发夕改,人心惶惶,此绝非治国之道。尤其现今从道握有散于各地的陆军官兵,一旦贻误时机,彼等会做出如何行动,实难测知,此乃我最忧患之所在。若强行中止出征,从道惟愿立即奉还敕书,只身直抵生蕃巢窟,荡平其巢穴。若清国发出异议,政府允以西乡以下之徒,答称脱舰开小差之贼徒可也。断与政府无关!
说话如此蛮横,几近恐吓,却得到了大隈重信的默许支持。大隈在5月3日发给政府的报告书中称:“军势之气盛,如何都无法控制。”西乡则退还了雇佣的英美船只,并辞退了外籍人士,只有克沙勒与奥瓦逊两个老美非常积极踊跃,表示“只要没有本国政府的直接命令,绝不离开”。
而三条实美在派出金井后,也意识到金井恐怕不是西乡的对手,便又派出重量级人物大久保利通亲自去长崎。不料西乡得知大久保要来,匆忙在5月2日令先锋部队立即出发。于是,大军出港,日本射向台湾的第一支利箭也就离弦而发了。
不过当大久保在3日晚上抵达长崎后,西乡才发现他的担心是多余。事实上大久保作为这次活动的谋主,一样是不愿退缩。就这样,西乡、大久保和大隈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告知政府,远征照旧不误。如需要雇用或购买船只,尽管大胆行动,“如酿成困难时,大久保为首负其责任”。至于运输问题则以买船代替租船,大隈重信出面以六万元洋银购买了一艘美国船,命名为“社寮丸”。又以十万元洋银购买了一艘英国船,命名为“高砂丸”——还是念念不忘所谓的高砂国旧典,船只命名也要强调台湾曾经是日本的领土。
也就在3日这天,陆军少佐福岛九成乘坐“有功丸”抵达厦门,拜访了厦门同知李钟霖,交付了西乡从道发出的“致闽浙总督公文书”和征台照会。是文开头就暗藏杀机,说:台湾土番之俗,自古嗜杀行劫,不奉贵国政教,海客留难是乐。迩年我国人民遭风漂到彼地,多被惨害。幸逃脱者,迫入贵国治下之境始沽仁字愠恤,藉得生还本国。
这里虽然话说得客气,后面更明白感谢中国“矜全我民之意厚旦至也,我国政府感谢奚似”,但是,所谓“土番……不奉贵国政教”、“我国人民”、“贵国治下之境”,又处处混淆视听,想方设法把琉球并入日本,而把台湾的大部分地区说成中国主权范围之外的无主之地。在照会正文中更说出以下奇文:故本中将虽云率兵而往,惟备土番一味悍暴,或敢抗抵来使,从而加害,不得已,则稍示膺惩之势耳。但所虑者,有贵国及外国商民在台湾所开口岸,运货出入者或见我国此间行事,便思从中窃与生番互通交易,资助敌人军需,则我国不得不备兵捕之。务望贵大臣遍行晓谕台湾府县治边口岸各地所有中外商民,勿得毫犯。又所恳请者,倘有生番偶被我兵追赶,走入台湾府县境内潜匿者,烦该地方随即捕交我兵屯营。
该照会文字极其客气,但内容则蛮横无理,而其所谓生番被追入“台湾府县境内”一句尤其可恶,是处处不忘将中国在台主权范围一缩再缩,居然还要中方帮日本捕拿生番,更是奇谈怪论。
所以,不难想象,当这个照会在5月8日送抵闽浙总督李鹤年的手中后,李予以拒收。并复函强调“台湾岛乃清国政府管辖之地,无日本军兵恣意上陆之理”,并要求日方“撤除阵营,令军兵返回本国,以确保两国交往之亲睦”。但是,送信人早就不见了踪影,而日军先锋部队已经在书到当天在台湾登陆,其中就包括了信使福岛!可以说,李仙得追求的同步性终于实现了。与此同时,李仙得亲自操刀的匿名大作《台湾蕃地是中国帝国之一部分乎?》也在上海刊行,为此行造势。那么,此时的大清帝国又在忙活什么呢?何以如此轻松地就让日军登陆了呢?
责难背后的真相
按照以往的观点,大多认为清廷各级官员在这次台湾问题上人浮于事,是造成被动的根本原因。可是,根据近数十年来史学界的新研究成果而论,这个说法实在很难站得住脚。
此时的大清国刚经历了长期的内战,各地督抚多是经历过实战历练的干练大员,应对外事的能力与眼界也早非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同辈官员可比。但是,两个缺陷限制了他们的个人能力发挥。第一个限制在于大清国糟糕的军政体制,第二个限制在于落后的交通、通讯手段,后者主要体现为铁路与电报的匮乏。
就在桦山在打狗地区搜集情报的3月24日(二月初七),水野遵与一名仆从由旗后港到枋寮,目的是前往琅峤进行地形勘测与军情侦查。因大风等船而耽误两天。27日(二月初十)他们乘小舟抵达琅峤,观察地形并绘图。水野一行自旗后港出发之时就引起清廷地方官的注意。3月30日(二月十三日),枋寮巡检王懋功与千总郭占鳌将这一行人的详细行踪上报凤山县。署凤山县令李煐于4月5日(二月十九日)上禀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台湾道夏献纶,夏又将这个情报上报福州将军文煜与闽浙总督李鹤年。
也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次信息大延误。由于当时两岸没有铺设电报线路,所以信使只能乘轮船前往福州,而当时两地的轮船是由固定班期的,由于等船,信使直到4月11日(二月二十五日)才离开台湾,文、李收到消息则已是4月12日(二月二十六日)。此时也正是日本因为外交纠纷而犹豫不决的当口。可惜大清国未能进一步搜集到有价值的情报,反而是驻华外国使节与洋员控制的海关税务司,因为有“铜线”(电报)传递海外消息,反而比大清国先得到了确切情报。
4月15日(二月二十九日),夏献纶通过台湾税务司得到惊人消息,5000日军搭乘5艘轮船即将前来台湾南部登陆。夏立即将这一消息上报。不过,他的这个情报传递得实在够慢。总理衙门在看到夏的报告前,反而先接到了洋人的预警。
4月18日(三月初三),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梅辉立前往总署,询问了一些相关问题,并发出了最早的预警。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威托玛发出公函,正式提醒清廷注意日本即将对台湾展开的行动,并询问清廷的立场。这份公函发出的第二天,总税务司赫德根据广东税务司的情报也跑来总署告警,到4月22日(三月初七),由于收到了厦门税务司送来的同样情报,赫德第二次到总署告警。
而此时日方正因意见分歧陷入瘫痪状态,要再过10天西乡才违令派出先头部队,而距日军最终登陆台湾则尚有17天的时间,距日军展开对番社的进攻则还有31天的时间。这是历史留给大清国的反应时间差,如果从第一次接到梅辉立的预警开始,历史一共给了大清国21天的时间阻止日军登陆,35天的时间阻止日军对番社展开进攻。以当时清政府的交通通讯手段,在21天内阻止日军登陆虽然困难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而在35天内采取有效的外交、军事反制行动,遏制住日军在台湾的军事行动,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可惜,所有这些预警都没得到应有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在4月27日(三月十二日)转发给总署的情报。这份来自上海的情报,是根据长崎方面的情报汇总而成,内容非常精确。不仅提及李仙得是“参议”,并提及日军规模及欧美船只代运兵员情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还精确指出了日本此次出兵的直接动因:“因旧藩部属武士新近内乱,不惬国家。
请征高丽不允,恐再作乱,姑使之往打生番,不计胜败,是驱若辈以从事而已。”
但是,对于这份情报内容的真实性,李鸿章并未作出判断,而只是中性地转给总署。就在第二天,李鸿章又给总署发出一封专函,这才讲出自己的判断:不相信十二日他转给总署的那份上海情报的真实性。
李鸿章按常理衡量日本,觉得“各国兴兵之举,必先有文函知会因何起衅,或不准理诉,而后兴师”。何况日本刚与中国正式缔结了友好和约,又在觐见清帝问题上大出风头,两国“和好如常”,仅仅一个台湾生番问题,日本又怎么会“未先行商办”,就“遽尔称兵”呢?而且,就算是“冒然兴兵,岂可无一语知照”?他哪里知道,日本的照会是和枪声同时送来,而且是故意送到福建地方官手中,而不是北京的中央机构。
此外,李鸿章还看到了“日本内乱甫平,其力似尚不足以图远”,就算是内部问题外化,李鸿章觉得日本也应先入侵朝鲜较为合理。可是,“江藤新平请伐高丽,尚因不许而作乱”,日本又怎么会“舍积仇弱小之高丽,而先谋强梁梗化之生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