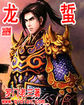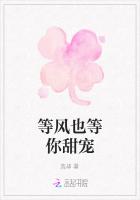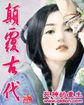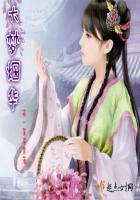最后,日本难道就没有考虑到,入侵台湾,必将与中国冲突,“中国以全力争之”,日本无法取胜,徒然在国际上留下“悖义失和”的坏名声,不是太不合算了吗?
至于外国驻华使节的警告以及税务司方面的情报,李鸿章同样不以为然。他觉得,“近年东洋新闻百变,诈讹多端”,不能听风就是雨。其次,这很有可能是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搞的鬼,因为此人与日本关系亲密是公开的秘密,故而“代为虚张声势,亦在意中”。李鸿章反而认为威托玛所谓“日本并未出有向中国称兵战书明文,且有钦差大臣前来中国之议,以此推之,似无发文称兵之心”这番追加叙述“似尚平实”。从而得出了日本不至于贸然出兵台湾的错误结论。事实上呢?日本兵是三天后就出了长崎港了。
不过,李鸿章仍有一过人之处,那就是他从预防最坏结果的角度指出,直隶远离福建,所以李鸿章“不知该省有无防备”。“此事无论虚实”,都应该提前进行战备。并引《孙子兵法》中的名言“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备之”为证。最后还再次强调“各国垂涎台湾已久,日本兵政浸强,尤濒海切近之患”,就算这次不爆发军事冲突,也只是早晚难免的事情。
总署的麻木与李鸿章的觉醒
但遗憾的是,总署看到李鸿章前面的分析后遂做高枕无忧之想,除了将李鸿章的建议全文原封不动地转发给福建将军文煜做参考外,此后近20日内,丝毫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日军遂得以大摇大摆地于5月7日(三月二十二日)成功登陆台湾,未受任何阻挠。又过了三天,李鸿章才刚刚根据上海发回的新情报确认日本出兵台湾的可能性极大,而且得到的还都是些日本陷入外交纠纷前的老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已足以让李鸿章意识到问题严重。在5月10日(三月二十五日)这天他致函总署,提出了四点建议外加一点总结:第一,日本“悖义失好”,美国人“雇与商船”帮助日本“装载弁兵军装”,“均属违背《万国公法》”,故而首先要从会晤美国驻华公使开始,依公法与之理论,如美国“遵照公法撤回李让礼等”,同时“严禁商船不准应雇装载弁兵”,则“计日本兵船无多,其谋当渐寝息”。此为第一要义。
第二,马尾造船厂自制的兵轮船及水师船只不少,“似应先派往台湾各港口盘查了望。如遇日本兵船入境,问其因为何事而来?如船中载有陆兵多名,应即拦阻,勿令进口上岸。”
第三,根据前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寄送的台湾全图显示,“琅峤系南路生番后山海口”,适合登陆,本拟建造炮台但并未施工,也没有设置驻军与警戒哨所,如果日军来此登陆,清军实在是“一无防备,殊为可虑”。台湾本岛驻军又没有战斗力,“无甚足恃”。只有从大陆地区“另调得力陆军数千,即用轮船载往凤山琅峤附近一带,择要屯扎,为先发制人之计”,才能有效阻止日军登陆。如果日军胆敢“擅自登岸”,清军就可以一面进行外交阻拦,一面进行军事集中,让“劲敌无隙可乘”,“此为第二要义”。
第四,郑重推荐船政大臣沈葆桢“管辖新造兵轮船,又系闽人,情形熟悉”,似应由总署知照,“会商将军、督抚密速筹办”。
一点结论:“日本既有此议,早迟必将举行,若不慎谋于始,坐待兴师,将来无论彼此胜败,恐兵连祸结,竟无已时;于沿海大局关系非浅。”
李鸿章的建议倒是立即引起了总署的高度重视,在这个指导方针下,恭亲王与文祥进行了宫廷说服活动,终于在5月14日(三月二十九日)请到谕旨,命沈葆桢巡查台湾,并通过照会责难日本背约。
应该说,这个决策过程本身还是很高效率的,可惜因为整体的情报传输系统的迟滞而大打了折扣。日军已经登陆,美英也自行与日本划清界限,李鸿章的未雨绸缪全成了事后诸葛亮。
定计之后又十几天的时间,清廷从中央到地方再次无所作为。又要迟到5月29日(四月十四日)才正式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但是,当时福建全省武备稀松,台湾更是只有两营兵力。沈葆桢固然可以随时去台湾,可是无兵无枪无炮,在日军已经登陆的情况下,就靠他带着几个幕僚、两艘轮船,自然阻止不住日军的行动。
更不可思议的是,5月14日发出的抗议照会系由一名雇佣的英国人送往日本,此君在上海迁延一月,直到6月4日(四月二十日)才把这份照会送到日本外务省。与此同时,台湾地方官员倒是在始终密切监视日军的一举一动,主角还是王懋功与郭占鳌。从登陆日开始,每天日本舰船的进入口数量、协助人货的详情、以及日军的行动,这二位始终在认真观察,详细记录,逐日上报。可惜,由于缺乏有效的通讯手段,他们尽职尽责的成果是注定无法为总署与李鸿章的决策做参考了。而台湾本岛由于缺乏现代陆海力量,同样无法采取有效行动,也只有对日军的行动认真观察,详细记录,逐日上报!
如此又拖到6月9日(四月二十五日),清廷才又发出上谕,指示南北洋大臣与沿海督抚协助沈葆桢武力增援台湾。而日军却早在5月22日(四月初七)已经展开了针对番社的军事进攻!
就在6月9日的上谕还在途中的时候,苦于无米之炊的沈葆桢已于6月12日(四月二十八日)上书恳请军事增援。沈的上书还没抵达北京,李鸿章已于6月15日(五月初二)不谋而合地致函沈葆桢,表示自己可以解决调兵难题。
原来,早在沈葆桢刚接到命他巡视台湾的上谕后,他就意识到日本此次来者不善,绝非空口所能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沈葆桢发现问题后,致函李鸿章,大呼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而李鸿章终于在此前的5月19日(四月初四)确定日本确实出兵了。在接到沈葆桢的求救信函后,他在6月14、15日(五月初一、五月初二)的回信中相继表态:现在国家装备最精锐、训练最有素的部队都是我的旧部,最先进的武器也都在我的辖区内,我岂能坐视不救?李鸿章在6月15日的回信中明确指出,“徐州之记名提督唐定奎,朴干能战”,其麾下所部武毅营原属刘铭传的铭字军系统,有十六营兵力,其中马队三营,步兵十三营,“均系枪队”,当年追随刘铭传“历剿粤、捻,号称劲旅”。现驻扎徐州,被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李宗羲“倚为保障”。其中步兵13营6500人可由“唐提督统带”,“由徐移至瓜洲,派轮船径驶该口,分批航海前去”增援台湾。剩下马队三营则留防徐州。
要调唐部赴台,必须得到两江总督李宗羲与江苏巡抚张树声的同意。好在前者是李鸿章的科考同年,后者是李鸿章的淮军旧部。李鸿章乃以私函沟通,先于6月20日(五月初七)致函关系密切的张树声,继而于6月23日(五月初十)致函李宗羲,无外乎替沈葆桢诉苦,指出沈“颇有发愤为雄之概。惟只身赴台,手无劲兵”,“订购铁甲船,亦虑缓不济急。惟闽省勇营本少,枪队尤少,绿营兵更不可用”。故而只有调唐部援台,因为“东南数省尚无此现成大枝枪队”,唐部“又扎闲地,暂可挪移”。最后李鸿章还似乎漫不经心地顺笔说到,长江口是不会遭到日本攻击的,实则是给李宗羲解压,以使之痛快地同意调唐部援台。接着就陷入了一个新的等待时期,直到6月24日(五月十一日),李鸿章初步确信调唐部无大问题后,这才正式致函总署,表示可以调唐部增援台湾,并希望总署能“令津沪各局,先尽现存炮械军火,陆续解济”。
这一运作过程充分表现了当时大清国的人情政治已经到了完全替代正规制度运作的程度,而更深层的悲哀则在于之所以人情政治能无视正规制度,正在于正规制度更加糟糕。君不见,两次鸦片战争都没能打出一个外务省,最后搞个总理衙门还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不是总理外国事务衙门。而且这个衙门也是可怜得很,当其创办之初连常设经费都没有,只能从户部每月赊借三百两白银,日后再由南北洋各省督抚的海关提留中分摊偿还。当其运转之初,自然也没有启动资金,只能再向户部预支三千两白银,这才勉强开张。至于宪政政府、参谋本部之类的机构,大清国就更没有了。所以李鸿章等人也只好搞人情政治,天才外交了。但是,再大的天才也难为无米之炊,交通、通讯手段的落后,严重限制了李鸿章的外交天赋的发挥,大清国就像一个迟钝的恐龙,反应总是严重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李鸿章的天才外交也就不免蜕化为恐龙外交了。
不过仍有值得肯定之处是,李鸿章个人的反应再次走在了同僚的前面,就在6月24日(五月十一日)致总署的公函中,李鸿章提出了“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的战略指导方针。并坦言“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为什么已经认识到笔舌难胜兵势,说来说去还是只追求和局,而不是趁机开战,狠打日本一通呢?原因是复杂的,主因还是在于此时的大清国内忧外患,焦头烂额,实在无力多顾。西北回乱牵扯了大清太多的精力,也消耗了太多的国力。东南海防实际就是个空架子,长久处于传统陆权构架边缘位置的台湾,就更是软腹。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私函中早就交了底:大清国财政困难,当初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李鸿章解决捻军,都是自己筹款,不仅不敢指望中央拨款,只希望中央不帮倒忙就好。现在国家尚未从长期内战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对外失败中恢复元气,自然难以强硬对外。所以能和平收场,实为上上策。除非迫不得已,还是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与日本人开战好。而且,李鸿章虽然争取和局,却也做出了最坏打算,这就是他后来在7月7日给沈葆桢的信中所说的:“狮子搏象,要用全力!万一决裂,必须备集而后动,谋定而后战。”即不打则已,打就要全力以赴。
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沟通的时间差,沈葆桢在李鸿章回信的6月14日,与帮办大臣潘蔚一起分乘马尾造船厂的两艘国产轮船(安澜与伏波)前往台湾。
潘蔚于6月15日先行抵达,沈葆桢则视察了澎湖,随后在6月17日抵达台湾本岛。无奈此时日军已经登陆,两艘轮船自然无法阻止日军行动,此后中日双方屡屡进行外交接触,但是西乡之流根本无意妥协,他们一面与中方胡搅蛮缠,一面加紧清剿番社。沈葆桢等人缺乏有效的陆军兵力可调,只有对援军望眼欲穿地等待。
而此时的李鸿章则忙着协调各方关系,为唐部赴台做准备工作。其中包括落实唐部调度及赴台后的军饷着落,另安排“刘盛藻统率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拔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扼,以备南北海口策应”。
这个准备工作一直忙到7月23日(六月初十)才有了头绪。8月1日(六月十九日),唐部接到增援台湾的正式命令,同时援台的还有李鸿章张罗到的洋炮二十门,火药四万磅。次日,唐军开始分批离开徐州,前往瓜洲古渡口乘轮船前往台湾。由于没有铁路运兵,故而行动缓慢。到8月14日(七月初三)第一批部队才得以登船出洋。又直到8月26日(七月十五日)唐部先头部队才登陆台湾,进驻凤山县旗后港。
整个调兵过程几乎成了李鸿章的个人人脉大运动。不仅所调是他的旧部,相商者一为他的旧部,一为科考的同年。最后负责调配船只者系其幕僚盛宣怀,组织人员、器械、粮饷分组运输的是徐文达。共计调用轮船七艘(永保、琛航、大雅、伊敦、永清、利运、海镜),其中四艘(伊敦、永清、利运、海镜)属于李鸿章一手操办的轮船招商局旗下(另三艘来自福州船厂,另有江南制造局的两艘轮船备援)。
整个调兵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时间问题。从瓜洲到台湾的水程虽然路程远,但因为有轮船运兵所以只用了13天的时间。而从徐州到瓜洲的陆路距离虽然短,却因为没有铁路反而花了14天的时间。如此整个进军过程共计花费了26天的时间(内有一日为抵达瓜洲与立即登船的重合时间)。反观日军,5月2日(三月十七日)离开长崎,5月8日(三月二十三日)登陆,仅一周就完成进军过程。更何况清廷决策已落后手,等唐部淮军进驻台湾,日军业已完成军事清剿活动,并占据了有利地形,静待大清国来理论了。
自掘坟墓的日本远征军
5月18日,日本军与当地番民发生了第一次战斗。5月22日,西乡率领的1900人的后队及给养运输船抵达琅峤湾,登陆射寮。同日200名日兵进攻石门,与80余名原住民发生了双方的第一次正面军事冲突,牡丹社酋长父子战死。随后日本扫荡了牡丹社等多个番社,并开始建兵营、修道路,造都督府,设医院,修桥梁,筑道路,开荒屯田,作长久之计,并向番民分发“烧饼旗”。总之一句话:不走了。7月21日,侵台日军指挥官西乡从道甚至宣布已经降服各社生番,大有开化番民,长久控制的势头。
但是,日军很快就遭遇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强悍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