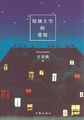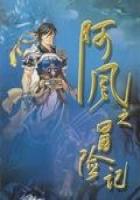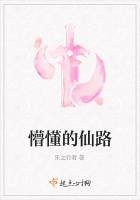为了这次远征,日本筹备了1000只鸡、6万个鸡蛋、2300条鲑鱼、60箱干鳕鱼,还有大量的米、牛肉、咸鱼、各类蔬菜。貌似准备充分。可是日本当时并不具备远程运输的保鲜技术,后勤安排是按照常规的三到五天的行程计划的,而仅运往台湾就要10天,且不说台湾当地的炎热气候。结果就是肉和蔬菜到了台湾就腐烂生蛆,其他食物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质。食物中毒加上传染病横行,共同给侵略者制造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据参与是役的日本军医监落合回忆,当时日本士兵“所尝到的艰难辛苦,究非笔墨所能详述。在这海南绝岛瘴疠之地……粮食本不完备,又加上运输困难,常为泥路及险恶的斜坡所阻,战斗部队因此为饥渴所困,不知有多少次。有时只能靠腐烂发着恶臭的饭团充饥……加之地势炎热如灼,设备又极简陋,所谓帐营,也不过徒有其名,只是一块天幕,有二三个月在其间煎熬,以致全军都患痢疾,苦闷呻吟之声,惨不忍闻”。甚至有五个病号因无法忍受,三人自缢,二人跳海。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西乡本人跑了两三次医院,给他的勤务兵抓药。其身先示范的作风固然能收敛军心,但西乡自己却已经意识到,再耗下去,日军必然“自动瓦解”。据日军战后公布的数据,是役日军死于战事者仅12人,而死于疾病者则有550余名之多。
由于医药匮乏,到了9月末,病情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日军全军几乎无一人能幸免。疫情最糟糕的时候,一天中连死13人,有近一半的士兵已丧失吃饭的力气。医护人员自身也罹患了一样的疾病倒卧在床。最后连服劳役的夫卒工作也只得雇佣附近的原住民协助。龟山分营的日本兵营连续两次被飓风吹倒,一开始日军还进行修复,但最后连修复的力气也没有了,竟任其倾倒在沙地上。同时,因为受到南海暴风肆虐的影响,粮食运输船无法靠岸,造成严重的军中缺粮现象。
士兵如此,那些本着“长治久安”的幻想来的移民们的境况更糟,“有从长崎来的商贩,分别经营屠牛店、荞麦店、豆腐店等,试图做军队的生意。刚开始的确门庭若市,但不到一个礼拜竟都罹患了恶疾,屠牛店、荞麦店皆有人死去,其余的人也纷纷搭船离去。”最后连棺木店的老板也病死了,这一点尤其令日军头疼,因为日、清丧葬的方式不同,所以日军只得选取简单材料,自行打造棺木。
据事后日军统计,这次侵台共出动3658人,经多次增兵,总数最多时达到了5990人。就是这5990人,共计有3769人患弛张热,3363人患消化道疾病,1590人患皮肤病,784人患间歇热,773人患脚气病,89人患伤寒热。其中很多人是一人患多病。扣除掉战死、病死的560余人,和运回国内的2000余名伤病员,一线兵力其实有限。根据清军的侦查显示,日军后期在台湾的兵力只有3400人,而且其中还有1200人是夫役。军人只有2200人。而清军有当地驻军担任警戒工作,粤勇负责后路守备,装备精良的唐定奎部6500人可以全部作为进攻部队使用。根据沈葆桢的汇报,“淮军甚精锐,勃勃欲试”,“人人有摩拳擦掌,不可遏抑之势”。又说“淮军有灭此朝食之慨”。唐定奎本人也“沈毅勇鹜见乎眉宇,未必肯不战归”。更非日军的集体陷入疾病状态可比。而且,当时双方的武器装备大抵相当,甚至淮军的装备还要略胜日军。
此外,日本的财政也因为这次远征而出现了危机。鉴于军费供给的困难,时任右大臣的岩仓具视希望宫内卿能够暂时将用于皇室建筑的27万元移作军费,可是由于伊藤博文等人的坚决反对而泡汤。最后只好由开拓厅主管黑田清隆挪用10万元的开拓费暂时应急,同时号召公务人员各捐薪水的四分之三以作军费。但无疑这个做法只是杯水车薪。
结果就是,日军对台湾的贸然入侵给近代中国提供了一次最有利的惩罚侵略者的良机。甚至可以说,无需直接交战,只要这样拖下去,就能拖垮日军。所以,连一向主张对外持谨慎立场的李鸿章,这次也主张以强硬姿态对日。可是,随后发生的一切,却谜一样的彻底改变了事件的进程。
外交争锋暗设陷阱
大清国的态度强硬,令日本人大吃一惊。毫无疑问,他们不仅错估了国际形势,也错估了大清国的实力与意图。
岩仓对这个局面深感惶恐,承认这次行动过于冒失,“对清廷的关系既然知之不详,而竟茫然上奏,说交涉程序和规划已经完备,军队已抵国境,临到行将开往台湾,英美两国公使提出抗议,又想骤然停止出师。上则陷圣断于轻率,下则毁国威,内则引起物议纷纭,外则招致他国诽讥,可谓有失体统矣”。
此时大久保一样的心虚,他当初决定不征韩而征台的两个基本前提是:一、征台可以避免与清国的战争,又能转移内部矛盾,二、征台可以速胜。
事实证明,除了内部矛盾确实得到了暂时转移外,两个基本前提都落空了。
事已至此,只有放弃对台湾的军事征服,转而在外交领域追求下述三个新目标的完成:
一、争取体面收场,即以外交手段诱迫清廷承认日本此次出兵为“保民义举”。
二、争取从清廷获得尽可能多的赔偿金,从而将这次远征的经济损失压到最低。
三、在“保民义举”的幌子下,尽量把琉球被害者的身份混淆为日本国民,从而为下一步的吞并琉球预设外交伏笔。
本着欲抑先扬的策略,日本虽然已经决定转向外交斗争,但武戏依然在唱,而且唱得更加热烈。它们一面在国内作动员,一面扬言要购买西洋军舰,远征朝鲜。
对于日本人的虚张声势,李鸿章很不以为然。
在7月下旬,李鸿章确实一度很担忧朝鲜的局势。7月27日(六月十四日),李鸿章特别咨询了过津拜谒的“管带烟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之所以咨询吴世忠,因为吴“在闽带船多年”,又“曾同美领事李仙得往台湾生番处,查办杀夺美船之案”,自然很有发言权。
在吴世忠看来,台湾番民矫健强悍,且地理情况复杂,“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也多次被袭害,两国皆曾“发兵船往剿”,结果却是“失利”,无奈之下仍只有“讲和而止”。相形之下,“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对于吴世忠的分析,李鸿章表示赞同。所以他并不担忧台湾,但却很忧虑朝鲜。
首先,从地缘战略上讲,“朝鲜为我东土屏蔽”,直接保护着大清国的龙兴之地与首都北京。可谓所有藩属国中最重要的一个。
其次,“日本觊觎朝鲜已久”,早在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就怀着“度辽东、图燕京之志”,“大举三韩”。虽未能得逞,但历史教训却很深刻。“盖日本陆军较水军为强,去朝鲜又最近”,若如倭寇之袭扰江浙沿海,尚不过是“沿海肢体之患”,但若日军大举侵朝,吞高丽而图东三省,由海而陆,雄视东亚,则必为“根本之忧”。恰于此时,陈兰彬又从美国来信,称日本“派子弟赴(西洋)各国学制枪炮,习驾轮船”,意图叵测。在李看来,日本人本“多强悍之气”,多购西洋枪炮,岂非中华大患?
但是,李鸿章很快看穿了日本的把戏是虚张声势。因为“往高丽应由日本西北之对马岛济渡,不应该由西南之长崎征发。盖长崎与台湾东面相对也。是其日前暂停发兵及改往高丽之说,或已闻知中国不准,故抑扬其词,声东击西,以懈我之备耳。”
很快,清廷的反应就出台了:
一、造炮台于澎湖列岛;
二、设海底电缆于台湾海峡;
三、购置毛瑟枪三万支于德国;
四、商购铁甲舰于丹麦;
五、由福建巡抚王凯泰集结大军25000人准备渡海赴台。
虽然这些举措都很难立即生效,但已经足以抵消日本的虚张声势。
剑拔弩张中,柳原前光又来到了天津,见到了久违的李中堂。
李鸿章首先问及同治十二年的来华日本公使福岛种臣,何以回国后便退出了政坛。柳原答以“与岩仓大臣议事不合。”李鸿章遂不无调侃地对柳原说出下面一番话来:“十年来华公使伊达,十二年来华公使副岛,回去即退休,是贵国用人行政无常”,还是来华钦差不利呢?对了,说起来你柳原“九、十、十一、二等年同来”,只因为不是公使,所以“官则一年高一年,今作公使,要小心些!”
对此,柳原自然也只有点头称是。
接着双方便开始切入台海危机,柳原抓出一连串的枝节问题纠缠不清,于是逼出李鸿章的连珠妙语: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除非有两日本国,一发兵,一通好也。
且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
你去年才换和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从前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
今日如此办法,中国文武百官不服,即妇孺亦不服,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所谓师直为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