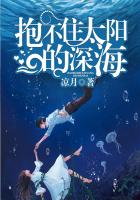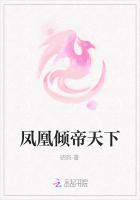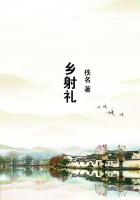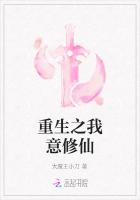事实上,早在1859年,就有来华英国人发现,广州姑娘的穿戴衣着欧化入时:“我在街上散步,看见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颏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引人注目的。”
但这些人终究还是排外的,而且排得近乎疯狂,那么排的又是些什么“外”呢?原来: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劼刚(曾纪泽——笔者注)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
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
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雍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鸱张无识之气,鼓动游民,以求以逞,官吏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嚣张无识者为之也。
所以《伦敦竹枝词》(1888年)才嘲笑他们:堪笑今人爱出洋,出洋最易变心肠。未知防海筹边策,且效高冠短褐装。
对立如此尖锐,他笔下那些人怎么能不恨他入骨?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可他们能毁郭某人的书版,却终究砍不下“二鬼子”的脑袋,原因何在?因为有李鸿章的庇护。
纵然到了垂暮之年,国事日艰,郭嵩焘还能在自己小像的背后,孤寂可又充满自信地写下: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历史讲到这里,郭嵩焘与李鸿章两人的异同,也就跃然纸上了。
论见识,李鸿章逊郭嵩焘一筹。所以他要反复研读郭嵩焘的信函、奏稿、文章。可若论在大清国里办事的能力,郭嵩焘又何尝不逊李合肥一筹?所以,郭嵩焘的很多构想,最终又注定要由李鸿章来实现。
两个人都知道“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也都尝过“一虎难敌群狼”的尴尬。但最终两人却分别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战场。
作为一个觉醒了的士大夫,郭嵩焘何尝不想“学而时习之”,既“立言”、“立德”又“立功”。可他的思维实在走得太远,以致同侪豪杰也被他远远甩在了后面,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面对十字街头的滚滚浊流,他又总忍不住发出超越时代的狮子吼。这就注定了他最终要以一个“孤独的启蒙者”的身份载入史册。
李鸿章不同。他也会发惊人之言,可总不忘了限定在一个尚能让同侪保持基本冷静的范畴内。最明显的一点,他最喜欢讲“变法”,尤其爱谈教育改革、经济转型与军事现代化,但却绝不会像后来的郭嵩焘那样,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清国,就倡议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形势的变化,权利的转移。施展手段,将怀有各种不同动机的人皆为己所用,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去办成一件又一件具体的实事。
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知道,二人都是英雄,纵然有时也互相点一下对方的失策与短处,那也不失英雄之间的交流。到头来,相互之间终究还是相惜的。所以郭才说李“于西学求之至勒,行之至力,诚有见于立国之深谋至计,而其处置洋务亦即能深中窃要。”反之,李也说郭“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郭嵩焘的号)为最。”
伊犁危机
在左宗棠的领导下,清军经三年血战,终于在光绪四年初平定了新疆叛军。
最后的麻烦在于伊犁地区。该地农业发达,矿藏丰富,控制着进入南疆与中亚的要津,可谓兵家必争之地,不幸却仍为俄军盘踞。
欲战,西征军已成强弩之末,军饷也无从筹措。欲和,偏偏派去圣彼得堡谈判的外交特使崇厚不甚了解现代外交,甚至连伊犁的地图都没看,就急于签约。
结果在谈判中损失惨重。
群情激愤中,崇厚被抓进了监狱,清流党齐声主战。左宗棠为自己打了口棺材,表示不成功就成仁。清廷则紧急召见朝野重臣、宿将入京,齐议和战大计。
对于中方的举措,俄国人自然不会保持缄默。光绪五年冬,两艘俄国铁甲舰肆无忌惮的冲到了中国沿海,做武装示威,更扬言要大举海陆军,攻入渤海湾。
结果引发大清国从北洋到南洋相继戒严告警。
当然,危机中也有镇静的人,也有不怕铁甲舰的人,那就是清廷倚为重臣的湘军老将彭玉麟。此公长江水师出身,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屡立奇功,可谓大清国的传奇将军。可事实证明,彭大将军虽然很懂长江水师,但却完全不懂现代海军。他竟然提议:火攻铁甲舰。
结果,不等李鸿章反对,和老彭同属湘系的刘坤一先开了口:时非三国,帅非孔明,地非赤壁。火攻之策,怕是难行吧?
话又说回来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时英国的军舰可是地道的木质风帆战舰,当时清军的火攻都从未有一次奏效,何况现在对方已经升级到铁甲舰的级别?
这倒应了一句话:无知者无畏。可是日本人同样无畏但却有知,于是大清国麻烦。至于现实中的危机则仍要李鸿章来化解。
李鸿章深知,有些话,外国人说一句,胜中国人自己说一万句。为什么呢?
这倒不是说在当年就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崇洋媚外情绪,而是因为在当年的大清国,政治忌禁多,很多话,中国人自己根本就没法子说,而外国人不仅能说,而且说了还更有震撼力。
光绪六年(1880年)夏,伊犁危机渐至高潮。在李鸿章的建议下,当年的常胜军指挥,李鸿章的老朋友,英国军官戈登应邀来华参赞军机。在与李鸿章老友重逢的快叙后,戈登进京。他坦言:中国不应为所谓的“体面”而以国运作赌注,陷入与俄国的无望战争中。他指出,中国欲取胜,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迁都西安;二、准备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放弃满人的统治权。
总之,中国的首都应远离海岸线;陆军的发展应优于海军;中国应大力发展游击战,以规避西方人擅长的阵地战、闪击战、扫荡战与战略包围。“今天中国人出现在它前面,明天出现在后面,后天在左面……直至敌人疲于奔命,直至敌方战士与长官发生矛盾,直至三军为疾病所累。”
最后,他还没忘记表示:如果中俄不幸真发生战争,面对俄国的攻击,他将毫不犹豫地为大清而战。为了减少母国外交上的麻烦,他甚至已作好辞去英国国籍的准备。
如果以上的言论已够刺耳,下面发生的事情就多少有些“危言耸听”了,在一次与李鸿章的私下会谈中,戈登竟劝李“取(清廷)而代之。”对此,李只有一笑置之。
但至少李鸿章的目的已经达到。
清廷虽然没有对戈登的意见作出书面反应,但行动胜于一切。就在这个躁热的夏天,中俄和谈重新启动。谈判地点还是圣彼得堡,只不过中方代表换成了曾纪泽。
英国人说:曾袭候此行实无异于虎口抢食。
但曾袭侯创造了外交奇迹。谈判从光绪六年的夏天一直谈到光绪七年的夏天。最终中方以和平手段收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Tekes)河一带之地。当然,也付出了代价:900万卢布(约500万两)的补偿款再加准许愿入俄籍的伊犁人迁入俄境。
在理想主义者眼中,如此“收复”可谓丢人。但从现实主义的视角,考之当日中俄实力对比,再想一想俄国的扩张传统,想一想当时“中、日琉球一案未了,中、法越南之争已起。美国又有排斥华工之事,清廷苦于招架”,则又无异一大外交胜利。
吞并琉球:日本的第三次落井下石
西洋列强忙,东洋的准列强也没闲着。趁前述机会,日本乘机彻底“解决”
了琉球“悬案”。
明治八年(1875年)7月,日本政府强迫琉球正式断绝与清政府的传统关系,内容包括:
一、停止对清国的朝贡;
二、禁止接受清国册封;
三、撤销福州的琉球馆;
四、移琉球国王入东京;
五、琉球从是年起用明治年号,施行日本刑法,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明治十年(1877年),日本公然阻止琉球入贡中国。
明治十二年(1879年),天皇废琉球王室,改琉球国为冲绳县。
李鸿章本希望他能利用西洋世界的内部张力,互相制衡,为大清国的“自强运动”争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现在看来、西洋世界确实未让他失望。但东洋的挑战却着实令他大感头痛。
李鸿章请周游世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调停琉球争端,结果却是引出日本人空前苛刻的条约。他们坚持由日本永久占据琉球中北部的73个岛屿,而将南部的两个荒岛割给中国。为此中国应:一、给予日本贸易特权与特许权,尤其是最惠国条款;二、永不再提琉球宗室的复国问题。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条约,总署却准备接受!不仅总署准备答应,左宗棠与张之洞也准备答应。前者主张将日本归还的两岛还给琉球,使之复国,既实现了中方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又为台湾找到了屏障,可谓一举两得。后者则强调了伊犁危机,主张“和日制俄”,故力主与日妥协。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在清流健将陈宝琛看来,以“最惠国”待遇换来两个孤岛,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折本买卖。同时,从天朝的视角讲,为两个小岛而放弃对“琉球宗室立国”的承诺,无异于自毁国际形象。
对此李鸿章表示支持。
事实上,直到最后一刻,李鸿章从不把琉球75岛当回事。因为他不会料到30多年后一个新兵种——空军的产生将从根本上改变该岛链的战略价值。他更不会料到70年后会出现联合国,以及更后来的“专有海洋经济区”,还有石油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这些都是任何战略家所难以预先知道的。所以他才说:“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且亦无谓。”但他还是不惜冒中日关系破裂的危险坚决反对这个条约,原因无他。只因他已从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落井下石,与得势不让人的霸道中,看到了一个中国的严重外患源。如果说在过往,李中堂还只是泛泛地谈日本的近与西洋的远,那么现在李鸿章已可以负责任地说,日本就是中国后300年内的头号地缘战略大敌!李鸿章说,“琉球既为所废,朝鲜有厝火积薪之势,西洋各国又将环视而起,自不能不借箸代筹。”
所以他反对分割琉球的提案。可总署的疑问也随之产生:既不同意又无力干预,难道中国就这样一无所得地失去琉球吗?
对此,李鸿章的策略是:既不签约也不承认。即采取“搁置”方案。一直“搁置”到中国在软权力与硬权力均再次强盛之日,再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李鸿章与清流派的一致反对下,总署也改变了态度,坚决反对该分岛条约,转而采取搁置立场。
当年的李鸿章已率先认清了一个事实:“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可惜大清国始终未能制订出一套缜密的国家战略,更不要说有步骤地加以推行、落实了。而日本相反。大清国的达官贵胄们也只有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糊里糊涂中手忙脚乱地去草草应付日本人的连环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