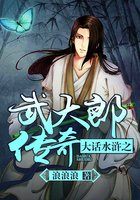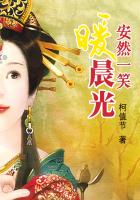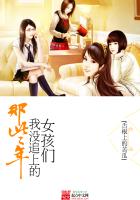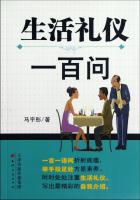就像电流的传递,宝海也震惊了。
震惊之余,他开始更大范围地调查大清国的军事实力。这一调查就彻底进了李鸿章的布局之中。因为李鸿章早就在所有宝海可能去调查的地方布好了阵势。
所谓急则治标,非常时期,表面文章也是要做的,而且要做大做足。
结果,宝海首先发现大清国的海军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向巴黎汇报:他们拥有为数众多的战舰和巡洋舰,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还可配有一支相当出色的辅助运输舰队。在这些舰只中,有好几艘属于造船业最为精良、最为现代化的舰型,而且在航速和武器配备方面也是属于最好的。舰上人员是很精干的。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这些船只的中国军官中,有很大一部分十分懂行,干的极为出色。如果他们在必要时得到美国、英国或德国辅助人员的帮助的话,他们就能应付要求他们干得一切。假如这样组成的一支舰队通过部署装甲舰以及配有威力强大的火炮的快速巡洋舰和铁甲舰,并依靠那些用于近海和内河航行的众多的炮舰的支援来封锁东京湾,我考虑,假如我们不冒巨大的风险,或者不调动大大超过我们已在这个遥远的海域部署的海军力量的话,我们怎能突破这样的防线并把足以击退中国军队的法国陆战队运送到红河三角洲呢?况且中国军队在我军到达要与他们争夺的目的地之前就随时可以集结。
所有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纷至沓来,尤其使我心绪不宁的是,我发现天津军火库一带有着惊人的忙碌活动:码头上每天堆满了大炮、辎重车、各种规格的弹药和各式武器,这些东西运来这里,又运往人们所不知道的地方。我自己设在中国南方的情报员告诉我,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他们还对我讲到在兵工厂和造船工地上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在船坞里,人们紧张地制造和修复船只,而建造船只在平时是需要数月或者数年时间的。
总之,“自中俄危机以来,还从未见过此类事情。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在非常认真地进行(军事)准备”。
于是,宝海忽然把所有问题都从另一个全新的立场上想通了。
德国公使一再怂恿法国占领河内,其实是阴谋让法国陷入与中国的持久战争之中。甚至有情报显示,来自德国的顾问不仅帮大清国组建新式陆军,训练部队,制造装甲战舰,兜售武器,而且还负责修筑防御工事和要塞。宝海忽然觉得他可以肯定,此时在越南境内的清军阵地一定是德国顾问指导构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中国政府撤军是相当困难的。”而总理衙门与曾纪泽的强硬立场及其对所谓宗主权的坚持,都不过是被法方误解了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尊严和民族自尊心的考虑”。更可怕的是,遥远的巴黎并不知道大清国的真正实力,也不知道这个实力背后潜藏着的德国阴谋!
恰在此时,从越南又传来消息,西贡总督居然准备对所有进入河内地区的中国士兵进行捕杀!
在宝海看来,这就意味着“势必会引起北京的不满和愤怒,这样便永远关上一切通往和解的大门,而且会使继续进行任何谈判都根本不可能了”。结果就是:“此时此刻”,“战争已不可避免”。而战争对中法双方都没有好处。
所以,宝海忽然由一个强硬派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扞卫和平的温和派。他向巴黎质问:“到底有什么迫不及待地需要把事情激化到这个地步呢?”“不管事情看来已经多么不可挽回,我仍要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试图进行最后的努力,以便至少推迟发生敌对行动。”
为此,宝海与李鸿章进行了一次长达五个钟头的会谈。他个人觉得,“这种花费时间过多的会谈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会晤的成果完全超出了我的希望。”
这个成果就是日后的李宝协议草约。
差一点,大清国也有了势力范围
当宝海最初对中方说,与其双方“纠缠于彼此难以取得一致的问题”,倒不如“将我们双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来寻求能使我们接近的东西”时,更多的还是一种套话。可是,在天津调查了十一天后,宝海开始真诚地如此呼吁了。
宝海觉得,无论越南最终归宿如何,中法之间应当保持和睦,并深化双边贸易交往。就个人立场而言,宝海乐于承认历史上越南确实是中国的藩属国,这个历史造成了现实中清越双方的特殊国与国关系。可是,法国与越南签署的一连串条约同样白纸黑字,不容也无法一笔抹杀。如果中方愿意正式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现有地位,作为补偿,法国可以在中方寻求的缓冲地带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具体方法为在中越边境地区划出一块缓冲区,作为中方的势力范围)。总之一句话:现在所议者为保中法两国之和局,通中法两国之懋迁而已。
李鸿章抓住了这个让步,希望能比照“欧西小国如比利时之类”,使越南成为中法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具体措置初步定为:越南割与法国的“西贡左近数省”,中方承认为法国所有。剩下的部分划为南北二境,分由法、清保护。“外人如有犯越北境者,中国出兵援之;犯越南境者,法国出兵援之。”
对于这个提议,宝海表示不能完全接受。虽然没有明说,但宝海最清楚,毕竟他所代表的法国是强势一方,所以没有必要作出太大的让步。如果按照李鸿章的方案办,法国就等于被排斥在了北部之外。而谋求红江的自由航行,并直接控制其至少一半河段,是法国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他又在李鸿章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案:坚持于红江的某个中间地段划界。其南由法国巡护,其北由中国巡护。这就大大压缩了李鸿章划出的分割范围。按照李鸿章的计划,是两分法占六省外的越南,但按宝海的计划,分给中国的只是北圻的一部分。
在北京城中的激进派们看来,无论是哪个方案都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越南本来就是大清的属国,何以要与法国人讨论分割方案?再者,红江以北本为中国经营已久的国防范围,光清剿土匪就去了好几趟了,还需要法国转让吗?何况还只是转让其中的一部分!法国凭什么落这个空头人情,又抢走越南这个属国的绝大部分领土?对此,李鸿章也有同感,但关键在于实力对比。国内的自强事业迟迟没有头绪,李鸿章自然不敢过分玩火。若抛开“藩属”这个名分,纯从中法实力对比讲,能控制红河以北地区做缓冲地带,已是中方的一个重大外交胜利。
若不乘此机会议定和约,恐日后更难收场。
在宝海也急于谋求和平解决的情况下,双方只用了两天的磋商时间,就在十月十七日(11月28日)闪电般初步定下草约三条:
(1)中国将驻北越的滇、桂军队自现驻地撤退回境,或离边境若干里之地驻扎。法国即照会总署,切实申明法国在这一地区无任何征服意图,亦无损碍越南主权之谋。
(2)法国切望自海口以达滇境通一河路,为商务起见,须使此河路直达华境,以便设立行栈埠头等。前有在蒙自设立通商口岸之说,今愿改保胜,中国当在保胜立关。洋货入关,照已开各口岸洋务运入内地章程办理。中国当使内地土货运往保胜能畅行无阻,如驱除盗贼之类。
(3)中法在滇桂界外与红河中间之地划界,界北归中国巡查保护,界南归法国巡查保护。
最后,双方还共同声明,“两国互相保证维持这种商定的边界线的现状,并且保证东京现有的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使它不遭受可能给它造成损害的任何外来侵犯”。
这三点协议非常值得玩味。第一点中方可谓全无损失,因为中方本来就没想过要霸占越南北部领土,现在以撤军回国换来法方声明,可谓划算,而且自动避免了冲突的风险。第二点则体现了李鸿章与曾纪泽的共同意见,以主动的开放促成双赢性的贸易发展,并在共同的贸易发展中增加互相依赖性,避免军事冲突。
至于最后一点,则是这次谈判最大的收获。它标志着大清国终于走出传统的天朝格局,学会了现代外交,并且,第一次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兼缓冲地带。这在19世纪是强国之间正常不过的行为。
接下来的程序是将草约送交总理衙门审批。这一等就是五天,在这五天内,“北京方面无任何回音”。宝海事后曾向巴黎汇报了他当时的心情:“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我承认这一点——似乎非常之长,因为天气日趋寒冷,白河也开始结冰,而我则处于进退维谷的地步,既害怕由于河道封冻而被阻在天津,又担心离开天津便不能同中国政府达成任何协议。”
恰在此时,宝海得到了一个新情报(其实是谣传),说中国的正规军已大举潜入河内地区,即将与法国部队发生冲突。心急如焚的宝海在十月二十二日(12月2日)下午三点开始的会晤中,希望中国部队能立即退出河内,以免双方的当地军方好战分子启衅。也只有中方先退兵,和议始能顺利通行。
对于这个呼吁,李鸿章当然最清楚,所谓“滇、粤各省派兵出境,原不过虚张声势,牵制法人,不使并占北圻,并非即欲与法人交战。”更何况事实上清军并未入河内,所以若能“于各军现驻处所酌退若干里,以示彼此愿保和好之意,俾法人得有转圜地步,于名实均无所损”。故而李鸿章向宝海承诺可以先撤兵。
宝海惊喜之余,进一步提出希望总理衙门能“声明中国国家并无开衅之意,万一此后中法将在越南者或因小故忿争,只作地方闹事办理,并不算两国失和”。
作为回报,他会致电巴黎外交部,声明中方已发出谕旨督促北圻地方华军北撤,希望外交部也约束法国在越南北部的武装力量不要挑衅华军。同时考虑到通讯时间差,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不幸发生中法之间的军事摩擦,则“应视为与两国国家无涉”。对此,李鸿章又很爽快地表示,今晚就能发出这个照会,并问宝海何时能发出那封电报。于是,宝海也投桃报李地表示,他同样当晚就能发出。为了表示诚意,他甚至还同意将这封电报的内容摘要转给中方一份存根。
就在这次会晤期间,忽然发生了一起小型地震,一个书架被震得来回摇晃。
地震过后,李鸿章微笑着问宝海:“公使刚才害怕吗?”正沉浸在成功感中的宝海立即回答道:“一点也不。在我们之间刚刚达成协议之后,我是完全镇静的。”
事实上宝海此时的心情非常愉快。
同样是在这次会面期间,宝海还被告知,总理衙门虽然不便于立即表态,但对于双方初步形成的草约表示支持。
谈到这一步,双方可谓皆大欢喜。临别之际,宝海甚至说:“中国办事尽如中堂爽快,再无难事了。”
这种友好空气延伸到十月二十八日(12月8日)下午三点钟的会晤上,宝海甚至文学化的追忆起往事来:“我初次来京进沽口时,蒙中堂饬令声炮相迓,我谒中堂致谢,有谓两国大炮永供迎送大员之用,断无打仗用处。今其言已验。我此次初抵天津时,时因越南一事,心中颇觉担忧;今事已大致办妥,明日乘船南去,胸次甚觉爽适。”对此,李鸿章表示,等来年开春越南问题彻底解决,宝大人回京过津门,你我再会晤时,当更觉欢快。明天宝大人南下,我无暇送行,但已经通知大沽炮台,再次鸣放礼炮,“以示中法和好之意”。
次日,宝海在礼炮声中南下,和他一起去上海的还有李鸿章派出的代表马建忠。他将与宝海在上海进一步敲定正式协议内容,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拿到法国大学博士学位的前留学生,现北洋智囊,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双方最终在12月20日成功签订了一个备忘录。
似乎已经大功告成。剩下的就是双方元首批准生效,变备忘录为正式和约了。
遗憾的是,草约也好,备忘录也罢,最终都没有变成正式条约。之所以如此,固然部分原因在于清王朝内部激进势力的反对声浪,但最主要的反对力量却是来自巴黎。
消逝的和平曙光
1883年2月21日(光绪九年正月十四),茹费理第二次组阁。他在东方问题上一贯持强硬姿态。他猛烈抨击了前任“软弱”的对华政策,认为“李宝协议”
是法国外交不折不扣的重大失败。实力超强的法国,凭什么和清国共同保护安南?又凭什么与清国同分北圻?最根本的一点,法国既然已经通过《第二次西贡条约》,确立了越南独立自主国家的地位,何以法越之间的问题要到北京协商?
又何以负责谈判的不是法国驻越南代表而是驻华公使?这不等于自打耳光吗?虽然李宝和谈得到了上一任外交部长的支持,但毕竟是上一任,现在既然换了新内阁,就要有新的东方政策。于是,新内阁决定,单方面推翻“李宝协议”,撤换驻华公使。
受此刺激,清廷在三月二十五日(5月1日)下旨,命李鸿章督办援越抗法事宜,南下节制粤桂滇三省防军。
李鸿章当然不想在和谈还未到最后关头之前就先摆出动武的姿态。他的幕僚与老部下们也不希望他远离经营多年的北洋。最后落实到军事层面,三月二十五日的上谕也是大有问题的,“广东距粤西边境数千里,粤西距云南边境又数千里,声气隔绝,消息难通,若徒受节制之虚名,转贻以互相推让之口实,诚恐误事不浅。”李鸿章的老部下周盛传更担心的是,“在朝廷之意,原以为非中堂前行不能挫折其气”,却没有考虑到法国无法用小恩小惠满足,军事上中方又缺乏实力。
万一有所顿挫,大清国可是连个善后的重臣也拿不出来了。“此则非为中堂一身计,正为天下计也。”
李鸿章也已看透,越南“自取灭亡,无从援救”。大清则“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李鸿章开始在上海拖延时间,终于在五月初三等来了转机,朝廷取消了李鸿章南下的任命,改命其北上,“速赴天津,仍回北洋大臣署任,筹备海防一切事宜。”
恰在此时,越南忽然传来了一个新的爆炸性消息:刘永福取得了第二次纸桥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