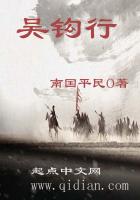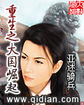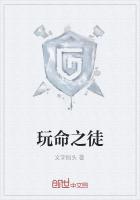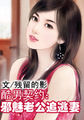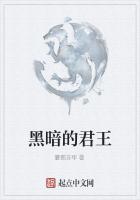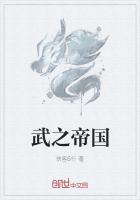结果适得其反,清廷的主战声浪因之更为高涨。清流派健将张佩纶与陈宝琛甚至联名上疏,要“水军直趋顺化、陆军夹攻河内”。这个建议虽未被采纳,但新一轮的主战高潮却就此掀起。正如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八月初七写给老部下潘鼎新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政府附和清议,总欲以兵威铃制,坚主滇边不准通商之说。而徐晓山(广西巡抚徐延旭——笔者注)旷代英雄,更陈请红江亦不准通商。
不知法越续约已议,准北圻归法兵保护,红江沿河准法人设营筑炮台。主人与客固大相判谬,将来何以结局耶?”
李鸿章也只有左支右绌,勉力为之。一面与德理固死缠滥斗;一面示意正在欧洲从事商务工作的招商局道员唐廷枢,从事两项工作:一、收集情报,二、制造舆论,以为腾挪。
结果是愈发令人心寒。
在欧洲,唐廷枢看到,“法之新闻纸,总以报复为心,并云中国不应管闲事。德国新闻纸故意煽之。惟英美报多有以法不宜与中国闹。至于意大利,本来无关进出,渠平日只见法国新报,总以渠占越南,系为通商起见,总以刘永福粤东强盗,总料中国断不发兵拒之。惟意大利心思,无不深恨法人。”所以唐廷枢由罗马动身时,“曾将法欺越之大略,授意新闻纸刻之,以动人心”。同时,利用当时法方对李鸿章可能被派往西南主持三省军务的恐慌,“广张声势,云中国既放傅相(指李鸿章——笔者注)为大帅,定必调集大兵,认真办理,断无苟且相就了事”。
但是,“人心”也好,“声势”也好,都是虚的,虚实要相生,才能济事,而大清偏偏最缺的就是这个“实”,所以唐廷枢最终也只能送给李鸿章如下一付药方:新闻纸已摇动人心,法国添兵未有定局,外部去电能了则了,此时傅相必要心软口硬,方好转机。中国硬,法国必软。所谓心软者,固不可随新公使所欲,亦不可坚心拒之。在我等生长于中华,何尝不想傅相大兵到河内,将法兵驱逐出境,以为中国壮气?无如心有所惧者,华兵难以敌法,即使众能胜寡,渠已先占地势,筑了炮台,恐枪不能敌炮。若全粤之兵兼傅相洋枪队尽往东京,法人既有铁甲兵船,保无分兵攻取羊城,以使我首尾难以兼顾?所以弟用心软二字者,系指不可激成打仗之局耳。转瞬戈理拔(即孤拔——笔者注)可到海防,水陆并进,东京定必为渠所有,滇粤之兵,未必能以取胜。傅相练军,此时尚在申江,既不敢航海而进,必取道西江,如是则东京之援,恐鞭长不及矣。噫!使中国早兴铁路,何至今日调兵有如此之难哉?是此事无论和与战,一经大局定妥,务必求傅相奏请招商开办铁路,方能立富强之基也。
可惜大清国的精英们,平时只晓得反对修铁路,建电报,此时倒逞起了英雄好汉。大谈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惨败,以为软柿子好捏,却从不曾认真想过当年德意志何以能胜法兰西,自然也就没人去听唐道员的肺腑之言了。
但该说的话,唐廷枢还是要说,因为至少还有一个听众:李鸿章。
所以唐廷枢又说,“弟之所忧者仍有三焉:夫法人向称强国,虽有德国之败,不数年间已将巨款清还,巴黎焕然一新,今日骑上虎背,焉肯自己下马?若中国不格外将就,必不容易了结,其一;法原系王主之国,今变民主之国,人心尚未大定,国中仍恩旧制者颇多,其今日骂外部之人,多非有心帮中国者,乃欲复旧制之人也。今之大臣,欲久享其禄,以为非开疆辟土无以坚人心,所以连年有都尔斯(即突尼斯——笔者注)、马地加时格(即马达加斯加——笔者注)、越南之军事。前者都尔斯已为渠所得,连日电报又云法兵已破马地加时格京城。有此二胜,渠心更觉高兴可知,其二;此时外部虽不敢开口加饷增兵,但渠料所去五千之众已足敷衍。若中国合越攻之,渠再请添兵未迟,所以事不易了者,其三;且下月初间即散议院,又需九、十月方能会议,其六、七、八月军事,任由外、兵部去办,所需兵饷,亦任渠向别款挪移,将来得胜,无难添款拔还。闻都尔斯初议亦是五百万法郎,今竟用至一万万,而绅院亦不拒之,是其明证。”
“总之,法人做事从不肯认错”,强弱相形,大清也只有当忍则忍,知耻而后勇,去追赶列强。
但这些话终究也只能在李唐之间说。国内舆论的主战声浪日趋高涨。攻击的焦点也日趋集中的李鸿章的身上。德理固也越逼越紧。法方开出的新要求是:“自沿海某处起至红江上游之保胜止,就纬线之二十一度及二十二度之间,定一界限”,而且这个界限并不是政治权利的分界,而是通商分界。界南自然是归法国占据,并施其权力。但界北却不允许中国占据,也不许中国施其权力。而中国付出的却很多:放弃越南,通商云南。
李鸿章知事不可为,但又不敢断然向德理固掀翻底牌,怕与前段谈判落差太大,造成中法彻底决裂。也只好借口已奉旨回津,暗示德理固不妨与之回津叙谈,或干脆入京与总理衙门直接商谈,或由曾候与法外部商议。
对此,法方一片震怒。
在法国人的思维中,李鸿章既已承诺有全权,现在又推三推四。实则是总理衙门,李鸿章与曾纪泽在联合愚弄法国。“故与李交涉则推曾,向曾交涉则推李,向总署交涉则推二人。”(德理固语)他们从不曾换位思考过李鸿章、曾纪泽与总理衙门的难处。
德理固遂于九月(10月)离华,重回日本做大使去了。
条约没签,法国代表倒气跑了。李鸿章鼻子一动,俨然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火药味。举目四望,却还是四个字:无路可退。
天兵入越
外交陷入僵局,双方在军事领域的较量却日趋激烈。
东线黄桂兰军以谅山为基地,稳步前进,已控制北宁。西线刘永福军在唐景崧的激励下,也已进占山西。从军事地理上讲,清军的选点不错。北宁、山西一带是北越重要的粮产区,南如河内,北如谅山,皆仰给于该区。在没有铁路,交通原始的北越,就地取粮对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有重大意义。再者,山西、北宁,互为犄角,虎视河内,控制着红河水道,立使法军如坐针毡。反之,法军若要继续北上,也必须过这把门二虎之关。这就注定了中法双方无不对这一地区取势在必得之心。
1883年11月底,清廷发布了划分东西战场的指示。考虑到西南地区特殊的地形,清廷决定以云南、广西为基地,兵分两路进兵北越。这样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东西两个战场。西战场由署理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重点经营山西。东战场则由新任命的广西巡抚徐延旭负责,重点经营北宁。
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壮族。值太平天国内战之际,以秀才办团练,积军功至封疆大吏,可谓大清国的一大传奇老将。
如果说岑毓英尚可谓沙场老将,那徐延旭就有问题了。
徐延旭,字晓山,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1860年)中进士,此后长期任职于西南地区。光绪元年(1875年),曾奉命带兵入越追剿私通法国的流窜“巨匪”
黄崇英,一战成擒,遂得“知兵”之名。他又利用接待越南贡使的机会,搜集整理了大批关于越南“地势民风,政教禁令”以及中越边境卡隘道路情形的资料,编辑成多种小册子,一时在智识阶层中广为流传。今天看来,他这些小册子也就是个普及读本的水平,中间还不乏硬伤性错误,可在当年,却使他成了大清国的头号越南事务专家。
更有机缘的是,徐延旭一向乐于助人,得过他救济的读书人很多,其中就包括了张之洞的姐夫鹿传霖。于是乎,张佩纶带头,陈宝琛、张之洞助势,徐延旭的大名终于直达天听。
既知兵,又熟悉越南事务,这样的官员不用,还用谁?
朝廷遂于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破格擢升徐延旭为广西布政使。继于五月十九日发旨给广西巡抚倪文蔚:“该藩司(徐延旭——笔者注)到任后,倘边防紧急,即着派令出关督办,以资得力。”奉旨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徐延旭就这样成了驻越清军的实际统帅。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更“准其专折奏事”,真是空前的恩宠。他们显然忘了,法军不同于土寇;徐大人也并不懂现代战争。
这还不算,为了让徐延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内阁学士周德润、廖寿恒,詹事府詹事洪钧等清流派健将们的努力下,先后将广西提督冯子材与广西巡抚倪文蔚请走。因为前者曾于同治十年参劾过时任太平知府的徐延旭,而后者在张佩纶看来:“倪文蔚为人长于吏事,而战阵非所习、洋务非所习、边情非所习,殆吏才非将才也。若量移内地,而别简知兵大员巡抚广西,庶中原得一贤抚,沿疆得一边材,亦两全之道也。”话说得还算客气。
到周德润与洪钧的奏折里倪文蔚就成了“才略素短”和“局量稍隘”了。
冯子材一看形势不妙,遂抢先于六月托病辞去广西提督职务(遗缺由黄桂兰接任)。倪文蔚则于九月初九日调补广东巡抚,徐延旭补授广西巡抚。
事后看来,倪文蔚固然不知兵,但徐延旭也好不哪去。倒是冯子材因祸得福,后文还会有交代。
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再拨回1883年的年末。法军进攻在即,徐延旭虽已进驻谅山,但以种种借口不再前进,而将北宁守备扔给了本就不和的黄桂兰与赵沃。
作为淮军宿将的黄桂兰,其勇敢无人质疑,战前也表示:“与之开仗,决其胜负,则提督等效力疆场,是其分也,誓不与彼族共地同生。”但是此君知识结构严重老化,已不足应付他那个时代的现代化战争。至于广西候补道赵沃,同样是个现代化战争的门外汉,只是依仗徐延旭的信任,和此前剿匪的军功,才得以与黄桂兰分任右路、左路统领。一开始黄桂兰率左路军驻北宁,赵沃率右路军驻太原,还算相安无事,自1883年12月初集中驻守北宁之后,摩擦不断,徐延旭不闻不问,大局遂为之败坏。西线的岑毓英则尚未起程出关,山西的防务实际上由刘永福与唐景崧负责。
这就形成了清军主力(三十余营桂军,万余人,由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指挥)驻北宁;刘永福与唐景崧率3000黑旗军,另加2000清军(滇军三营,桂军两营)、2000越军(越北圻统智黄佐炎率领)驻山西的局面。两军互为犄角,瞰制河内,成了法军的心腹大患。
法方策略
“李德谈判”破裂之后,法军于1883年10月25日成立了以海军少将孤拔为总司令的远征军,统一指挥北圻的法军。他们的任务是武力夺取北圻,强行驱逐黑旗军与驻越清军。
孤拔兵力有限,至12月初仅有9000人,所能集中的机动打击力量只有6000人,不可能同时攻取山西和北宁。但若能集中于一个战场,又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要知道,黑旗军迄至怀德、丹凤作战前尚未与人数超过1000的法军打过正规战。更值得注意的是,法军此次派一个海军少将统一指挥作战,正是要充分发挥两军种的密切协同作战。海军将提供适于内河的炮舰与运输船,支援陆军,作逐个击破的进攻。
既是逐个击破,就要慎重确定先后次序。河内、山西与北宁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钝角等腰三角形,法军控制的河内就是“大角”,而清军则挂在“大边”的两端上。考虑到越南复杂的地形与落后的交通,两股清军想实现相互间的直接增援是非常困难的,较可行的增援方法便是围魏救赵。即当处于内线的法军攻击其中一股清军时,另一股清军便趁机偷袭河内。这一点,法军不得不防。
再进一步讲,从山西与北宁到河内的距离,均为约40公里。但二者一在红河南岸,一在红河北岸。这就决定了法军攻击的先后顺序是先山西后北宁。为什么呢?因为1200米宽的红河是一个巨大的地障。若先攻北宁,法军就要连续渡过红河与新河(今急流河),这不仅构成前进中的障碍,万一失利又将变成后退中的陷阱。若山西方向的黑旗军再乘虚偷袭河内,法军就会进退失据,甚至全军尽墨。
相反,若先攻山西的黑旗军,北宁的清军就必须连续跨越上述两条大河,才能攻击河内。以清军的组织水平和随军工程力量,这是不可想象的。渡河本身已很困难,至于将清军本就不多的重武器运过红河就更困难。更何况法军早在红河南岸修好了一座坚固的碉堡,“内装一门120毫米大炮,该碉堡不仅位置居高临下,而且坐落在来自北宁的各条公路的交叉点上。因此,敌人必须首先攻占这座工事,但他们尚无这样的力量去冒风险,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没有必要担心敌人会从北宁方面发动任何攻击。”
而法军顺红河西攻山西,正好充分发挥其水陆联合打击力量的优势。具体到对山西的攻略,孤拔的计划是:绕开守军苦心经营的东城正面防线。利用法国的水军优势,顺红河迂回守军右翼,先摧毁城东北的扶沙要塞,再攻克城北的堤岸阵地,如此一路将主力推进到城西,切断守军退路,聚而歼之。如果守军以攻对攻,也切断法军的退路,后者也不担心,因为他们真正的交通线并不在陆上,而是红河。
但先攻山西也有很多困难。当时可供法国军舰从河内到山西的水道只有一条红河,而红河在山西与河内之间“有五个河套”,“在每个河套处形成了沙滩和流沙,使航道完全堵塞。从9月份起,吃水线不会超过一点五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