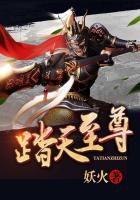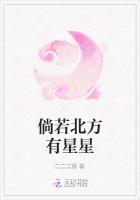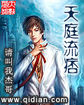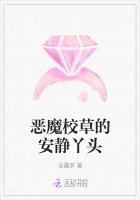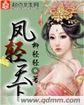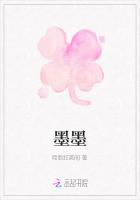占领山西后,法军进行了全面的物资搜索,据孤拔递交海军部的公文中显示,法军共计缴获:金银与钱币:6262枚安南银元,5枚金币,66块大银锭,1381根银条,264根小银条,7块小银锭,8000串铜钱,2只装满账册票据的箱子。
其他物品:200件无艺术价值的铜制品(如香炉、高脚杯、烛台等),350件茶杯、茶托、烛台等锡制品,两口精致大钟,262块铅锭,18块锡板,100块铸铁板,1个中国烧磁花瓶,两张描金漆安南桌子,1张床。
生活必需品:650万公升稻谷,6万升大米,1万升粗盐,10筐碳。
武器:7门青铜膛线炮,2门青铜滑膛大炮,7门12厘米青铜滑膛炮,1门8厘米青铜滑膛炮,46门青铜小炮,39门大口径铸铁炮,88支守城用枪或轻型长炮,371支步枪。
弹药:15万发雷明顿枪弹,1万发温彻斯特连珠枪弹,2700发供1867年式步枪用枪弹,2000发1866年式步枪用枪弹,1500发左轮手枪弹,1500公斤安南火药,两箱英制狩猎用火药,10万枚雷管。
虽然物资上收获颇丰,但法军还是连夜上演了山西之战的最后一幕:大屠杀。事见英国战地记者登在《泰晤士报》上的采访。对此,法国人自己也有记录。
如法人迪克·德·龙莱的《在东京(1883-1885年)——逸事叙述》中,就曾记有:“阿尔及利亚土着步兵和其他士兵对该城进行了六小时的抢劫,杀死了二百名安南人和躲在屋里面的黑旗军。此外,俘虏统统被枪毙,一个也不留。每次枪毙四至六个,有时更多些。他们被带到河边,枪响人倒,河水即把他们冲走。”
整个会战期间,北宁清军按兵不动,原定由云南方向派来的援军也迟迟未能赶到前线。
何以如此迟缓?且听岑毓英的夫子自道:“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兴化,陆路一千一百余里;即由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数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
一句话:缺少现代化的交通手段,相反,“洋人用兵,持有电线数万里,军情瞬息可达;又有轮船载运粮饷军装,数十万斤之重,数日可至,数其军火充裕,每战辄数昼夜不停。官军文报既多迟滞,挽运更属艰难。以滇、粤比较,则滇军尤难。”岑毓英到保胜将及十日,“而各营弃勇到者未及一半,军火军装亦赶运不及”。
后来清政府还想组建一个统一指挥东西战场的前敌机构,由岑毓英负责。可岑代理总督却不敢接招,原因也很简单:缺乏现代化的通讯手段。机构很容易建立,事实上的统一指挥却不可能,可天大的责任却要他一个人负。这个黑锅,岑毓英可不想,更不敢去背。
打来打去,最倒霉的还是越南老百姓。法军为防黑旗军死灰复燃,所以严禁土民拥有兵器。但法军自身兵力有限,所能控御者,实在只是少数几个大城池,偶尔才对城外进行扫荡或排查。这就使红河地区出现了大片的真空地带,填补这个真空的力量便是各路盗匪。土民手无寸铁,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也去做盗匪,要么便是被盗匪焚掠枪杀。否则也就只有“跟着强者走”,寻求庇护。
谁是能克制盗匪的强者?一曰官府,一曰法军。可这两强现在恰恰处于严重对立的位置上。结果,“附法者受越官之残害,不附法者受法兵之杀伤,进退维谷,岂不哀哉!”
李鸿章的误算
法军攻克山西的消息一经传出,巴黎与北京立时都陷入了巨大的震荡中。所不同的是。法国人是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居然出现了“山西的辉煌遮掩了色当的灰暗”的新闻报道。想当年普法色当一战,法国三军尽墨,皇帝被虏,真是狼狈何其。世界第一陆军强国的宝座也随之丧失。这个“灰暗”是山西的“辉煌”所能遮掩的吗?巴黎政坛的轻浮风气由此可见,茹费理内阁的悲剧结局也从此埋下伏笔。
相反,清廷方面则是一片手忙脚乱。战前无比乐观的清廷众臣终于意识到他们严重错估了敌我实力对比,于事很多人提出撤离北宁等关外据点,撤军回国布防,争取外交解决。
但是战前主和最坚的李鸿章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在李鸿章看来,当此黑旗新败之时议和,大清必然损失惨重,所谓英、德的介入调停全无实效,因为政治是实力的游戏。
相反,北宁是大清长期经营的国防重镇,黄桂兰是淮军老将,足堪一战。从时间上讲,冬天快到了,到时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要暂停。只要能拖到冬天,法军劳师远征无果,我方就可以选择较佳机会主动与法方恢复和谈,争取较佳的结局。现在放弃北宁,岂非功亏一篑?
当然,李鸿章也看到了潜在的危险。
第一,“倪、徐二君,实不知兵,不知洋务大局,其言实不可信。”
第二,双方战斗力存在差距。
从数量上说,法军“新旧合计一万数千人”,清军则“滇、桂两军及刘团合计则将三万人”,法军实不占上风。李鸿章坚信,如果只是在“陆路交战,似足以相敌”。问题出在“法所据之海防、南定、河内、海阳、山西各处,河套环绕,利用舟师。法人长于水战,又多浅水轮船,水陆相依,最为稳固。”相比之下,清军“仅赖营垒炮台,无得力兵船,无善用水雷”,无法有效封锁水路,所以难以抵挡法军的水陆夹攻。这就使清军的数量优势打了折扣。山西的失守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李鸿章建议立即进行塞河工程,防止法军故伎重演。
从装备上讲,法军人手一杆后膛枪,“操练熟悉,弹药备齐,兼有轻炮队相辅而行。离水近处,兵轮大炮又可夹击。此西洋用兵定法也”。清军“滇桂各营后膛枪既少,或有枪而缺子弹,操练又素未讲求,轻重炮位更少,徒以肉搏梃击取胜,不仅晓山(徐延旭——笔者注)于此事隔膜。即彦卿(岑毓英——笔者注)久统滇军剿回匪,亦只惯用内地枪炮,于洋器究少阅历”。
当然,清军也有优势,那就是复杂的地形。具体说就是多山(所幸兴化、宣光、太原一带,跬步皆山),所以利于伏击,而且可以“人自为战”,抵消法军的组织优势。只要能有效“塞河拦阻”,“彼仅以陆队攻我台垒,坚忍苦守,未必骤下。即一处被陷,亦未必处处瓦解也”。
只要军事上能“拖”,外交上就能“转”。如是始可体面收场,化呆着为活棋。
那么李中堂分析的是对还是错呢?
事实证明,李中堂对敌我优劣的分析,尤其对法军水陆协同作战的敏锐担忧,是极其有先见之明的。所以他才抓住了核心问题:河防。可惜终究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李鸿章还是犯了严重错误,那就是他严重低估了法国陆军的战斗力。
说来,李鸿章对西洋海军的威胁和强大始终有清晰准确的认识,但他对西洋陆军的认识却未免太拘泥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经验,却忽略了两个问题:
一、那些由冒险家、雇佣兵、流浪汉组成的助剿洋枪队,并不能代表欧洲一流精兵的水平;
二、从太平天国战争到现在,欧洲军队又有了新的发展,李鸿章的认识并不深刻。
而且,作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对于遥远的两广、云南地区终究不很了解。
他虽然知道这些地区的部队装备落后,却不知道战斗素质更差。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法军多兵种密切协同的陆战威力,更将看到大部分清军士兵连最基本的瞄准方法都不太熟悉,往往法军还未进入射程就胡乱放枪,徒然浪费弹药,且暴露位置。作战时又往往“聚成一处,若法用连珠炮攻击,所伤必多。”反而不如长期在实战中得到锻炼的黑旗军战斗素质高!这却是嘲笑黑旗军是“土寇伎俩”的李中堂所没有料到的。
更可悲的是,李鸿章的主战得到采纳,但关键性的建议却一条也没付诸实施。徐延旭还是受重用,黄桂兰与赵沃还是闹矛盾。塞河虽然批准,但经费直到最后也没落实,工程自然也就始终没有实际进行。事实上,就算李的“塞河”
构想实现,在一场单纯的陆地较量中。北宁也是守不住的。只不过中方能争取更多的时间,予法军更大的杀伤罢了。可事实呢?由于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北宁守军的河防工事到战前也未落实。这就为北宁之战预先填塞了悲剧与闹剧的双重色调。
闹剧般的北宁之战
从“李德谈判”破裂,到法军攻击北宁,历史给了大清国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徐延旭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倒没闲着。自出关以来,老徐“万苦千辛,经年筹运”各种物资支援前线,“经年之久,人负马驮,一概运赴北宁,交存两统领,不令缺乏。徐帅一腔愤恨,不得一战,灭此朝食。”
张树声也承认,“滇桂边军整旅入越,徐藩司延旭愤法侵越,慷慨布置,有灭此朝食之志;于越将刘永福维持调护,不迭余力;唐主事景崧并入为谋主,调遣官军。”
能说徐大人不爱国吗?能说他不忠于职守吗?要是这点能耐都没有,就凭那几本小册子,糊弄一般人还成,要让张佩纶、张之洞与陈宝琛为他摇旗呐喊,那可就难于上青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