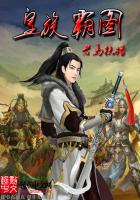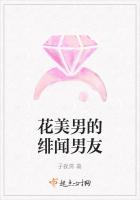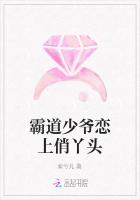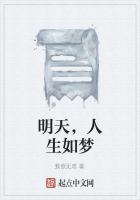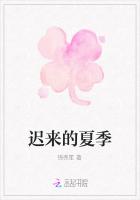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因为主要发生在重工业领域,所以直接促成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武器装备的急剧变革。这样一来,教育体系在继承其人文传统的基础上,第一次可以直接贡献于富国强兵与国际竞争。同时,又由于新的工商业手段释放出了更大的财富与力量,所以新式政府如果有心,就可以推广全民教育。这就产生了一条全新的强国之路。而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正是得此风气之先者。
君不见,“早在18世纪末德国就确立了所有6-13周岁的儿童都应接受普通教育的原则(尽管现实并非如此)。英国则直到19世纪后期才引入这一原则。”
此外,德意志的教育体制还为国民“提供了从小学到职业学校,从工艺学院到大学的求学机会。”其中,“大学对科研相当重视,物理、化学及数学方向的研究气愤尤为浓厚。”“时至1870年,一批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已经在克虏伯和博库默尔、维赖恩这样的大型钢铁企业中任职。鲁尔的大企业多数已聘任化学家对生产投入进行分析,并进行质量管理,此举又领先于其他国家很多年。桥梁、机械工程、钢铁制造方面的德文教科书大量涌现,随处可见。正如俾斯麦所言:‘有学校的国家才有未来。’”(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当完善的教育体制与关税同盟、战略性的铁路网、德意志独特的工业技术传统、庞大的商会组织结合在一起时,就“就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德国式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使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诸邦占据了时代的先机,这个先机不仅赋予了统一运动本身以强大的动力,更使得统一后的新德国飞速发展,迅速成为欧陆第一强国。
震撼全球的军事革命
当然,单纯的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诚如第一章中业已提及的那样,普鲁士地处中欧,其西面的法兰西,东面的俄罗斯,南面的奥地利,都是欧洲传统的陆军强国。而且这三个国家中的两个(法国与俄罗斯)都垂涎于欧洲霸权。奥地利虽然目的有限,却想方设法限制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的影响力。法国更是自黎塞留以来就以阻挠德意志统一为国策。就算是有了俾斯麦高明的外交战略,也只能是为普鲁士提供避免多线作战的环境。如果普鲁士连单打独斗获胜的军事实力都没有,俾斯麦也不能撒豆成兵。当普奥开战时,俾斯麦怀揣毒药走上前线,正说明他对于军事胜利本身是缺乏足够信心的,而历史证明俾斯麦多虑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已经在军事改革的道路上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
这个领先既包括了装备与新战法的领先,也包括了制度建设的领先。这个新制度就是日后影响深远的参谋总部制度。
普鲁士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却能够相继击败丹麦、奥地利与当时世界第一陆军强国法兰西,确实震惊世界。其制胜的关键就在于参谋总部制度。
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之前,士兵的战斗力主要来自于经验积累。但参谋本部第一次通过训练与教育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也可以说参谋总部是现代教育在军事领域的大放异彩。
完善的参谋总部制度同时具备了下述四种特性:首先,参谋本部是一个研究机构,或说学术机构。它直接管理陆军大学,并以战史编纂为头号任务。它将军界的精英聚集起来,广泛搜集本国和各军事强国的兵要地志资料和各种军事情报及与军事有关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军事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中对军事史的研究被规定为参谋本部的核心职责之一。
其次,它又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将前述研究成果转化为操典和教材,通过军校和军队,切实地贯彻到基层。同时他不仅从基层遴选精英,还周期性的将总部的精英派到基层,形成互动。并且还通过外派武官制度,使得军界精英得以到国外尤其是假想敌国进行长期的体验和观察,既收集相关信息,又做到从思维方式到文化心理的知己知彼。
再次,它又是一个决策机构。负责选定假想敌,并制定战争计划。
最后,它还是战时的指挥机构。
具体到德意志统一战争时期,普鲁士的参谋总部又得到了一个优秀的参谋总长——毛奇。这位被后人称为“火车将军”的德意志名将,早在德意志拥有第一条铁路之前就关注到这个新事物的革命性意义。他巧妙的把新兵役制度、电报、铁路、参谋总部、知识型的军官团结合在了一起,不仅铸造了锋利的德意志利剑,而且形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军事变革浪潮。
陆权的复兴
正是靠了前述各种合力的效果,最终促成了德意志统一这一奇迹性历史事件的完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说陆权文明与海权文明都可从蒸汽动力的陆权化中获利,但后者终究无法把铁路修到海上去,不然那就不叫铁路了。这样一来,陆权文明的收益就压倒了海权文明,而且空间越大的陆权国家,所能施放的能量也越大。如此你有火轮船,日行千里;我有火轮车,也日行千里。你要由海上陆,我却能以逸待劳。这就有了自强的基础,自强的同时求富,富有余力,我可就要由陆向海,做两强兼备的超级大国了!
所以当一个外国记者问俾斯麦,若某一个海军强国以其超强的海上力量,在德国海岸作两栖打击,德国如何措置时。俾斯麦才会说:让当地警察,把他们统统抓起来。这份自信,大清国就没有。但普法战争的历史经验却正是它急需的!
如果说,无敌舰队的覆灭,将海权兴起的神秘,像历史的耳语般,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那么普法战争的结束,同样将另一个神秘,从一个大洲传向另一个大洲。那就是:沉寂已久的陆权文明,终于又要复兴了!
这就是普法战争在战略学层面上的历史意义。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清国自强运动可能成功的历史枢机。
有了这个纵深认识,我们就该明白,1870年的普法战争实际上预示了如下四大时代命题:
第一,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战略资源,可以直接贡献于富国强兵,而且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性日趋增高。
第二,在一个多元化、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理性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必不可少。
第三,自海权的全球崛起以来,陆权文明第一次面临着全面复兴的历史机遇。
第四,电报、铁路与参谋本部制度的结合构成了新的军事革命风潮。
以普法战争而言,表面上交战双方力量大体相当,各有优劣。实则在两国战争指导层的脑海中,构划的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战争景象。结果,参谋本部战胜了小拿破仑;铁路、电报加外线式战略击垮了法兰西。这里,电报加铁路,好似鲲鹏的双翼,而参谋本部就是心脏与大脑。
在这个背景下,李鸿章在同一年出任直隶总督,也就多了一层不可言说的历史机遇感。
从最直接的层面上讲,李鸿章之所以在同治九年被从内战场上调任直隶总督,是为了处理中法之间因为天津教案引发的外事危机。法方姿态一度极其强硬,李鸿章既要进行外交斡旋,还要进行备战。可是,普法战争彻底粉碎了法方的强硬立场。从这一点上讲,李鸿章与大清国都是这场战争的间接受益者。
这四大时代命题给大清国带来了特殊机遇。
大清国不正是一个大陆国家吗?中国不是有着悠久的重视教育的传统吗?或许,唯一的遗憾就在于自秦汉大一统之后,中国经历了太长久的一超独强经历,从而形成了天朝无外交的不利现实。但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震撼后,大清国不是也开始翻译《万国公法》,开始引进西洋技术了吗?李中堂不更是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一贯以其现实主义外交观令洋人刮目相看吗?
何以历史最终留给后人的却不是一部成功的传奇,反而是一曲悲凉的挽歌?
个中曲折,却正要从中日两国近代的是非恩怨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