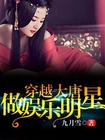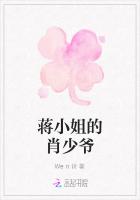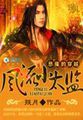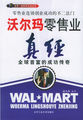清军部署
八月十二日(9月11日),左宝贵部侦察部队,在玄武门东北80里处,大同江上游,发现了朔宁支队。左宝贵立调三营兵力出城,主动进攻,双方夹江互轰,激战正烈,左宝贵却忽然收到叶志超的羽箭急令,命他立即回城,依托工事取守势御敌。
原来,在平壤的东南方向,清军侦察兵也发现了大队日军。叶志超坚信东南方向的日军是主力,但玄武门的重要性他也很清楚。所以他不许左宝贵轻易出城野战,而命他坚守工事,正是希望左宝贵能守牢后门。然后他集中战斗力最强的盛、毅二军于他心目中的主战场:平壤东南大同江东岸,一举击败来袭日军!
只要能消灭南线日军,平壤不就化险为夷了吗?老中堂不就有了和日本人议和的筹码了吗?
这个想法本身并不错,但问题是,玄武门一定能守住吗?大同江东岸一定是主战场吗?
可历史已不给叶志超反思的时间。
八月十三日(9月12日),双方的斥候与小队开始小规模交火,遥远的天津城内的李鸿章念念不忘的还是军事纪律。当天,李鸿章致电卫汝贵,首先转达了皇上对卫军的严重不满。然后痛心疾首地说:“现闻盛军在平壤,兵勇不服,惊闹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左、马、丰三统将,忠勇协力,上下一心,独汝所部,狼狈至此!远近传说,骇人听闻。汝临行时,吾再三申诚,乃不自检束,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吾颜面声名何在?电到后,切勿自回护,密商叶总统,应如何说法安抚军心,顾全大局,或将该军暂令孙显寅帮统,以孚众望,而期努力效命,立候电复。”
但历史同样不再给卫汝贵时间。
八月十四日(9月13日),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布置防务,划分各军防区。
叶志超首先宣读了李鸿章的指示:“倭情诡诈,必须严防。”然后会商决定:叶志超驻平壤城中调度全军。叶志超所部芦榆防军2100人守平壤城西。马玉昆部毅军,卫汝贵部盛军一营约2500人守平壤城东及大同江东岸。卫汝贵部盛军,丰升阿部盛军约7000人守平壤城南至西南。左宝贵部奉军三营(1500人,守玄武门与牡丹台),江自康仁字二营(1400人,守箕子陵)共计约2900人守平壤城北。并规定:“查南门外(大同)江南,马总统(玉昆)与盛军一营共扎浮桥;倘有缓急,马总统一营、聂统领(桂林)一营可派队速令应援。自大西门至盛军孙镇(显寅)与马总统营处交界方向,倘有缓急,可使盛军应援。北门外山上,江统领(自康)驻两营;倘有缓急,可使丰总统(升阿)队速援之。从大西门至七星门(静海门)其间,芦榆及山海关戍兵、即时正定练军及武毅军古北口练军务营防守之,倘有缓急,盛军卫总统(汝贵)队可速援之。不论何军何营,倘有疏失,一经查出,立照军法惩办!”
如此一来,在大同江东岸战场,负责“自杀性进攻”的大岛第九混合旅约4000人,面对的是马玉昆部毅军加卫汝贵部盛军一营共约2500人。
在平壤西南战场,野津第五师团约5400人对聂桂林部庐榆防军,卫汝贵部盛军主力,加丰升阿部盛军约7000人。
在最关键的平壤北战场,立见尚文“朔宁支队”与佐藤正“元山支队”约7800人,对左宝贵部奉军三营、江自康仁字二营共约2900人。
这样,在决定性的北部防线,日军占据了2.6倍的优势。考虑到其中直接用于玄武门与牡丹台防守者仅1500人,日军占据的优势也就更大。至于这个优势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立显。
天上掉下了馅饼
同样是十四日这天,为便于指挥前线作战,明治天皇率参谋总长(有栖亲王),御林军总司令(小松亲王),内阁首相(伊藤博文)等军政要员从东京出发,将战时大本营迁往广岛。以作御驾亲征之势。同日,山县有朋、大岛久直(陆军少将,第六旅团司令官)起程前往朝鲜前线,很显然,平壤的战斗远不是终结,而只是更大的激战的序幕。
同日午夜,桦山与伊东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为配合陆军对平壤的攻略,联合舰队将由仁川北移大同江口南侧的渔隐洞,并以此为临时根据地,伺机攻袭北洋水师,夺取制海权。至少也要保证大同江的安全,掩护陆军对平壤的攻击。
说来悲哀,还是八月十四这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希望总署能代表“请旨敕令前敌各营,均归叶志超节制调遣,以一事权”。这就说明皇上当初的任命,至今还没产生实际效果。
次日(八月十五,9月14日)上午,外出侦察敌情的吉野与高千穗二舰自威海卫归来,它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北洋水师主力已不在威港之中。
同时,蔚岛、仁川方面的侦察舰则相继传来“未发现异常现象”的平安汇报。
伊东遂于午后四时下令:留下第二游击队与八重山号泊守仁川,掩护陆军登陆。
自己则亲率本队与第一、第三游击队,及特务舰、运输船等,北上大同江,巡歼北洋舰队主力!
可是,伊东却怎么也巡不到北洋水师的踪影。
似乎已是山穷水尽。但很快,转机就来了。只是这转机不来自海军,却来自朝鲜的陆军。
原来,就在十四日这天的上午,北上平壤途中的第五师团野津道贯部,渡大同江时,“无意”中俘获了一艘从大同江下游驶来的中国商船。参谋长福岛安正率兵登船检查,搜出一封密信。写信人是清军大孤山守将,收信人是写信人的好朋友——平壤守将丰升阿。前者告诉后者,“(上峰)虑平壤华兵乏,方今以舶船数艘,自大沽、旅顺送兵鸭绿江岸,且以运粮军舰护卫之。兵达平壤当非远也”。
这位守将显然很够意思,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通知自己的好友,以稍缓对方的愁情。可惜,他的这个做法太无纪律性。借助商船捎信又不免太无保密意识。
反而让福岛安正捡了个大便宜。
对日军来说,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联合舰队终于不用为北洋舰队的动向而焦头烂额了!
起锚
就在平壤激战的前夜,北洋水师也走到了它命运的十字路口。
如前所述,日军业已挥师北上,万一平壤不守,那战火可就要烧到咱大清朝的龙兴之地了。军情似火,北洋水师还能再等吗?
命令终于传来。李鸿章令镇守旅大的刘盛休部铭军4000人,火速乘轮船招商局的五艘轮船,海运增援,巩固平壤守军的后路。而丁汝昌所接受的命令,正是为铭军护航,兼运一批军火粮饷去大东沟。
黄龙战旗再次扬起,汽笛迎风长鸣。
这一天,是光绪二十年的八月十六日,西历1894年的9月15日。当日上午,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由威海卫抵达大连湾。午夜,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大小舰艇十八艘,护送分乘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五艘运兵船的铭军,直奔大东沟进发。
这支曾经虎视亚东的舰队,就这样在西林巴图鲁丁提督汝昌的率领下,在一帮小留洋巴图鲁们的驾御下,驶出了军港,踏上了征程。
据美籍洋员马吉芬回忆,“鉴于七月二十五日在朝鲜半岛海面,济远和广乙被袭击的教训,各舰皆卸掉舢板,只留六桨小艇一只。意在表示军舰的命运即船员的命运,一旦毁坏沉没,岂能侥幸求生或借小船逃跑,或忍受投降的屈辱?济远的小船忽被击碎而燃烧,虽尽力扑救但已成废物。二铁甲舰将保护三十点五厘米(十二寸二)克炮的厚一寸、直径三十余寸的重大钢盾也都卸去。因为如果敌人的榴弹由露炮塔上擦过,碰上炮盾,就会将其打穿而于盾内爆炸,盾内上下四周,就将有充满碎片硝烟的危险。据闻丰岛之役,日本军舰从远距离发射一枚榴弹,击中济远炮盾顶端的后部,立即爆炸。炮弹头部虽然穿透炮盾而飞走,但残余碎片在盾内四处飞散,炮长以下七人死亡,十四人负伤,盾内炮兵无一幸免。
当时如果事先将炮盾去掉,该榴弹必然平安飞去。因此证明二铁甲舰采取的措施甚为得当。其他不必须的木器、索链及玻璃之类,也都移置别处。把舰桥的翼端切断,把所有的拉窗梯子都卸掉,铁索、索梯也尽可能都取走。只有安在舰首舰尾的六寸炮炮盾,为了防止重炮发射时,保护炮手免受空气的冲击而保存未动。
舰队各舰都涂上不易辨别的深灰色,钓床用以保护速射炮手。上部构造的重要部分,四周都堆起砂袋,宽三尺、高四尺左右,在其内侧,并排放着六寸炮用的百磅实弹、榴弹数十个,以便迅速射击。装煤的袋子也配置在重要处所,尽可能用作保护。”
前方的航线,他们不知走了多少次,可谓轻车熟路。再过两天,“致远”号管带葛尔萨巴图鲁邓总兵世昌,更将迎来他的四十五岁生日。但这一次,一切注定与众不同。
痛失平壤
回头再看十五日(9月14日)的平壤城。叶志超密切关注的大同江东岸仍只是小规模的冲突与相互炮击。一整天,日军并没有进攻,叶志超正纳闷,坏消息已从城北传来。
原来,朔宁、元山两支队业已会师,两军于当日猛攻玄武门外清军山岳防线。守军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无奈日军攻势如潮,步炮协同密切,激战竟日,城外高地相继失守。左宝贵反攻失利,只有退守城墙工事。
消息传来,叶志超才猛然惊觉,自己业已犯下与当年守北宁的黄桂兰一样的错误。
顿足长叹中,叶志超知道:大势去矣!
所幸正面日军并未发动大规模进攻,虽然原因还不清楚,总之对我有利。在叶志超看来,这是撤退的大好时机。否则一旦北路日军全面控制北城制高点,南路日军全力进攻,清军走走不了,战则只有坐以待毙。那就全玩完了。
对叶志超的撤军构想,左宝贵坚决反对。所谓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仗未开就轻弃平壤,如何面对皇上、太后,又如何面对江东父老?
叶志超无话可说。
于是,撤退命令被取消。叶本人也被左的亲兵软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