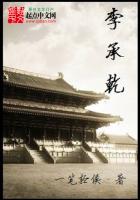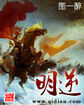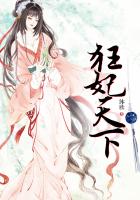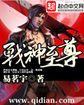既然要战,就应集中兵力于北门,夺回生死攸关的致高点,并打通后撤路线,然后再集中兵力于其他战场,如此胜则逐个击破,败则有路可退,这才是死里求生之道。但可惜的是,不等清军调整部署,大岛义昌已于当晚凌晨一时,对叶志超瞅了好几天的大同江东岸,发起了计划中的自杀性进攻。
事实上,按日军的原计划,这个进攻应在朔宁、元山两支队南下之前发起,从而达到预期的歼灭战效果。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由于野津的第二路军遇上江水暴涨,结果耽误了整整一天的行程,而朔宁、元山两支队反提前展开了进攻。对清军这是一眨眼的好机会。若叶志超不是那么过于注重南面防御,而是集中兵力打击朔宁、元山两支队,战局就将全面改写。退一步,在两支队已拿下北门外高地的情况下,清军至少还能撤出孤城平壤,像牙山之战后那样,全师而退——失去南路支援的北路日军孤力是留不住清军的。
但很可惜,清军未能抓住这一眨眼的机会。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北路日军的战果,大岛与野津都不知道。同理,大岛与野津的情况,北路两支队同样糊里糊涂。这就是在通讯、交通落后的年代进行分击合击作战的风险。时间已是十五日深夜,大岛才与野津、朔宁支队先后取得联系。大岛这才知道,野津的部队仍未进入攻击阵位,野津本人的大脑也仍在继续灌水。他居然要求大岛将攻击日期再推迟一天,以等待自己进入攻击位置。
大岛终于愤怒了!
在大岛看来,自己的攻击本是为朔宁、元山两支队创造战机,可是现在“元山、朔宁两路,计已如期攻平壤之后”,我军反而落后,“其若预约何!况贵督大军未至,我岂能逡巡观望?”
就这样,大岛在野津误期、北路战况不明的情况下,断然于十六日凌晨一时,分兵三路,向大同江东岸的清军发起了猛烈进攻。
日军首先遭遇了马玉昆部毅军的顽强抵抗,双方以互不相让的勇气在暗夜中修罗恶鬼般血战。当太阳照亮战场时,大同江西岸的卫汝贵看到的是他致死难忘的一幕:弹雨中,遍野的死尸上,双方士兵在以最原始的血腥搏杀。关键时刻,卫汝贵立即亲率盛军四营渡江助战,挥军大举反攻。激战一直持续到下午二时四十分,日军弹药已尽,基层军官死伤惨重,士兵普遍筋疲力尽,而清军斗志仍盛,大岛只好下令撤退。至于战场上的日军遗尸,既无法拖带,又来不及掩埋,只好将死者“遗发及名牌收藏”后,任其横尸疆场。下午四时,天降暴雨,清军停止追击,日军则冒雨继续撤退。据日军初步统计,这场战斗阵亡约140人,伤约290人——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
同一天的凌晨七时,迟到的野津终于对平壤西南,发起了计划中的“乘机突击”。但是正如前文所记,在西南战场,叶志超布置的兵力最多,达7000余人,大岛以优势兵力尚不能突破大同江,野津以少打多,又加长途跋涉,体力透支,又如何攻入平壤?
战至中午,野津以“白昼不宜进攻”为由,在大岛还在苦战的时候,命令部队“暂且退居要地”,先败退出了战场。
对清军而言,美中不足的是,丰升阿发起了一场画蛇添足的反击。他派骑兵冲击日军据守的高地,在日军的密集火力拦阻下,清军损失了273匹战马,伤亡130余名士兵后,撤回城内。
但日军的攻击毕竟失利,最糟糕的是,他们的军粮和弹药都不充足了。
野津越想越觉得失败,于是说下一段硬话:“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竟不能陷之,有何面目归谒我天皇陛下?我意已决,明日之战,举全军以进逼城下,冒敌弹,攀胸墙,胜败在此一举!我军幸得陷城,我愿足矣;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
可是,胜利之于军人,终究是没有替代品的。战争中,少不了豪言壮语,但豪言壮语却无法替代战争。
综观十六日一天的激战,似乎清军即将获胜。可惜,日军的杀手锏是朔宁、元山两支队。
十六日凌晨五时,也就是马玉昆在大同江东岸与大岛义昌浴血奋战之际,日军元山、朔宁两支队对平壤北部发起了决定全局的总攻击。
激战至上午八时三十分。依仗着准确而协同密切的山炮火力,日军终于攻下了对全城性命攸关的牡丹台。
左宝贵亲自督率敢死队发起了多轮反攻。可是,面对日军居高临下的火力,步队的仰攻是无力的。左宝贵终于明白,平壤城与他的最后时刻到了。
接下来的一幕是令人震惊的。左宝贵穿上了皇上御赐的黄马褂,戴上了他无上勇武象征的头品顶戴,义无返顾的登上了已在日军火力俯射范围内的玄武门城头,亲自开炮击敌。
在战场上,这无疑是一个太过于招摇的目标。那一刻,两军将士都震惊了。
据说,左宝贵一共打出了36发炮弹。
而大势已无法挽回。
在日军猛烈的反击炮火中,左宝贵倒下了,永远的倒下了。
玄武门随之失守。
对叶志超而言,战斗已经结束。头疼的问题是,在制高点已失,日军火炮俯顶的情况下,如何全师而退。
暴雨如注中,平壤城内竖起了一片白旗。叶志超希望能通过转让平壤城,换来停战,从而安全北撤。
可是,日军肉已在口中,还要叶总统来喂吗?于是,日军提出了条件:“若降伏,可允许。应速开城门,集中兵器缴于我军。否则,即攻取之”。
很快,清军作出了答复:降雨甚,刻下兵多,难以速散,当期明朝,开放此门。
看着这张字条,立见尚文笑了:缓兵之计。
立见预感到,当晚清军必将有所行动。于是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地装作接受了清军的条件。实则将日军秘密布置于清军北上道路两侧的险窄之处,静待清军自投罗网。
当晚八点,暴雨如注中,清军取道平壤西面的七星门和静海门,沿义州大道北撤。一开始,清军还尽量保持秩序,但很快就乱了套。雨大、路滑、人多、退心切,大家争道北撤,反而阻塞了交通。
一片混乱的暗夜中,早已潜伏好的日军,向毫不知情的清军,举起了黑洞洞的枪口。
枪声、炮声、雨声、骂声、绝望的惨叫声……这就是那个晚上平壤城郊的真实写照。
一天的激战,清军也不过战损200余人,但这一个晚上的损失就达到了2000余人(亡1500余人,被俘683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死于混乱中的互相践踏,其中甚至包括了盛宣怀的兄弟盛星怀。
日军就这样占领了平壤,缴获的物资堆积如山,相对于清军抱弃的那些多已发锈的老式火炮,已二十多天粒米未进的日军无疑更兴奋于那4700石军粮,和354口行军锅。
而叶志超的“联军”经此一撤,组织全无,一路溃逃,武装损失殆尽不说,士气的打击更是致命的。
这边厢平壤失守,那边厢北京城里的文武百官又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忙着讨论老太后的徽号问题。经过诸重臣的慎重集议,太后的徽号最后定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禧皇太后。一共是16个字,比中法战争那会又有了新长进。要知道,乾隆早有规定,皇后、皇太后驾崩之后,尊谥最多不得超过16个字。现在西太后人还活着,就享此殊荣,真可谓大清国的空前。事实证明,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绝大清之后。
意外的海战机会
就在北洋水师扬帆出航的9月15日,联合舰队主力顺利抵达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的大青岛。伊东派出速度最快的第一游击队四舰,分两路搜寻北洋水师主力。但是忙碌了一天,一无所获。
对伊东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坏消息。只要北洋水师不出动,他就算完成了掩护陆军作战的任务。而一旦陆军运输完毕,第二游击队就将解放出来。到那个时候再进行主力海战,对他更有利。
所以16日上午,伊东拟定的新计划并不是如何抓紧进行主力海战,而是来一次空前雄壮的渤海湾武装大游行,好好刺激一下清政府,令敌人的指挥中枢更加手忙脚乱。他计划16日下午开始巡航,24日结束。航线:小乳纛角,海洋岛,小鹿岛,威海卫,大连湾,旅顺口,大沽口,山海关,牛庄,威海卫,然后再回到小乳纛角。
就在联合舰队即将出发之时,伊东终于收到了来自陆军的紧急电报:北洋水师主力正集中于大孤岛港外的大鹿岛附近从事警戒。
这正是野津道贯的功劳。
此前,大鸟圭介也曾发来电报,称“中国军队取海路前来朝鲜,估计要在大鹿岛一带登陆。”但伊东并未很在意,现在看来,所言非虚。
联合舰队又一次驰到了抉择的关口。是攻?是守?若攻,要不要将仁川的第二游击队也带上?
最终,伊东决定进攻,但并不带第二游击队。一者他不敢冒让仁川门户大开的危险;二者他坚信手中的力量已足以击败老朽的北洋水师。结果,他不仅未等第二游击队,更将第三游击队也留在了大同江口,然后亲率本队与第一游击队北上。事后的实战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考虑到大鹿岛靠近海岸线,伊东特地带上了第二游击队中的赤诚号炮舰。因为该舰吃水浅,便于近海与岛屿搜索。桦山资纪则乘坐西京丸随行观战。
下午五时,第一游击队鼓浪先发,本队六舰随之驶离小乳纛角,西、赤两船则位于本队右侧跟进。
黄昏时分,天降雷雨,西南风也愈刮愈猛,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伊东的决心,也不能放慢联合舰队的步伐。
可是,折腾了一个晚上,直到早晨六时半,日舰依然无一发现目标。
会不会是情报有误呢?
有人提出了置疑,可伊东却近乎偏执地坚信,福岛安正陆军中佐的情报绝对不会出错。他命令各舰继续搜索前进,边前进边抓紧时间进行最后的战斗演练。
终于,9月17日十时二十三分,在大鹿岛洋面,一马当先的吉野号率先看到了天边的一柱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