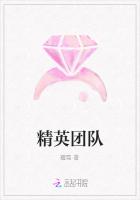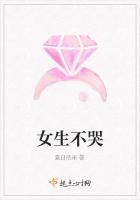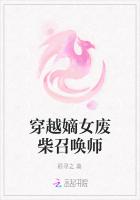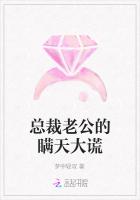研红动机
《红楼梦》是笔者六十年前初中时代就喜欢的读物。虽自1956年考进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国进修,1970年返回母系任教,2006年退休后兼职授课到2011年,做了逾半个世纪的化学人,但未尝疏离此小说或与其相关的研究资料。引起笔者研究兴趣是因1958年秋,听了林语堂先生在台大法学院讲的“平心论高鹗”。他认为全书一百二十回都是曹雪芹写的,也讲到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先生的研究,并以“纵然是糊涂了案,到底意难平”为结。当时觉得甚有启发性。又由于中学时曾听过潘重规先生的公开演讲“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乃和胡、林两位见解又不同,而想到说不定自己将来也可做点有关的研究。职是之故,嗣后暇时,不仅欣赏百二十回《红楼梦》的故事文本,也收集其他版本、书籍和阅读他人发表的研究文章。
从学习和研究化学的经验,笔者渐觉许多读到的《红楼梦》研究结论不够严谨,过程不合科学方法。因思若能掌握足够的资料,自己或可一试。最先尝试的是有关“曹颙遗腹子”的问题,这是因为许多研究乃依据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入嗣子曹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初七写给康熙皇帝“代母谢恩”折,认为曹寅之嫡子曹颙死后留有遗腹子。有人说这遗腹子是曹雪芹,又有人说是曹天祐。此奏折的内容如下:
江宁织造主事奴才曹谨奏:为皇仁浩荡,代母陈情,恭谢天恩事。切(按原文如此,疑应作“窃”)奴才母在江宁,伏蒙万岁天高地厚洪恩,将奴才承嗣袭职、保全家口。奴才母李氏闻命之下,感激痛哭,率领阖家老幼,望阙叩头。随于二月十六日赴京恭谢天恩,行至滁州地方,伏闻万岁谕旨:不必来京,奴才母谨遵旨仍回江宁。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但折中只说马氏怀孕七月,未见任何人举出马氏生男之证据,故觉“曹颙有遗腹子”之说可疑,乃开始了相关的研究。
曹奏折说明曹颙没有遗腹子
实际上,曹颙遗腹子的问题胡适之先生早就于1960年和高阳谈过,他认为“缺乏最后的证据”。因为“第一,我们不知曹颙的妻子马氏生的遗腹孩子是男是女。第二,我们不知那个遗腹孩子长大了没有。第三,我们不知那个孩子——如果是男孩,如果长大了,——是不是名霑,号雪芹。因为没有法子得着最后的证实或否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276—277页)浅见以为这是正确的科学治学态度,所以想找证据以给肯定或否定的答案。
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年和1971年出版的《故宫文献》中刊有院藏江宁织造曹寅、曹颙与曹写给康熙皇帝奏折的部分复印件。当时笔者乃据这些第一手资料,于1976年元旦假期写了第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说明“曹颙没有遗腹子”,故“脂砚斋”不是曹颙的遗腹子。(此文刊于1976年4月22日《联合报》“联合副刊”)按江宁织造除进京述职时期外,须每月上一奏折,向皇帝报告晴雨录及各种事情。现据《故宫文献》与故宫“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全文影像资料库”,知共有曹奏折四十九件。他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就任江宁织造后半年内曾有以下各奏折:
从日期看,其中并无短缺,因而可以视为完整的文献资料,以用为分析和探索。现补充1976年的讨论于后。
三月初七曹除上述之“代母谢恩”折外,还有一封因钦命承袭父兄职衔的谢恩折。四月十七有请安与报告“江南四月雨雪粮价及进呈三月份晴雨录”之奏折。六月初三又有奏折请安,报米价和“谨将江宁四月、五月份晴雨录恭呈御览”。因一般每月初均报告上月的“晴雨录”,四月份的到六月才报告,表示他五月未上奏折。由于六月初三的奏折只是请安、报米价和呈晴雨录,故康熙帝批示:“你家中大小事为何不奏闻?”因此,曹在七月初三虽已有一请安及呈“六月份晴雨录”折,七月十六赶快又上一折,向皇帝报告:
江宁织造主事,奴才曹跪奏:恭请万岁圣安。
七月十四日奴才家奴赍捧折子回南,蒙御批:你家中大小事为何不奏闻,钦此。奴才跪读之下,不胜惶悚恐惧,感激涕零。窃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今复荷蒙天高地厚洪恩,俾令承嗣父职。奴才到任以来亦曾细为查检所有遗存产业,唯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田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此外并无买卖积蓄。奴才问母亲及家下管事人等,皆云奴才父亲在日费用很多,不能顾家。此田产数目奴才哥哥曹颙曾在主子跟前奏过的。幸蒙万岁天恩赏了曹颙三万银子才将私债还完了等语,奴才到任后,理宜即为奏闻,因事属猥屑,不敢轻率,今蒙天恩垂及,谨据实启奏,奴才若少有欺隐,难逃万岁圣鉴,倘一经查出,奴才虽粉身碎骨,不足以蔽辜矣。奴才不胜惶恐感戴之至。
此折中没有只字言及曹颙之妻马氏是否生男,八月之折也未提。可见马氏怀孕十月后,在五六月时或系生女,或因婴儿夭折。故未向皇帝报告。为什么马氏生男之事,须向皇帝报告呢?这是由于康熙帝相当喜爱曹颙。据内务府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十二奏请将曹过继给曹寅之妻李氏为嗣的折中说:
传旨谕内务府总管:曹颙系朕眼看自幼长成,此子甚可惜。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看起来生长的也魁梧,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他在织造上很谨慎。朕对他曾寄予很大的希望。
由于此一报告“家中大小事”只提家产、家中经济而不及马氏是否生男,故可推想马氏并未生男或生男夭折,曹不愿让老皇帝伤心,采用“不报忧”的方式。否则依上述康熙帝对曹颙的评价,如曹颙有嗣,曹岂能不向皇帝报告?故曹颙留有遗腹子之“假设”未得证实,显然“曹颙没有留下遗腹子”。
又《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燕山出版社1990年复制本)虽有“天佑,颙子,官州同”之记载,但此谱关于“曹锡远……曹天佑”这一支,疑问重重,上述记载未可置信,笔者另有他文讨论(《曹雪芹家族文化探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262—269页),兹不赘述。
花气袭人知“昼”暖?
《红楼梦》里的“袭人”,是小说主人公宝玉的大丫鬟,原名“珍珠”,“袭人”一名是宝玉给改的。据“庚辰本”第三回: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花气袭人之句,遂回明贾母更名袭人。
其他各本文字大体相同,唯有些本子“珍珠”作“蕊珠”。《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及第二十八回里曾两度说明,这一“旧人诗句”是指“花气袭人知昼暖”,但未说是何人的诗。笔者孤陋寡闻,多年前读到此句,并不知道其出处,而且也不了解为什么从“花气袭人”会知道“昼暖”?
笔者学“化学”,知道花的香气(“花气”)是由花朵所含具有挥发性芳香气味的有机化合物所产生。这些化合物挥发成气体,接触到嗅觉细胞,使人感觉有芬芳的气息。一般而言,从液体或固体挥发成气体需要吸收热量。多数的花都在白天盛开,且因暖和,气温较高,能促使香气成分自花中释出,会有“花气袭人”的感觉。由于诗句为“知昼暖”,表示不是白天而是在傍晚或晚间写的。但是到了傍晚或晚上,气温下降,一般的花香也减弱,不易有“花气袭人”的感觉,也难能因此知道“昼暖”。即使如“夜来香”之类,晚间的“花气袭人”也与白天暖不暖无关。故笔者有很长一段时期不了解“花气袭人知昼暖”这句诗的意义。
直到二十几年前读到清代人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时,才知道这句诗应作“花气袭人知骤暖”,曹雪芹误以“骤”为“昼”。周春说:
花气袭人知骤暖、鹊声穿竹识新晴,陆放翁佳句也。宝玉用袭人以名花大姐,二字甚韵。后来政老以为淫词艳曲,由政老不知诗之故。
笔者才恍然大悟。因气温突然升高会促使香气自花中挥发,故若感觉“花气袭人”即是天气突然转暖——“骤暖”的一种自然现象。陆放翁的“花气袭人知骤暖”不但是诗中佳句,也合乎事实和科学原理。周春认为小说里的贾政“不知诗”,其实,小说的作者曹雪芹也似不甚了解这句诗。按吴语“昼”“骤”二字音近,他一再将“骤暖”写成“昼暖”,表示不解诗意,才有此误。
李纨房的“玻璃窗”问题
第七回写周瑞家的送宫花到各处,有一段在多种抄本,“程高本”及通行本均为“……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越西花墙……”“甲戌本”“有正本”和“蒙府本”在“过”字下都有双行夹批“细极,李纨虽无花,岂可(失而)不写者,故用此顺笔便墨……”但“己卯本”“庚辰本”和“杨藏本”无此批,而文本作:“……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隔着玻璃窗户,见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呢,遂越过西花墙……”所增“隔着玻璃窗户,见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呢”十几字,笔者看来,颇不合理。首先的问题是:“白天能从玻璃窗外看见屋内情形吗?”一般而言,白天外面亮,屋里暗,是不能从玻璃窗外看见屋内情形的。《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叙述宝玉的丫鬟小红(或作“红玉”)“在窗户眼内往外一看……”四十九回写到宝玉在怡红院里“忙起来,揭开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故知“玻璃窗”可能只是一小块玻璃的“窗户眼”,且有遮光的窗屉。由此亦可证明李纨卧室若有玻璃窗应在前方,且只是有窗屉的“窗户眼”,从外面是看不见屋里的。另一疑问是:“女人,尤其是寡居少奶奶的卧炕,能让人从屋外看见吗?”《红楼梦》的作者似不应这样写。换言之,周瑞家的白天隔着玻璃后窗,看见李纨在炕上睡觉的这一描述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情。
再者,制作透明无色平板玻璃之技术,较普通器物为复杂。据笔者所知,18世纪中业以前(乾隆初年)中国似除内务府“造办处”的皇家作坊外,一般尚无制作透明玻璃窗的能力。除圆明园等皇家宫苑建筑,也无玻璃窗的记载。故可推测,“隔着玻璃窗户,见李纨在炕上歪着睡觉”一句是18世纪后期,甚或19世纪之人所妄添,且是画蛇添足,点金成铁。
结语
笔者读红研红向重文本原典,不强作解人,也不盲从附会。解释或推理不违科学原则,立论则力求客观有据,以遵从科学研究之习惯。以上举三题为例,谨供同好参考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