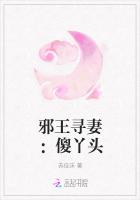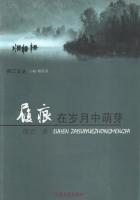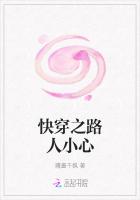仗打到激烈处,美军的一群坦克突然冲到了第149师师部,炮口几乎伸进了院子。师政委兼代师长金振钟得到消息,毫无惊惧之色,冷静地在电话里调集兵力部署反击。正是由于沉着冷静、遇大敌不乱,使敌人根本不知道已经打到志愿军的师部了,结果,在被炸药包炸毁几辆坦克后,这伙敌人狼狈窜去。
仗打到最激烈时,有一个团几乎扛不住了。团长便向师长请示,团部可否向后移。就听师长冷冷地回答:“随你们的便,反正我的位置不动!”结果,这个团再也不提后撤的事儿了,团部在前沿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2月1日至3日,某营副营长戴汝吉带领第8连防御白云山西端侧翼的白云寺。仗打得非常惨烈,阵地上只剩下10多个伤病员,就要支撑不住了,负伤的戴汝吉吹着牛角号,在阵地上来回奔跑指挥,鼓励士兵,一直坚持到援军赶到。
仗打了不到半个月,第50军就已经伤亡过半,全军勉强能成建制投入战斗的兵力只剩下不到半个师了。志愿军节节抵抗,逐步放弃一线阵地。2月7日,为避免陷入背水作战和地形狭窄受敌优势地空火力杀伤的不利境地,第50军主力遵照总部命令,转移至汉江北岸。
到了汉江北岸,第50军将士又直面美国王牌兵团,坚持了一个多月,给美军第1军所属之美步兵第3师、步兵第25师,韩军第1师、英步兵第29旅部队以沉重打击。
50天惨烈的汉江阻击战,第50军共毙、伤、俘敌1.1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15架,击毁敌坦克等各种车辆70余辆。这样的战绩,难能可贵。
防御作战尚未结束,彭德怀司令员就赶到第50军,接见了曾泽生和这支已经所剩无几、蓬头垢面的部队。
当彭德怀看到硝烟中这些头包纱布、面容黄黑、缺胳膊少腿的硬汉子时,两只大手紧紧握住曾泽生军长,对他们慰问有加。
1973年2月22日,曾泽生将军去世,享年71岁。
他是一个汉子,一个硬汉子,一个带着一群硬汉子的硬汉子!
万岁军第38军打得也非常出色。
第50军和第38军,都得到了彭德怀的表扬。
作家魏巍上前线采访,看到志愿军英勇作战的场面,心情难以平静,又写了一篇战地通讯《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看后让人激动不已。
志愿军的防御战术
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又将战场分为西线和东线。
西线指挥被称为“韩指”,是副司令员韩先楚率领的以第38军和第50军为主的部队。
东线指挥被称为“邓指”,是副司令员邓华率领的部队。
为打好这种不熟悉的防御作战,志愿军总部经过认真研究,专门下发指示,明确了这样的作战原则:
疏散配置,机动防守;
防御作战,工事坚固;
兵力配备,前轻后重;
火力配备,前重后轻。
较大反击,夜间进行;
无力防守,主动转移。
这些原则,是志愿军司令部对现代化战争的规律性探索,很好地指导了整个防御作战。
让邓华后悔一辈子的决策
东线反击作战怎么打,是摆在志愿军将领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不同于西线,联合国军在东线的进攻非常慎重、小心,协调也比较好。
1月28日,东线美第10军向骊州以东至原州、武陵里一线发起进攻,突击方向在横城、砥平里;韩军第3军、第1军突击方向在县里、襄阳。我第42军第125师及人民军第5军团节节阻击,掩护志愿军主力开进。31日,第125师在九屯车站包围了美2师第23团团部及一个加强营,经一天激烈战斗,未能全歼该敌即主动撤围,至2月9日,南汉江以东之敌被我阻止在砥平里、分水院、上苍峰里、釜洞里、乌项里、束沙里、广川一线地区。
此时,横城、砥平里两个地方,突了出来。
先打横城还是先打砥平里,就成为摆在志愿军司令部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
此时,一向以果敢著称的彭德怀出现了指挥作战几十年来少有的犹豫,志愿军总部的两个主要将领——邓华和韩先楚副司令员意见也出现了不一致,争执起来。
这次争执,被称为“第二次邓韩之争”。
邓华和韩先楚两位虎将,都是四野名将。
邓华,原名邓多华,湖南郴县人。祖辈三代书香,自幼喜好古文,博览群书,尤爱《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
据介绍,邓华将军广闻博记,才华出众。早在红军时期,一次东渡黄河,毛泽东为红一军团诸将领送行,随口吟诗道:“涉远祁连外,来从晋地游。”众将军皆不知所云,面面相觑。
邓华将军略思片刻,对曰:“主席是改用李白《渡荆门送别》诗的前两句,为我们送行呢。”
随即背诵全诗: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方荣翔,著名京剧大师,曾被国民党第71军收编为该军第88师京剧队。东野大军解放四平后,有一日,突然有三驾马车前来接他去赴宴,宴请者是邓华将军。后来,七纵成立了以方荣翔为主要演员的京剧团。龙书金将军曾说:“邓华将军身材修长,面孔白皙,武官文相也。然治军极严,训人如雷霆震荡,暴雨倾盆,人皆惧之。”
邓华将军为人耿直,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顶住压力,为自己的老领导彭德怀辩护,结果受到牵连,1960年被贬谪四川。离京前,将军将军装尽染黑色:黑帽、黑衣、黑裤、黑鞋,以示不满。
第一次邓韩之争,发生在四野部队攻打海南岛时,那次林彪采纳了邓华的稳妥方案。
这次,彭德怀该怎样决策呢。
邓华倾向于先打横城。他的观点是:守卫砥平里的美第23团兵力比较集中,战斗力较强,且已构筑了工事,不易被迅速分割歼灭。如果一两个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则利川及原州附近的联合国军就会来援,这样,仗就打成了黏糊战。对于既无地面装备优势更无制空权的志愿军来说,情况极为被动。
先打横城的好处,就在于横城的联合国军兵力人数虽多,但横城以北的韩军第8师、第5师兵力分散,战斗力不强,利于志愿军快速歼灭。
韩先楚副司令员则建议先打砥平里。他的理由是:“你邓华讲得有一定道理。但从战略位置看,砥平里是威胁西线后方的一根刺,它离西线较近,属于枢纽位置,一旦占领,就能迅速西向,威胁联合国军的西部战线,使其全线动摇。而打横城,虽然能够取得较大战果,但从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和作用看,则小得多。”
先打砥平里侧重于打得准,打横城则侧重于打得痛。犹豫再三,彭德怀最后采纳了邓华的意见,志愿军将反击目标东移,定至横城,先消灭战斗力较弱的韩军第5师和第8师。
此时,李奇微看到志愿军如此被动,正在为自己的计谋成功而高兴呢。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西部防线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彭德怀还将捉襟见肘的志愿军主力集中到东线,反手打他。当然,他也没有料到志愿军在东线会放着砥平里不打,先打横城。
横城战斗打得很漂亮,将联合国军打得很惨。李奇微等美方将领都认为,横城惨败是上了中方欺骗策略的当。志愿军的这一决策,对第四次战役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以后的战局,乃至双方作战心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仗,也使具有反思精神的邓华将军在后来的岁月中后悔不已,他认为还是韩先楚将军的判断正确。因为砥平里虽小、虽然难打,但打的是七寸,打的是要害;而横城歼敌虽多、虽易,但打的是屁股,打的不是要命的位置。
他还将这一判断,定为自己一生几大军事决策失误之一。
打赢了横城反击战,但输了全局
1951年2月11日晚,横城反击战打响。
志愿军集中了9个师的重兵,对横城的联合国军实施了完美的三重钳形穿插包围。几小时后,韩军第8师师部与所属各团及下属部队的联系全部中断。完全超出李奇微及联合国军高层的设想,他们根本没想到中方在横城有力量发起这么大的攻势,因而延误了宝贵的撤退时间。而撤退的联合国军又摆出一字形的后退队形,这是非常臭的做法。
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中方以伤亡4100人的代价,共歼灭联合国军1.2万人,其中有美军2000人。此次反击战还俘虏了韩军7500人、美军500人,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俘虏韩军数量最多的一次战斗。
对于横城败绩,美军第10军司令阿尔蒙德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正是阿尔蒙德的瞎指挥,使邓华有机可乘。而阿尔蒙德将军则刮了帽子赖天爷,将失败原因归于“指挥官缺少积极进取的领导能力”,指责“在危机出现时现场高级指挥官没有积极主动地指挥邻近部队并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调集空军、炮兵、装甲兵和步兵去消灭包围我们部队的敌人”。
打了败仗后,治军严格的李奇微派出了调查组。在美军调查组的报告上,将矛头指向了倒霉的韩军,称“韩8师没有或几乎没有警告的突然和彻底的失败,连累了美2师”。
韩军指挥官白善烨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什么阿尔蒙德指挥下的韩军总是受到首轮攻击而别的地方不是如此?”白善烨认为,不排除阿尔蒙德有意让韩军首先承受预料中的中方攻势的可能性。
横城战役,是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发动的最漂亮、最成功的战斗之一。对这一点,中美双方都认同。
志愿军虽然在横城打得漂亮,但放到全局,是不是打得漂亮呢,这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