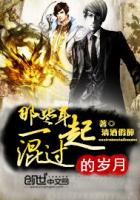武松一刀劈过去,
却扑了个空,
劲使得猛,头重脚轻,
一个跟头栽到溪里。
……
本夜话题
武松李逵,打虎谁英雄
——写作的辩证法
《水浒传》中,好汉和老虎较量,一个是武松,一个是李逵。武松景阳冈上打死了一只老虎。李逵沂岭上却一口气杀死了大大小小四只老虎。然而,一提起打虎来,大家不约而同想到的是武松;至于李逵,就很少有人把他和打虎联系起来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水浒传》的作者,是怎样分别来写他们两个人打虎的。先说景阳冈武松打虎。武松别了宋江,一路来到阳谷县地面。他不服那“三碗不过冈”的说辞,一连喝了十五碗酒。他要动身,店家提醒他,不可一个人,更不可在晚上过冈: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武松不信,以为是店家骗他留宿住店,便提了哨棍,自过景阳冈来。来到冈子下,看了树上写的两行字,警告有虎,还以为是酒家的把戏,吓唬人回去住店。可见他并非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可见,他根本就不是怀着上山打虎的豪气,准备打虎去的。
等来到山神庙,看了阳谷县的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第一个念头是转身回酒店。但怕吃人耻笑,才又硬了头皮往上走。还想的是上去看他怎地——心存侥幸不是?这样一个十分了得的英雄,也不愿单独一个人去惹那个大虫的。真有些英雄气短了。
上了冈,待到随一阵狂风,跳出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一声“呵呀”,闪在青石边。老虎第一扑,武松一惊,连酒都做冷汗出了。而且,慌乱间,举起哨棍劈将下来,打虎不着,反把哨棍折做两截。这一“惊”一“慌”,全无半点无所畏惧的豪杰样子。
一顿拳脚之后,老虎气都没了,还怕不死,又捡回半截断棍,把个死虎打了一回。想要拖那死虎下冈,“手脚都疏软了,动掸不得”。这是什么英雄呀,胆小鬼一个,胆怯力亏得没法儿说。
下冈子来,碰到由猎户装扮的两个假大虫,倒把武松又吓了一跳,叫道:“呵呀,我今番罢了!”哪里还有些英雄的胆略英雄的气魄。
这便是那个人人皆知的打虎英雄。再看沂岭李逵杀虎。
话说李逵要取老娘到水泊梁山快乐几时,往沂州地界去,半道杀了个假李逵,到家背了老娘,“于乱山深处,一步步捱上沂岭”。娘要喝水。李逵庵里找个香炉盛涧里水,来到松树边,石头上竟不见了娘。定眼四望,见有血迹;沿血迹寻将去,就到了老虎洞。
先见洞里有两个小大虫,李逵挺起朴刀去搠。一个被搠得慌,张牙舞爪蹿上前来,李逵手起搠死了。另一个便往洞里钻,被李逵赶到洞里,也搠死了。举手之劳,刀起虎毙。
李逵伏在洞里张望。母大虫又张牙舞爪地来了,尾巴去窝里一剪,后半截身躯坐到洞里来。李逵用腰刀尽平生气力舍命一戳,连刀把子都送到了母大虫的肚子里。从容镇定,干净利落。
母老虎逃出洞口,抢下山岩。李逵恰待要赶,就见卷起一阵狂风:是那公老虎来了,原来也是只吊睛白额大虫。那大虫猛一扑,李逵不慌不忙,手起一刀,正中大虫颔下。那大虫退不到五七步,如倒半壁山,登时死在岩下。这吊睛白额大虫,在李逵面前,也不过是个纸老虎。
作者赞道:“猛拚一身探虎穴,立诛四虎报冤仇。”
《水浒传》的作者,的确是精心写了武松打虎;李逵杀虎,则写得较粗。这无可否认。但这绝不是武松比李逵在打虎上更出名的主要原因。武松未见虎就先怯了,还曾想转回身来;只是怕人耻笑仗了酒性硬着头皮上了冈;老虎来了又惊又慌,出冷汗,折了哨棍;打完虎累得手脚酥软,动弹不得,也才打死了一只虎。李逵明知有虎,偏寻了虎去;于不慌不忙之中,三下五除二,就送老虎一家四口见了阎王。
武松李逵,打虎谁英雄?谁是真的英雄?大家还是觉得,恐怕武松更英雄,是真的打虎英雄。到底为什么?
武松是用拳脚“打”死老虎的,而李逵是凭借了刀“杀”死老虎的。但这也不是武松更英雄的主要原因。
武松的转念,武松的惊慌,武松的胆怯力亏手脚酥软,都是合乎人情常理的事。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大虫,毕竟不是一只兔子,一只猫咪。所以,武松打虎,才打得真实,打的也是真老虎,也才见出了英雄本色。而李逵,杀四只老虎,就像杀兔子杀猫一样的轻松容易,这就有些玄乎了,给人的是不够真实不可信的感觉,也就不觉得李逵是个英雄了——打虎的英雄。
所以,人们认同了打死一只虎的好汉,觉得他英雄;而且觉得心慌胆怯力亏但终于打死了一只老虎的武松,才是真实的英雄,真正的英雄。
打死了一只老虎的,比杀死了四只老虎的更英雄;心慌胆怯力亏的,比不慌不忙杀虎如杀兔杀猫的,更显英雄本色。
少胜于多,弱胜于强。
——这就是写作的辩证法。再看以下的情况。
《三国演义》写刘备的“仁义”,最典型的一处是第四十二回的“马前掷亲儿”。刘备兵败新野,仓皇间由张飞护过长坂桥,诸将及妻儿皆在混战中失散。赵子龙于乱军之中,单骑救出刘备的儿子阿斗,抱护在怀中,一路杀出重围。赵子龙见了刘备,双手递给刘备。刘备接过,掷之于地,说道:“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这就是所谓的“无由抚慰忠臣意,故把亲儿掷马前”。刘备的这种“仁义”之举,总显得有些做作和矫情。
写诸葛亮的“智”,可圈可点的地方也不少。如果说,诸葛亮料到大将魏延日后必反,并在生前留下“锦囊妙计”,等魏延真的反叛了再除掉魏延,还可以彰显其“智”的话,那么,诸葛亮在赤壁之战时设七星坛祭东风,在五丈原禳星增寿,就神奇得有些过头了。
难怪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作如是评价:“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过犹不及,渲染得过了头,就可能失去艺术的真实性,反倒不如平实一些的好。
《红楼梦》中的人物描写,很有自己的独到处。第二十回,写黛玉正和宝玉说话,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黛玉听了,笑话湘云:“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这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着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咬舌子”,于一般的人,也许是个缺点,但在湘云,越显出了她俏皮的“风风火火”性情,更显得淘气可爱。
第四十八回,写香菱跟着黛玉学作诗,读杜诗,竟茶饭无心,坐卧不定。宝钗见了,说道:“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他算帐去。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在这里,香菱的“呆气”,反倒给她添了几分特殊的雅致,多了几分天真纯洁的情韵。
同样,黛玉的“尖刻”,黛玉的“小心眼儿”,还有宝玉的“痴”,也都是一路写法。
写到贾雨村这样的奸佞之辈,作者反倒给了一副好相貌。在第一回里,甄家丫鬟的眼中,贾雨村“生的腰圆背厚,面阔耳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很有些雄壮的样子。但这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好相貌,而使人在他后来判“葫芦”案时,觉出他有凛然正气。
美而有些缺点,不但不会损害美,有时反而会增加真实感,会美得更有情致。同理,让反派人物“人模人样”,不搞脸谱化,甚至给他安上一副好面孔,有时会让人在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中,更能深刻地体味出反面角色卑劣的一面来。
缺点增添了人物的美感,英武的相貌凸显了灵魂的肮脏。
《脂砚斋评石头记(庚辰本)》中,脂砚斋在“湘云咬舌”一段的批语中,有“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的说法,讲的就是写作的这种辩证法。